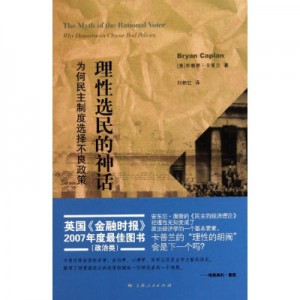 摘要: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摘要: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第一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的缘故。”
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乐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到了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面。
第二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的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结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政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经济政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
第三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阶段。以威特曼(Donald 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威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
威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费者。这个机制一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就说明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
第四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阶段。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把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突破口出现在1997年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 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政议政,不是因为自己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卡普兰(Bryan Caplan)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老百姓就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职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职业经济学家则视之为手段。这解释了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
反市场偏见——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老百姓普遍不以为然。这解释了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行其道的现象。
悲观偏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老百姓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
卡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蒙受股市上的亏损。然而,人们如果在政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侪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政策之苦”的积极性。
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政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顾低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黄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人们这种在言论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要减少“理性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布赖恩•卡普兰博士是我在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系求学时的老师,译者刘艳红博士则是当时梅森经济系的访问学者。应邀为师友的重要作品作序,是我莫大的光荣。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网易云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