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这篇五万字的长文是夏明教授新著《高山流水论西藏》(台北:雪域出版社,2019年)的理论总结。本书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六十周年结集而成。为了推动海内外读者深入了解和讨论西藏与中国、民族构架和中国未来前途等重大问题,我们特此在《纵览中国》上发表本重要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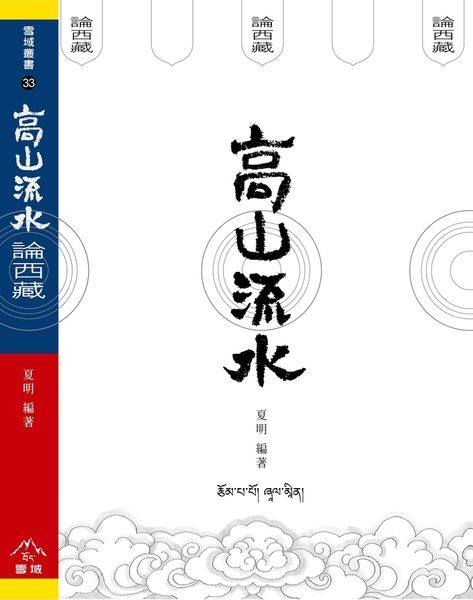
引言
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她古老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面临灭绝的问题,也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屠杀最终将导致的种族灭绝。也有人说,它是中国对另外一个独立国家西藏的入侵、占领和殖民统治的问题。还有人说,它是西藏人为获得独立自由、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亦即西藏归藏人的斗争而引发的藏人与汉人、西藏与中国的冲突。
如果仔细分析,上述三个认识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犹如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它们又只是片面的和肤浅的。第一个认识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问题的症候,不一定是反映了人类族群生存和冲突的本质。第二个认识部分揭示了西藏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过程,但并非事情的全貌,也无法从复杂的族裔上的汉藏关系、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西藏关系认清自身的认知困境,那就是用西方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出现的一个特定国际观,亦即以追求权力和财富为首要目的的国际现实主义(经常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认识、甚至规范东方几千年文化模式中发展出的社会、族裔、小区和国家的治理调节模式。第三个认识着重的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因为没有认清西藏问题的实质,这种解决方法更多的是一种从部分藏人角度出发的单向度的思考;在排斥了他们最大的竞争谈判对手的根本利益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必然陷入唐吉诃德似的简单浪漫主义,其危害可能超过正面的贡献。
面对复杂而又充满情绪化、猜疑心的言语、思维的论争,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试图跳出汉人思维的樊篱,也摆脱藏人诉求的局限,从多层次(小区、族裔、国家、联邦制形式的复合国家、区域民主自由国家共同体、世界大同的世界主义)和多视角(政治、经济、历史、道德伦理和宗教视角,个人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世界主义、超越精神以及“生命网络”的全息整体思维)来透视西藏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双赢的、建立可持续性的、永久和平的方案。本章的思想基础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普世、非暴力、世俗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以此为延伸,作者一方面梳理达赖喇嘛尊崇的圣雄甘地的思想,提炼出印度-佛教有关人类小区解决冲突、和谐共处的智慧;另一方面,作者又将东方智慧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连接起来,探寻出一套思考、认清和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价值。在融贯东西方文化智慧、综合出普世的政治冲突解决方案的努力中,两位印裔背景的美国学者阿玛塔亚•森和杜赞奇有关现代性、族裔认同、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的论述极富有创新性和启发性。最后,从康德和罗尔斯的有关共建人类和谐的政治哲学中吸取养料,提出一系列超越族群、宗教、地域、国别和阶级的自由主义普世认知。
达赖喇嘛明确指出:“西藏问题,也不仅仅是有关西藏人利益的问题。大而言之,它影响世界和平,特别是关系到亚洲的利益和未来。西藏问题关系重大,而且是正义与功利的争取。”[1] 如果我们只是就西藏问题论述西藏,我们将浪费一个思考全球危机和寻找出一个营建全球永久和平方略的机会。就在本书即将完稿的2018年夏天,《纽约时报》(2018年7月19日)头版报导,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宣布“以色列是犹太人民的民族国家”。《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的基本法给予了犹太民族民族自决权,强调“民族自决权是犹太人民独享的权利”,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并不享有这一权利,阿拉伯语也从过去的官方语地位被降至特殊语言地位。阿拉伯裔的议会议员谴责这是一项“种族隔离”的法律,“带着震惊和悲伤宣布民主在以色列的死亡”,“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正式开始”,这是又一个“黑色的日子”。即便一名温和派的犹太裔议员也说这项法律是“给民主的一剂毒药”。永无穷尽的阿以冲突根源在于族裔认同、民族自决、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要协调共存充满困难和危机,这已成为一项全球性挑战。所以,西藏问题的实质是过去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加全球性的一个危机表现,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专制体制下,民主的公民权如何构建;实现民主建制后,自由民主又将如何包容和鼓励多元性并将差异变成社会制度优势;在全球化和高科技加速突变的前提下,多元与博爱,民主与差异动态中带来的各种挑战及其解决如何必须放在个人与集体互动,小区和全球整合的相互依存的网络思维下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个人和民族认同的多元理论
为了逻辑清晰和组织结构安排,我首先讨论有关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和公民权的四种基本理论:本质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本质主义可能是其中最古老的哲学分析方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物质存在着不同的本质,因而不同物体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偶然意外的)差异。当我们把某项物体的随机的、偶然的、可选择性的特质全部舍象以后,我们就抽象出了本质。持这种观点的人经常会把种族、族裔、性别等群体特征归于某种本质,因而把他们看作永恒的、天然的、不可更变的特征。人类学家戈茨(Clifford Geertz)谈到,在六十年代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情绪不满造就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原始的关系”(关联、依恋)上的。“原始的依恋是指那种发自许多先定事实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文化不可避免牵涉所谓的‘既定的’社会存在:主要是直接相邻和血缘关系,但除此以外,‘既定的’也来自生长于同一个宗教小区,讲一种特定的语言,或者某种语言的特定方言,遵守特定的社会行为等等。这些血缘、语言、习俗等等的一致被看作是有一种无以言表并时常强大有力的、内在的和释放出来的强制性。一个人和他/她的亲戚、邻居、同修事实上绑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情感、务实的需求、共同利益或者肩负的义务,而且也至少是因为这种纽带而产生的某种无法说清的绝对的重要意义。”[2] 在强调共同纯洁的血缘时,本质论的民族主义者自认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事实上存在或者在神话故事中创造和想象),而无视征服、移民、通婚等带来的血液融合和人种杂交。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民族主义研究权威汉斯•科亨就指出:“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流动和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已经把混合杂居带到了每一个地方,因此,现在几乎没有多少民族能声称有近似共同血缘的东西。” [3] 在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后,在二十一世纪更没有多少民族能声称民族血缘的纯洁。
自由主义是随着启蒙运动而兴起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人的理性(这一点又和本质主义有点关联,因为启蒙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理性)和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人必须是自由的、自治的,保护这种自由和权利的是民主的民族国家,它保护公民权。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在英国、美国、法国(这三个国家被不同的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滥觞,例如莉雅•格林菲尔德认为是英国,安德森认为是美国,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是大革命的法国)等西方地区同时出现,第一代的民族国家和国内的自由宪政民主匹配较好。因此,国家主权、疆界、国籍、公民和公民权利意味着接纳和排斥在同时进行:公民和外国人的差异。当最早出现的西方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现代性,整合出一个比较均质的民主政治文化时,强调和鼓励个人的自治、自决,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熟,对民主政体是一个帮助。自由主义暗含的一个前提是,现代化最终会帮助所有人“脱魔”,走出传统社会(部落、村社、族群等等),在“进步和发展”指引的线性历史进程中成为现代人,因此在普世的自由主义和平等的价值观下完成种族的融合(美国作为种族“大熔炉”多少反映了这种理想)。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回答“民族是什么?”时,写下了下面的话:“人不是被奴役的,他的种族也不是,他的语言也不是,他的宗教也不是,河道也不是,山脉走向也不是。一大群人聚集有健康的灵魂和温暖的心,创造出道德的良心,这就被称为一个民族。当这个道德的良心能够要求个人为小区利益牺牲自己从而证明自己的力量后,它就是有合法性的,就有生存的权利。”[4]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全面继承了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亚当•斯密和康德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威尔逊三合一”(Wilsonian Triad): 利伯维尔场、民主(共和)政体和世界和平。和这一总体构架相连还有“民族自决权”。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美国没有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主义包袱,所以也乐于慷他人之慨,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这项政策持续到二战结束后,直到美国和苏联进入冷战,民族独立运动更多倾向东方阵营,美国的热情才减少。
马克思主义和启蒙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普世性、现代性和国际主义上,二者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看重阶级性,认为民族压迫和性别压迫最终是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在社会政治分析中,族裔、血缘和性别都是次等的,而且会随着现代化逐渐削弱最终消灭它们带来的差异。民族同化和民族最终的融合将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明确支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提出“民族自决权”,并阐述了它的三项内容:第一,“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只有分离的权利。”第二,“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鼓励任何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第三,“不能把民族自决问题和某个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无产阶级坚持民族自决权,但并不提倡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现民族自决,而要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是否需要分离和什么时候分离。”[5] 如果“民族自决权”对列宁或毛泽东曾经成为嘴上的口号,其意义也主要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策略手段,是实现无产阶级最终的革命胜利、建立一个无国家、无族裔、无阶级和无差异(贫富、男女、城乡、官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等)的乌托邦的工具。
但随着殖民主义的消亡和全球主义的兴起,不同的宗教和族裔小区在民族国家出现并扩张,认同政治(女权运动、LGBTQ运动等)泛滥,族群和小区共同体的自决要求(尤其是民族自决)开始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政体。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世性都受到批评。身份同质化的模式受到挑战。多元差异性和民主治理形成了张力,并在许多国家造成民主制的危机(前面提到的以色列,以及英国、西班牙、德国等等)。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现代化理论遭遇一系列现实的挫折和理论上的挑战,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结构主义、批评学说、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物质主义等就民族、身份认同、公民权、国籍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在全球主义的推动下,自由主义思潮继续演进;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发生了剧烈的冲撞(特朗普、普金、习近平、厄尔多安、莫迪、安倍、金正恩、杜特尔特等新强人的出现只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过去三十多年的思想发展,给我们认识族裔冲突和和解的话题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思路。为此,自由主义理论家也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探索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后结构主义针对“差异”、“不同”和“多元”挑战了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在《后结构主义:简短导论》[6]一书中提供了一系列有意思的思想:在传统的结构主义看来,语言是整合一个民族的重要规范。但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干预着我们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第6页)。“我们制定出的各种区别不一定是由包围着我们的世界造成的,而是由我们学到的符号化的各种体系产生的。”(第7页)传统上,语词被认为是“符号”,它代表了存在着某处的一种存在;“含义”似乎是存在在词语后面的。但索绪尔(Saussure)认为,“含义就存在在符号之中而不是其他地方”(第10页)。“符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发出符号者和发出的符号(含义),基于不同的场景,即使前者是一样的,但后者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希腊语符号对懂和不懂希腊语的人);“作者”跟“读者”影响了符号的不同意义。如果语言不是私有的,而是公共的,对话性的,而且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是从我们外部得来的,如何确定语言的最终含义就变得难解了(第18页)。针对“独立的、自由的个体”,后结构主义也认识到“主体”(主语、主格)也不是同一、自由的:“主体这个词不只是表述‘自我’的一个常用词。但我们用‘个人’、‘自我’时是要表达一个整体,而‘主体’自身内部是分裂的,而且还和肌体分离。”(第67页)“主体”通常是“复合的主体”;“身份认同意味着同一性,也是它的词义。主体能够产生差异—甚至和自身产生差异。”(第52页)例如,朱莉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名著叫《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第63页)。贝尔西(Belsey)写道:“文化总是‘殖民主义的’,在此它通过自己命名世界和传输行为规范的权力来强加于人。没有人天然地栖息进某一种文化。从定义来看,没有文化是天然产生了。我们都是流亡者。而且,我们归宿的文化绝非完美无缺,绝不是它应该的那样。”(第64页)当结构主义试图发现所有文化中的共同要素、“永恒的人”(eternal man)(第42页),后结构主义得出结论:“我们,说到底,就是差异的创造物。”(第8页)
在论述身份认同时,后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很重视“我们-他们”、“自我-他/她者”和“他者化”(othering)的讨论。贝尔西(Belsey)继续论述道:“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变成了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变得能够表达了。”“但是语言所允许的所有东西都是他者。”一个大写的“他者”(Other)把“语言和文化的相异性”和其他人的差异性区分开来。她继续说道:“大写的他者(Other)先于我们的存在而已在那儿,它也不属于我们。例如,在索要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过程中,既然我们想要沟通而没有除此以外的办法,我们必须从‘他者’借要术语。这样人的这个微小机体起先尚未意识到自我和世界的差别,开始从他的周围环境分离开来,而且被迫用语言中已备好的差异性来形成他的要求,尽管这些差异性可能会使他感到离异的。”(第58页)在结构主义思想里,他者对完全相同者有不可避免的侵入(the inevitable invasion of the other into the selfsame)(第73页)。另一个术语是“构成自身的外物”(the constitutive outside)。民主理论的政治哲学家穆斐(Chantal Mouffe)写道:“‘构成自身的外物’这一观念迫使我们接受这一思想:多元主义意味着冲突和对立的永恒性。实际上它帮助我们认识到,冲突和分裂既不必被不幸地看作一种不能被完全消灭的打搅,也不必被看作是阻止我们完全实现一种不可企及的和谐目的的切实障碍,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和我们理性的、普遍的自我完全吻合。”[7]
政治哲学家为此极为关心“民主与差异性”、“差异性的政治”、“对他者的纳入”等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观察到“民族国家的三个代际”:第一,在西欧和北欧既有的国家领土疆域里建立的民族国家;第二,意大利、德国等“延后的民族”(也包括后来的中欧和东欧)跟随了“一条由宣传播种的期盼型的民族意识开辟出的小道”。此二者通过“从国家到民族”或“从民族到国家”两个不同的路径;但他们的通性是有了一个“文化民族”的“想象中的统一”。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和后来的苏联帝国崩溃,在多多少少掺杂了暴力的独立过程中,族裔的民族兴起,试图填充人为任意划定疆界的国家版图。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尤其是“经济的去国家化”),“国家主权的不断削弱将促成政治体制在超国家的层面建立和扩展。”[8] 哈贝马斯注意到,在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存在一个由模糊逐渐变得尖锐起来的矛盾,“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紧张”:“平等的法治共同体体现的普世性和由历史命运团结起来的小区的独特性构成的张力是植入进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的”(第115页)。在哈贝马斯看来,只要一个民族的公民有“世界主义”的思想,而不是用“族裔中心论”(或者是一个天然的人民概念)来解读民族,这一张力就不会成为危机。“只有一个非天然性的民族概念才能天衣无缝地匹配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普世性的自我认知”(第115页)。
在汉斯•科亨二战时期完成的《民族主义理念》的开山巨著中,他反思纳粹德国的纯种雅利安人血缘构成的民族主义,从西方文明最早的希腊和犹太两大源流中找到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一种“心态”、它不同于“对家庭的爱”或“对家乡的爱”,而是在质上和“爱人类”(博爱)、“爱整个地球”更亲近(第9页)。科亨说:“古代犹太人和希腊人民族的概念起初是完全基于共同的血统。一个被拣选的种族概念,一个上帝保佑的纯净的血的概念,对个人、小区和历史来说都是最伟大的价值,它也激励了具有宗教狂热的天然的部落主义。种族主义也是希腊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没有与宗教和生命的终极意义联在一起,所以没那么高调。但是,历史发展把犹太人和希腊人双双从原始种族的和物质的民族主义概念引导进一个更精神和文化性的概念。随着人类个性的发展和人本主义的成长,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增进,后来古代时期见证了从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民族概念进步到主观的精神性的民族概念。在古代终结之前,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思想发展出普世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看法,把种族和民族文明的各种差异抛在后面,把个人(不管他来自何方)敬赞为整个人类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在古代只有两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人民发展出了一套自觉明晰的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第36页)[9]
但近、现代的民族主义更是美国大革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人民主权、公民平等和世俗主义成为它的三大主要特征。[10] 莉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和乔纳森•伊斯特伍德(Jonathan Eastwood)的研究揭示,因为对民族的界定有复合型和单一型两种,对民族成员的本质界定标准又有从族裔性和公民性两种,历史的演进造就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第一,个人主义和公民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复合型的,是个人们的结合,例如英、美。第二,集体主义和公民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单一型的,是基于其独特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一个不可再分解的整体,例如法国和以色列。第三,集体主义和族裔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单一型的,而且是由族裔因素,主要是遗传、基因标准来界定民族的成员。在族裔的民族主义下,它强调的是血缘,“生物性变成了命定”(Biology becomes destiny)。他们说,
如果个人不是生之具有某种民族性,就不可能获得;如果某人生在一个民族,那就不能放弃,就像血型不可更改。那些这样做的两类人要么被看作是冒名骗子,要么是族奸,总之就是某种罪犯。个人意愿和民族、语言的选择、宗教、价值观、对特定国家的忠诚,喜爱某个特定的领土,所有这些被看作民族特性的东西,都是没有关联的,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选择。个人是由他/她生于的民族(国家)决定的,更需强调一下,是被剥夺自由的。就个人层面来说,没有自由的需求,个人不是被看作自由的能动体。个人能够(事实上是应该)期盼的自由只能是摆脱外族控制的民族自由。因此,由族裔条件界定的民族性剥夺了个人构成个性的东西,消融了个人能动性,使得人民被说成群众成为逻辑必然。[11]
在建构主义看来,民族和民族认同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和个人主观选择是主要的一面。没有所谓不同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就是不同。“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通过差异形成的”。我们的身份认同具有“偶然性”、“模糊性”、“挑起争议性”和“被争议性”等等。[12] 在面对公民的族裔差异时,传统上主要有两个做法:分割或者压制(同化通常是在多多少少的强制下或压力下进行的),但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包容成为了最重要的选择。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处理族裔问题时曾写道:“包容差异是真正平等的核心”。[13] 本哈比布认为:“既然每一个认同的找寻都包含使自己区分于和自己不同的东西,认同政治就总是而且必然是制造差异的一种政治。”多重性的身份认同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而应被看作是一种“资源”,甚至应该保护“差异的权利”(the rights of difference),“庆贺差异性,尤其是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价值,鼓励差异性和把差异性作为一个正面的社会利好呈现出来”。[14]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也同样强调民族的“非天然性”和它的“文化根源”,尤其是统一语言的作用。但因为语言并不具有排他性,所以民族与民族之间并无内生性的、清晰的、凝固不变的分界线。安德森指出,“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都已证明是无比困难去界定的,更不要说去分析了。”[15] 在他看来,民族“就是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被想象得既是有限的,又是最高的”。这种“想象”表现在:第一,即便最小的民族人们也不可能认得大部份,但大家却想象生活在一个群体里;第二,无论再大的民族有10几亿人,也会认为有一个达到极限度的边界把自己与其他民族分开来,“没有民族想象自己与人类相毗连。”第三,民族梦想自己自由,这种自由的体现就是“主权国家”。[16] 因为这些想象,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者们时常被三个悖论所困惑:第一,历史学家眼中的“民族的客观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主观的民族远古性;第二,作为文化社会学范畴的民族性的普遍性(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犹如每个人都有性别一样)和其具体体现的特殊性;第三,各类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和他们的哲学贫乏。[17]
当今世界一个危险的趋势是出现了“返祖的观点,认定消除差异和他者就可以维护和安守自己的认同”。[18] 所谓“家园”的梦幻 反应的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千好万好没有自家好”。这种对家的渴望想要一个类似于家、“类似于母亲子宫”的世界,远离一个充满纷争的世界,那里没有“差异、冲突和困境,是一个有序的、受到欢迎的地方”。学者指出,其实,母亲怀的胎儿也只继承了一半母亲的染色体,胎儿和母亲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也是充满张力和对抗的,例如母体强烈的孕妊反应未尝不是母体对胎儿的排斥。所以,美国政治哲学家洪尼格(Bonnie Honig)指出:“家之梦是危险的,尤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因为它启动和恶化了被构建的主体或者说民族无法接受他们自己内部的差异和分歧,也滋生了狂热性和梦想着把同一或家变成现实的意志。它导致主体把自己内部的差异投射到外部的他者身上,然后对着他们发怒,因为他们在家园或其他地方挡住了自己的梦之路。”[19] 问题是,洪尼格还补充道:“当我们远离家时,我们更想要家。”但我们在家时,我们也是要更多的家,所以产生了无家可归、流放和异化等现象。她建议说:“自我形成为主体-公民的社会特性要求也产生了一种开放性,在与一系列(经常是不兼容的)团体、网络、论题、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在自己的家国或海外,不断重新商谈自己的边界和附属。”[20] 这种开放性恐怕对我们讨论西藏问题也极有价值。
甘地和达赖喇嘛:印度-佛教思想资源
就差异性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印度之上。种族(从黑色到棕色再到白色)、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佛教、犹太教等)、种姓制度、贫富/城乡/男女/沿海内陆差距、意识形态(民主政体下也有共产党在邦政府执政)造成印度差异的复杂性和爆炸性。为了把这种差异转化成印度的资源、骄傲和成就,同时避免差异促生种族屠杀的可能性、危害性,更重要的,还要重建一种团结四亿多人口的新认同,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思考和详细的对策。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印度作为第一个通过非暴力手段赢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尽管甘地百般努力试图维持印巴的统一,但即便没有联邦政府层面上的暴力行为或鼓励措施,印巴分治引发1200万的难民双向逃亡,导致100万人的死亡。[21] 在甘地看来,“所发生的一切–肆意谋杀、纵火、打家劫舍、绑架、强制改宗,人们还看到了更坏的:战争,在他看来,就是没有约束的野蛮行为。确实这样的事并非前所未有,但以前没有发展到全面的小区的歧视。这些事件的各种描述使得他充满伤心和耻辱。更让他感到耻辱的是,清真寺、教堂和锡克庙宇被夷为平地或破坏。当这种疯狂统治时,那就远离了自由。”[22]
而西藏在中共的统治下,经历了人口和文化的双重屠杀。对于屠杀的规模和范围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具有北京背景的学者估计只有3万藏人在大饥荒中死亡,而西方学者和流亡政府则估计,由于大饥荒、屠杀、战争、关押死亡和中印边界紧张导致边界关闭和边贸中断等多种因素,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前三十年,藏人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万,也可能100万,甚至150万。[23] 正如“死无对证”所言,而且中共对历史真相还在掩盖和扭曲,我们还无法知道最后的数据,但藏人在中共政权下的非正常死亡在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之间应该是客观的估计。目睹本民族遭受生灵涂炭和民族文化灭绝的威胁,西藏自由运动领袖达赖喇嘛也有深切感受和深度思考。总之,圣雄甘地和达赖喇嘛都是种族仇恨和屠杀的历史见证者,目睹自己族裔同胞被屠杀,他们的思考和教导就具有不同凡响的价值。达赖喇嘛自认为是“印度之子”、甘地的学生。尽管达赖喇嘛没有与甘地在历史上相见(坊间有人以良善愿望拼制出甘地与孩童达赖喇嘛的合照,而达赖喇嘛明确说过,“而圣雄甘地我虽不曾见到”[24]),但他明确表示,“我是甘地的追随者之一,我追随他无害行的信念。”[25] 我们可以看到从甘地思想到达赖喇嘛思想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继承关系。他们的智慧展现出了印度和佛教思想特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西方宗教和政治思想的相通,也可以发现独特的东方智慧以弥补西方政治思想的不足。如果古希腊诸神站在奥林匹斯山获得了天地贯通的奥林匹斯世界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可以说,甘地和达赖喇嘛占据了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天地人间的问题。
在2005年正值达赖喇嘛70寿辰,印度教育家萨提希•伊南达尔博士编辑出版了《圣雄甘地和尊者达赖喇嘛论非暴力和慈悲》(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信息和外交部出版)合集,为我们系统而简便地了解两位东方智者的思想提供了方便。[26] 因为许多的中文读者(尤其是大陆的中文读者)对圣雄甘地和尊者达赖喇嘛的思想并不熟悉,而一些藏人极端派可能也没有接触或忘记了甘地、甚至达赖喇嘛的教导,所以我把他们许多重要的思想翻译出来,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该书以一年365天来编排,所以没有标注页码,下面所有来自该书的引文就以日期来标注。)
甘地是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一生的,他最后为印度宗教团结、民族统一献出了生命。尽管遭遇暴力的镇压和威胁,甘地一直宣扬、坚守“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战略。甘地说:“我尽我所能研习了主要的现存宗教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如果适合且有必要找出所有宗教内在的统一,首先要找到一把万能钥匙。那把万能钥匙就是真理和非暴力。当我用这把钥匙打开一个宗教的宝柜后,我不难发现它与其他宗教的相似性。你看所有的宗教就像一棵树上的各式各样的叶子,但他们都在一棵树干上。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根本合一,否则,以宗教之名开战就不可避免。” (Jan. 21)
对甘地来说,统一而非分治是印度的最佳选择。但他一直无法克服穆斯林联盟分裂印度、建立巴基斯坦的主张。因为印巴分治,社群主义(communalism),尤其是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间在小区层面的冲突,成为印度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根源。甘地为他的追随者制定了《不合作运动誓词》,前面两项这样写道:“我自愿成为不合作运动积极分子。我庄严宣誓,只要我还是不合作运动的一份子,第一,我将在言语、行动上保守非暴力,并积极在意念上追求非暴力。我坚信如今天印度的形势所许,非暴力就能帮助实现完全独立的目标,并能促进印度所有族裔和小区的统一,不分印度教、穆斯林、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第二,我相信并会为这项统一奋斗终身。”(November 20)甘地曾这样向穆斯林呼吁:“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小区或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穆斯林的朋友和弟兄来讲话。作为一个非暴力之人,如果印度的穆斯林们坚持己见,我是无力来阻止分治建议的。但我决不会情愿参与这个肢解。我将动用每一个非暴力的手段去阻止它。因为它意味着废弃无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几个世纪努力作为一个国家生活在一起的工作。分治是明显的谎言。我的整个灵魂都会反对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代表两个对立的文化和教义。对我来说,同意这种看法无异于背叛神。我的整个灵魂都相信《可兰经》的神就是《薄伽梵音》的神。我们所有的人,无论以何名义都是同一神的子民。我强烈反对这一想法:几百万的印度教徒一夜之间要皈依伊斯兰、以此为自己的宗教。我拒绝相信八千万的穆斯林将会说他们和印度教的兄弟没有共同之处。我依然坚信,如果没有社群的统一而用暴力手段,我们就不会有独立。穆斯林们能够阻止通向和平自由之路。”甘地还说:“我追求的联盟不是一个拼凑出来的,而是心心相印的统一联盟,它建筑在完全承认下面无可争议的主张上:没有印度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牢不可破的联合,印度的独立自治就是不可能的梦想。这不能只是停火,也不能基于相互的恐惧。它必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相互尊重对方的宗教。”(April 13)尽管后来印巴不可避免分治,甘地也继续呼吁双方善待少数宗教教派:“有人说(印巴)分治的工作已经结束,军队已经被分割,海军也被分割。我要说我们被削弱了。这项分离将制造一场内战。外国人将与一方结盟对另一方。我希望巴基斯坦和印度将是朋友,他们都将善待他们的少数群体。”(Jan.19)甘地的担忧不幸成为历史事实: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印度教和伊斯兰),屠杀发生了,巴基斯坦走上了民主衰退、军事政变频繁、政局不稳、伊斯兰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化、外国趁机干预、经济长期停滞,尔后因为文化语言和地缘的差异巴基斯坦又不得不面临孟加拉国的独立,而每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都比原来的母国在政治上更动荡、更不民主,在经济上更落后、更少乐观希望。
“非暴力不合作 ”是甘地从英国追求独立的手段,“非暴力”也是他试图挽救印度统一的手段。在甘地看来,“哪里没有暴力,上帝就在那里。”(Jan.19)“非暴力不是一件弱者的武器。它是一件勇者的武器。它的巨大价值只有在被勇者拿起使用时才能测出。”(October 25)“我们绝不和这个世界的良善美好之物为敌。”(April 17)必然的,暴力为甘地所憎恶和遭唾弃:“非暴力是我们人类物种的法则,而暴力是畜生的法则。”(April 11)“剑之力也是兽之力。杀人并不需要智力。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智力误导去服务于兽之力;尽管有智力相助,兽之力依然是兽之力,刀剑的法则还依然是野兽的法则。”(June 10)“我呼吁的是放弃心里的暴力和积极行使此种放弃而产生的力量。我在弱者的消极抵抗和强者的积极非暴力抵抗之间作了区分。后者即便在最严厉的敌对牙齿间也能、也在发挥作用。但其目的还是要激发最广泛的公众同情。非暴力人士所受的磨难已被证明可以融化最坚硬的石头心肠。”(October 29)
非暴力对甘地如此重要,他把它看成印度本质的一部分,是印度伟大之所在: “我自豪地视印度为我的国家,因为我相信她向世界展示了灵魂力量的至上至尊。一旦印度接纳兽之力为最高,我将不再高兴称她为我的祖国。我的信仰是,我的大法不承认义务的范围有限度或有地理限制。我向神祈祷我会证明我的大法并不念顾自己,也不是只局限于一地。”(August 9)“如果不合作运动导致暴力,或不合作运动者寻求暴力;如果印度把暴力变成信条,而我还活着,我不会再生活在印度。她将不再激起我的自豪感。我的爱国主义服从于我的宗教。我对印度的依恋犹如婴孩对母亲乳房的情感,因为我感觉到她给予我的灵性滋养。我感到,她有一个环境对我的最高理想做出回应。当这种信念消失了,我就会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儿,永远无望再找到一个保护人。那时,喜马拉雅山雪中的孤独会给我流血的灵魂带来最后的慰藉。”(May 17)
达赖喇嘛和甘地一样面临自治自立、同时是否追求完全与中国分治独立的挑战,在追求前项目标、避免后项结果又如何发挥非暴力不合作的优势,避免暴力和由此带来的流血。作为一个藏人、一个僧人和一个有情众生的一份子,尊者达赖喇嘛特别强调自己有三大责任需要推进:“首先,我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都是一样的,可想而知‘人类的一体性’是很重要的,它会自然地减少我们彼此之间的敌意。我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们却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以‘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来看待彼此。使用武力不可能解决冲突,反而会制造更多的冲突;我们必须藉由对话来解决冲突。如果我们以‘人类的一体性’的认知为基础,促进和推动人类的爱心、慈心,我坚信世界会走向更和平,更安乐。其次,我是一个佛教徒,并承诺促进宗教和谐。尽管各宗教之间拥有不同的哲理差异,但所有主要宗教传统共同的教诲是爱、宽恕、包容和自律。 因此,我们在尊重所有的宗教哲理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推广所有宗教共同传递的讯息。第三,我是一个藏人。西藏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是一个和平、非暴力,以及慈悲的文化。是可以利益很多人,并值得保存的文化;同样,西藏的自然环境也应善加保护。一位中国生态学家判断青藏高原对于全球气候的影响等同于地球的南北两极,所以他把西藏称为‘第三极’。十几亿人口赖以维生的亚洲主要河流的源头在西藏,所以保护西藏的环境也非常重要。”[27]
达赖喇嘛的根本坚持是和他对差异的认识是有关的。达赖喇嘛指出: “事实上,自我和他者是相对的,犹如‘山的这边’和‘山的那边’。从我的角度,我是自我、你是他者;但从你的角度,你是自我、我是他者。我们天然地感到差异,因为我们以为他人的幸福和苦难不关我事。他们对我无意义。尽管我们的身体有无数部分:头、双手和双腿,我们看待我们的躯体,每部分结成的一体,都是宝贵的。同样地,所有的有情众生也像我们一样拥有共同特性,也很自然地希望趋乐避苦。”(December 31)他还指出: “在身体层面我们有不可避免的各种问题,在社会和家庭层面上我们也有。在我们自己人中也有意见的差异。这样的矛盾没有什么不对。这造就出思想观念上的运动和能量。事实上,矛盾是自然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处理矛盾以及我们是否能主动利用它们。我们的精神态度是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中坚持和平与善心,即便敌对的力量也不能打乱我们的阵脚。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条件或朋友,而是意识到真正的和平与满足。”(November25)
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当宗教成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主要根源时,达赖喇嘛非常关心心性的改进。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唯物主义知识的局限性。尽管它造就了人类福利,但不能造就永久幸福。为了复兴人类价值和获得永久幸福,我们需要重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人类遗产。人类价值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团结成一个家庭。”(June 11)他也积极推动宗教宽容和不同信仰的对话:“今天世界已变得更小,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沟通也变得很强。在此情形下,我认为各教派信徒的多元主义就很关键了。通过客观的、无偏狭的研习,一旦你看到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同宗教对人类的价值,那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接纳或尊重所有不同的宗教。独一的宗教不能满足大千世界的众人。”(December 3)
从人类各种差异中,达赖喇嘛认为慈悲是我们的共同点,博爱是化解分歧和冲突的基础。达赖喇嘛说:“我相信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家庭、国家和国际,通向更幸福和更成功的世界关键在于慈悲的培育。我们不必皈依一个宗教,也无需信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我们所需的一切就是开发我们良善的人类特质。我认为,个人幸福的培育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改进是极好而有效的办法。我们对爱有共同需求。在这个共同点上,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可能是一个弟兄或姊妹。着眼于外部的差异是不智的。我们的基本本性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人类归一,这个小小的星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假如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敏锐经历普世的利他主义和慈悲的感觉。如果你有一个开放的心,你就没有必要惧怕他人。”他的这种思想也可以延伸到国家层面。他说:“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开放的、合作的气氛已经变得更为急迫。处理经济问题时,国家边界已不复存在,世界已经无法改变地连在一起了。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最终会导致自己国家的经济改进。观察现代世界的现状,我们的思想和习惯都需要一个全面革命。与日俱增已经越来越明显,一个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必须建筑在真正的全球责任感上。这不只是一个神圣的、道义的或宗教的理想。这是我们现代人类生存的现实。”(April 10) 他还说:“基于现存的国际情形,合作是必须的,尤其在经济等领域。国际差异至上的想法已经被欧洲走向统一等例子削弱了。欧洲的举措太神奇了。国家间密切工作并非源自慈悲,而是发自必需。世界有了走向全球意识的趋势。在现存条件下,与他人更紧密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生存本身的必要元素。因此,基于慈悲的全球责任成为一个基本概念。世界充满着各种冲突,原因有多种,甚至在我们自身。但在我们明白所有这些冲突根源之前,我们有这个潜能一起共建和谐。所有的原因都是相对的。尽管我们有许多冲突的缘由,但我们同时也有许多团结和和谐的缘由。”(June 9)
基于慈悲精神,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天下人类一家和共同的人性。无我和利他,消除憎恨,合作和非暴力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达赖喇嘛说: “认识到人类一体在当今世界尤其重要。新现实是,我们邻居的毁灭就是我们的毁灭。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October 28)所以,“憎恨和纷争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幸福,甚至不能给战斗的胜利者。暴力滋生苦难,总是得不偿失。所以时候已到,全世界要学会超越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造就的各种差异,透过双眼看见共同的人类处境来看待对方。如此必将利于个人、小区、民族和全世界。”(March 13)“随着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已经前所未有,人类理智必须超越国家疆界,拥抱广阔的国际共同体。除非我们不用威胁或武力,而是通过诚心的理解营造出真正的合作气氛,不然世界的诸多问题只会增加。”
对于小民族,达赖喇嘛尤其关心:“针对每一个小区或民族,个人应该给予幸福的权利;众多民族中即使最小的也应该有福利上的平等考虑。我不认为一种制度比另一种好,所有的人都应该采纳。相反,多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更可取,以适应于人类共同体里多种气质秉性。这种多样性促进人类不停地追求幸福。所以,基于自决和慈悲的原则,每一个小区应该自由演进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 即便对于敌人,达赖喇嘛也告诫:“我们对家人和朋友的热爱和情感,通常表达形式是和依恋混在一起的。那不是一种真正的慈悲。即便对我们的敌人我们也需要有真正的关心,因为他们也是人类,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有平等的幸福权利。”(July 29)
达赖喇嘛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当然看到了我们现今世界的问题,但他并不悲观:“我们如何处理困难的局面?我们掌控的能量不仅来自慈悲的态度,也来自理智和耐心。尽管这些是最有效的方剂,有些人却把他们误解为怯弱的表现。我认为它们是真正内心力量的表现。本性上,慈悲就是轻柔、平和、柔软的,但它也强大无比。那些轻易失去耐心的人才是没有安全感和不稳定的。因此对我来说,愤怒升腾通常是怯弱的直接表现。到头来对手的破坏性的能量只会伤害他们自己。与其去报复,不如管好自己的欲望、行使慈悲、尽力帮助他人逃离折磨。愤怒滋生的报复很少能达到目的。”(November 5)他告诫经受失望的人如何不要盲目急躁:“确实我发现,大量我们称之为的内在折磨可以归咎于我们想快速求得幸福。没有明白情形,我们急于去走许诺满足的快捷方式。这样做实际上堵住了我们长期的完满。当我们去满足一时之需而没有考虑他人的利益,我们就打消了持久幸福的可能性。” (August 20)“此时此刻,就个别国家或国际共同体里的国家之间,世界情形是不公正的。在藏人之间有个说法,‘如果九项努力都失败了,那就试第十项。’至少现在还有人愿意营造一个公平的世界,并直面当下的失败和挫折。我们不得不这样。”(October 26)
面对不公平的世界和复杂的矛盾,达赖喇嘛推崇对话的解决方法:“我们如何能在二十一世纪减少暴力和破坏?我们如何可以不用暴力反应的方式来制止冲突?我感到在和解精神下应该引入对话方法。当我们在推动和平时,我们也必须推广对话的精神。它应被引入学校教育,所以孩子们就会自然以这样的态度应对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我认为,用武力是不文明的、落后的解决冲突的方式。”(October 28)他还说: “今天,我们的生存和福祉是与无数他人合作或有他们贡献的结果。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与他人的关系。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国家的疆界变得无足轻重。我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人造的。所有出自民族主义和国家边界的冲突、流血等问题都是人造的。如果我们从太空看世界,我们不会看到任何国家边界的划分。一旦我们在沙上画条线,我们就生出了‘我们’与‘他们’的感觉。一旦这种感觉增生,我们就更难看清事情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很简单:去伤害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受伤。在过去,国家、甚至村庄在经济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敌人的毁灭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胜利。战争已是过时的概念,我们必须通过对话来面对我们的分歧。对话是唯一妥当办法。暴力的概念已不再适合。我认为,非暴力是恰当的办法。”(November 11)
达赖喇嘛曾总结他的理想:“我有一个实现幸福的想法:内心平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的三结合。有必要培养全球责任感和对所有有情众生的深切尊重。”(November 7)如果我们能够践行这些理想,暴力将变为多余,军队也能被废弃。他说: “军队是人权的最大破坏者。牺牲生命也把士兵的权利剥夺了。一个强大的军队破坏的是自己国家的幸福。如果我们知道专制是可恶且具有破坏性的政府形式,我们就必须承认强大的军队建制是其中一个重要根源。不仅军队昂贵,而且也浪费了宝贵的人类能量。”(March15)如果有一天西藏能够获得自治,他倡议,“西藏应该是一个彻底的非军事化地区。”(July 9)
面对追求自由道路的艰辛而又有少数热血容易沸腾的狂热主义者,达赖喇嘛告诫道: “在漠视和狂热之间最好行中道。”(Jan.18)这也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宗教、哲学和认识论的大背景。基于他的慈悲思想和他的人类一家、族裔/宗教和谐的主张,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向汉人提出了双赢共存的和解方案:中间道路——即在不寻求西藏独立和完整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实现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
达赖喇嘛的思想资源是无穷无尽、异常丰富的。在其他上百本各种著述和众多经解中,达赖喇嘛都系统阐述了他的宗教观、哲学观、政治主张和汉藏和解的建议。上面引述的只是沧海一粟,法国作家索非亚•斯特里尔-雷维尔(Sophia Stril-Rever)编辑的《达赖喇嘛:我的精神自传——个人反思、讲道和访谈》又是另一部精心串珠而结成的合集。我在这部著作中敬称达赖喇嘛为“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就是因为他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思想有坚实的哲学和宗教学的基础作为基石。而这一基石一边架构在佛教的千年理论上,另一边又架构在古老的印度哲学和文明之上,尤其是达赖喇嘛非常强调的“那烂陀传承”。“菩提心”、“缘起”、“因果”、“无害行”、“我执”、“自性空”、“无自性”等佛教的核心理论,“众生平等”、“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谦卑自处”、“忍辱精进”等修持方法,成为达赖喇嘛这个比丘政治哲学的根本素材。依据理性思考和实证探索,他对民族、国家、敌人、差异、灾难、人类共同体、世界和平等见解主张都自然地从此流出。[28] 但在这里论述政治问题,我想特别强调下面三部著作的重要性:《新千禧年伦理》(1999年)、《众信仰迈向真正亲密关系:世界各宗教如何走到一起》(2000年)和《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201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构成了达赖喇嘛伦理思想三部曲:从缘起和不忍心引申出慈悲和博爱的普世伦理,从爱看到所有宗教的共同性因而构建众信仰的亲和,然后超越宗教并在世俗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世俗化的世界伦理观。在《新千禧年伦理》一书里,达赖喇嘛提出“心性革命”,从“缘起见”讲到我们就能避免“把事务事情看作凝固、独立和不相干的存在”,防止“用黑白极端”来看“复杂的相互连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利益也是无可更改的紧密相连,我们必须接受伦理观来调节我寻求幸福的欲望与你的欲望。”[29]他认为,在教育中灌输丑化历史上的他者、培育偏狭和种族主义都应终止:“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的国家’、‘你的国家’,‘我的宗教’、‘你的宗教’的区别是次要的考虑。相反,我们必须坚持遵守我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不比他人的同样权利更重要。这不是说我们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抛弃或忽略我们生长其中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恰恰相反,他们根植于这些传统很重要。学习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宗教、文化等等对他们是有益的。但危险在于这经常走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族裔中心观和宗教偏执。”[30] 达赖喇嘛从国际组织、区域贸易合作和邦联体系,尤其是欧洲联盟看到“人类为了共同目标联合在一起的冲动”和“人类社会持续的演进”:“起初较小的部落单位通过城邦的基础进步到民族国家,现在进步到容纳上亿人的联盟,逐渐超越了地域、文化和族裔的分割。我相信,这一趋势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下去。”[31]
在《众信仰迈向真正亲密关系》一书中,达赖喇嘛表达了他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各宗教的宽容团结和多元共存。其面临的重要挑战来自原教旨主义。达赖喇嘛是这样认识这一现象的:“概而言之,原教旨主义者们,不管出自哪一个具体的宗教派别,倾向于认为无德和非神的价值充斥现世,笃信者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类社会带回到按照神的道德律令运转的黄金时节。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原教旨主义者总体上坚定认为,他们的圣典包括全部所有值得通晓的真理,面对多元主义和世俗化的进犯因而使得真理相对化,他们有责任捍卫自己圣典里的真理。原教旨主义一个重要点是,捍卫典籍字面上的真理和维护其一尊地位。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以他们所理解的神显示的律令是绝对的、超时空的和没有商量余地的。”[32] 达赖喇嘛提出了我们的责任来超越差异、实现和平共处。他这样告诫道:“当我们看另一个人时,让我们首先感到亲和。在这个世界没有陌生人。普天之下皆是人生旅途上的兄弟、姐妹。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的暂时过客。顶多我们的生命也就是百岁,与我们共享的星球高龄相比,不过是一剎那、一口气。如果我们纠缠于纷争和强化不合,如此荒废我们短暂的人生是非常无聊的。”[33]
在《超越宗教》一书中,达赖喇嘛提出了“世俗主义的普世伦理”。所谓的“世俗主义”是从印度传统来理解的,它不是要放弃或敌视宗教,而是包容所有宗教、甚至无神论。即便不用宗教基础,基于人类的天性(从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母爱),我们也可以建立世俗的普世的慈悲,并用世俗的慈悲培训方法提升人们的慈悲能力和逐渐从家人、朋友扩张到更大社会范围、直至全人类的关爱。在达赖喇嘛看来,我们的动心发念和言行举止都应该建立在“我们全人类”的身份认同之上。“不管有多种特征,例如种族、语言、宗教、性别、财富等等,把我们区分开来,就根本的人性来说我们是平等的。”事实上基因生物学揭示,我们人类共享绝大多数基因染色体,在这个层面,“个人间的差异可能超过不同族裔间的差异”。[34] 修心的目的就是要培育人类普世的、宝贵的价值观:善良、慈悲、原谅、耐心和个人品德,同时管理、控制和消除负面情绪,尤其是贪嗔、嫉妒和愤怒,以实现内心的满足和平和。达赖喇嘛指出:“慈悲减少我们自己的忧虑、提升我们的自信、给我们带来内力。通过减少隔阂,我们向他人敞开,感到与他人连在一起,从而获得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慈悲也使得我们从自身的困境和烦恼解脱出来。”[35] 特别针对藏汉问题,达赖喇嘛提出了如下见解:“尽管我们藏人经受巨大磨难,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努力避免落入敌视和报复的倾斜。即便对于中共参与暴行伤害藏人的士兵们,我们也试图保持慈悲。……避免纠结于过去经历的不义、有意识地努力培育对我们汉人兄弟姊妹的慈悲心,我们藏人就可以避免停留于过去,才能保有自由的意识。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放弃立场、不再坚定地反对我们面临的不公。”[36]
从汉人的角度观察,达赖喇嘛代表藏人向汉人表达慈悲,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时机来消解汉藏积怨,汉人可以据此纠正历史错误,同时为解决与其他族裔的冲突提供范本。达赖喇嘛说,“每一个个人都有能力贡献出慈悲的非暴力。我们可以从家里开始,然后上升到国家和国际层面。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人类社会的一部份,像是一个人体的不同部份。”(November 15)其实在中华文化传统里,孔子(公元前551-479)早就提出过中国人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公元前372-289)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怵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与1759年亚当•斯密发表《道德情操论》提出“同情心”作为西方现代伦理相比,早了整整两千年)。墨子(公元前468-376)更是提出三个层面的普世法则:个人行为的“兼爱”、国家关系的“非攻”和超越层面的“天志”。中国传统思想和佛陀、甘地和达赖喇嘛倡导的“菩提心”、“非暴力”和“慈悲心”都可以完美对接。
讨论西藏问题的认知误区
讨论西藏和其与中国的关系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西藏和中国是否存在在一个政体下?如果是,是分裂还是营造一个自由的、公平的统一?个人自决和民族自决的关系是什么?民族自决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独立和建立一对一的“民族国家”?在西藏完全独立和维持中国的“大一统”之外,是否有更好的、对西藏和汉人、甚至所有的中国境内的居民的最佳选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讨论西藏,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中国-西藏”(或西藏-中国)的二分法:似乎中国和西藏各自都有明确和清晰的定义、内涵和边界,二者似乎是一种平等、独立和对抗的关系。继而我们经常听到“西藏独立”和西藏行使民族自决权建立民族国家等说法。然后,我们也经常听到“汉人”和“中国人”似乎可以互换并用,中国人似乎是一个匀质的民族概念,完全以汉人为核心。最后,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听到从藏人角度对中国人的控诉,好像西藏的悲剧都可以从汉人(或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姑且把二者混用)找到充要和必要的原因(一种单因论)。下面我就要从概念出发,论证这些概念和认识的简单片面性,指出它们蕴含的狂热主义和偏激立场的果因。
汉人、藏人、维族和其他穆斯林、蒙古人、满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50个少数民族族裔共同生活在一个政体下,这应该是一个不含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女权民主理论家艾丽丝•杨(Iris Marion Young)认为,如果不同的人群/集团要生活在一起,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生活下的政体,其次是要有自由民主层面上的更高团结。她说,“驱动政治的统一是人们被抛进在一起的事实,大家发现自己在一个地域比邻、经济相互依存,以致某些人的活动和追求会影响其他人从事他们活动的能力。一个政体是由居住在一起的人构成,大家挤在了一起。”[37] 一方面,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难以采取鸵鸟政策,幻化掉已经存在了七十年的一个政体;但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或人群的不满也不能被霸权族裔视而不见、粉饰和谐太平。杨指出,比一个政体更高的、更紧密的团结需要尊重多元、理解分歧、平等交流的协商型民主制。“如果人们不生活在同一个政体下,处境不同的各个集团就没有理由或架构来在民主协商中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种统一当然是民主沟通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一个政体要变成一个协商型的民主制,它还需要更多的统一。所有的成员都必须承诺,相互平等尊重,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就是愿意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表达意见和各自观点的权利,大家都应倾听。而且,政体的成员必须就公平讨论和决策的程序原则达成共识。这三个条件:实质性的相互依存、正规形式的平等尊重、共同认可的程序,是协商型民主制需要的全部统一。”[38] 具体到藏汉关系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华人民在共和国中的地位,汉藏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了实质性的程度。不平等还存在,民主程序和制度还没有建立。汉藏两个族群的首要任务到底是要拆散现有的共同体,还是转型政体,亦即,从专制的、缺乏公民权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平等公民权的政体转型进入建立和保障公民权、因而差异和多元成为资源的民主制?达赖喇嘛的详细论述以及他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显然是要实现后一个方略。但在藏汉两边我们都听到了人数少、但音量大的前一类主张:解体中国、藏汉分治。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径:第一,民主化和公民权会造就一个民主中国,从而赋予所有族群/集团平等权利,通过协商型的民主建立更紧密、更广泛的多族裔、甚至跨国的团结;第二,通过追求民族区域自决独立获得民族分家,从而各民族有更好的民主发展空间和机会。哪一条是活路,哪一条是死路,我们可以在公共理性讨论中得到答案。
我们先从“民族”的概念说起。中国学术界基本采纳了斯大林对民族所做的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9] 从这一本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概念出发,显而易见,藏族和汉族不是同一个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看起来一个很平常的描述却充满情绪化的争论和生死攸关的冲突。历史学家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一书中探讨了这一历史。根据他的研究,最早发现的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40] 以后在《尚书》中,“中国”又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又叫中原一带,大约有50万平方公里。[41] 到北宋时期石介写“古代中国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中国论》时,中国在北方辽国、西北西夏、西面吐蕃诸部和南面大理国的挤压下,覆盖的领土范围大概北从石家庄、西至兰州、南下到成都最后靠南宁入海。在石介看来,“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他还说:“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42] 文明与否,而这里的文明又主要是指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成为华夷之辨的基本标准。有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因为蒙古帝国南下征服了南宋,以游牧文明为基础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认为的中国文明以同心圆的方式通过教化蛮夷不断向外扩张的模式。蒙古帝国以征服者的姿态把中国和周边的“四夷”打通连接起来,尽管蒙古帝国后来灭亡,但它与中国的嫁接却留下了永远的帝国版图作为嫁妆。又有人说,“明亡之后无华夏”,因为老陈的华夏文化在明朝暮气沉沉,最后被女真人建立的满洲帝国征服,“汉人的中国”再次被砸烂重构。
但我要指出, “崖山之后无中国”、 “明亡之后无华夏”在今天看来都是误导人思维的。它们的错误主要基于一个族裔中心论的、凝固的华夏历史观。正如前面已经指出,“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性的地理概念,“中心”是相对于“边缘”而来的,其地理思想基础就是天圆地方、地平说。后来地圆学说的证实和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流碰撞使得地理的、文化的、族裔的中心论都站不住脚。在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以华化夷”、中心逐渐向外扩张而形成的同心圆扩张的历史过程这一论述,其实也只看到了华夏民族文明创造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华夏中原文明只是文明互动关系的一方,在挑战-应战、征服-失败、贸易文化的平等交流的关系(或经常是关系网)中,总还有另外的主体、能动者或文明的助推力量。如果我们尊重“人类非洲走出说”、超级大陆漂移说,再看看所谓以帝都或京城为象征的文明中心包括东面的杭州(临安)、南京,西面的西安、洛阳、开封(汴京)、成都,北面的大都、北京和盛京(沈阳,清朝的陪都),他们覆盖的范围就已超出了宋以前的“中国”范围,更不要说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变化扩张就更大了。而“中国”的这种扩张并非中原单向对外发散的结果,经常是周边(尤其是北方和西北方)民族吞并、消化、重组“中国”的结果。在动态的、循环的历史思维里,“中国”就是一个有伸有缩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一个多族裔、多民族逐鹿中原的历史大舞台。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二战爆发前),林语堂在《中国人》(又译《吾土吾民》)一书中写道:“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和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是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43] 林语堂还总结道:“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44] 而这种种族融合,尤其是北方血统和南方血统的混合,外来新血统的混入,“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是过去两千多年历史上“每隔八百年”便会出现的“周期性的民族更新”。[45]林语堂引用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的研究说明,“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始皇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 其间约780年;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46] 在最后一个周期,我们不仅看到满族清帝国的入侵、日本人、俄国人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更重要的是马列主义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以“黄俄”方式入侵。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从三国、西晋和东晋16国到隋唐统一,从五代十国再到元明清,历史展现的不仅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逻辑,也呈现出动态的、多元的、多线条的历史观。蒙古人、满人两次相对于汉族来说都是异族的入侵,但“中国”这个地理概念却得到了最大的扩展。从来就没有一个从炎黄子孙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黄帝的后代、龙的传人,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万事一系的正统,也从来没有匀质的汉民族作为主人或主体民族主宰一部在所谓中国这片土地上演绎的历史。[47] 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个历史舞台,它的地理空间、历史大戏的英雄、编剧、导演和主角,甚至群众角色都发生了各种转换、打断、平行、融合、消失。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称自己为这一个中国时空的天然主人或独享导演,如果在此时空有所谓的少数民族,那也只是数量意义上的,而不是权力和权利意义上的。立足当下,所谓的汉人也曾经多次是征服者,也多次是被征服者,在过去八百多年的历史期间(以1221蒙古征服南宋算起),就有一半的时间汉人是被屠杀、蹂躏、奴役的人群。在蒙古帝国下,汉人(南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儒家文人更是排在“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末。[48] 僧人地位的隆重(他们也免于赋税)也反映出蒙、藏在所谓中国的变异过程中的作用。汉民族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政治劣势,成吉思汗、忽必烈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塑造者(成吉思汗的基因也是人类历史上传播最广的第一人)。而清王朝满人对中国人的塑造和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讲的普通话(汉语)其实是深受满人影响,所以英文里叫“Mandarin”(也就是满大人官话的意思),而女性以为是民族服装的旗袍也是从满族旗人的服装来的。继续以汉语为例,在历史上汉语文字至少受到三次外来的冲击和充实:佛教用语(例如“剎那”、“阎王”、“造孽”等等)、日语(例如“民族”、“社会”、“科学”等,1982年出版的《汉字外来语词典》,收录了约一万个外来词,其中日制汉语词汇有896个)、西洋外语(“摩托”、“引擎”、“巧克力”等等)。佛教对汉地的又一影响是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以致后来的“儒释道回耶”的五教合一。
鞑靼人(包括突厥族各部落,和今天的新疆地区或东突地区的族裔有关)、蒙古人、满族人和藏人都有对中原地区的入侵。尽管藏人从未在中原建立王朝,但在七、八世纪吐蕃帝国兴起,不仅频繁与唐朝发生冲突,蚕食汉地,在640年逼唐朝嫁文成公主和亲,在763年吐蕃军队击败唐军,赶走唐代皇,占领都城长安,并扶持李承宏(金城公主的弟弟)称皇。唐朝和吐蕃王国的恩恩怨怨持续百年。[49] 更为重要的是,在蒙古帝国元和满族清帝国下,藏传佛教都是异族帝国治理汉人的统治工具,或者说,藏传佛教和它的僧侣系统跻身入两个帝国的上层建筑,成为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0] 西藏和元帝国的紧密关系可以从两地的“供施关系”和藏传佛教掌管汉地佛教事务为例证。在清朝帝国鼎盛时期,被称为“亚洲腹地”的四个地区,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均由清军戍守”。“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1800年后,中心开始转向中国的本土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19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51] 藏传佛教因为也是蒙古人和满清所接受的,清帝是藏传佛教的保护人,藏传佛教对晚清和满洲国的影响,可以在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1987年)历史巨片中直观感受到:喇嘛僧人在溥仪入宫、慈禧驾崩和溥仪做满洲国皇帝祭祀大典上都可以看到。因为溥仪的弟弟溥杰、帮助溥仪完成《我的前半生》的李文达、郭布罗•润麒(末代皇后婉容之弟)和爱新觉罗•毓瞻(末代恭亲王)都是该片的历史顾问,所以其历史细节还是可信(历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对喇嘛出场等细节评价为“符合历史的”)[52]。与中国官方历史学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蒙古帝国(及其元帝国)和中国是等同概念,满清帝国和中国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西藏通过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同中国发生的关系,并不能以历史论证来证明西藏在元和清两个帝国时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高兴还是不高兴,因而撇开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历史事实:蒙古、西藏、新疆、满洲和中国被扔进了一个共同体之中(蒙古帝国、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这种共同体是以暴力、屠杀、征服和奴役为手段圆成的,在某个时期也是以某一个或多个民族(甚至是以汉民族的被屠杀和奴役)的独立为代价的。“我们被扔进一起”(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谓的“being ‘thrown’ into existence”[53]),其实这既是个人存在的荒谬现实,也是民族和国家存在的荒谬现实。
对待这一段多民族纷争共存的历史,我们时常看到两个偏执:第一是“不可避免代价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张艺谋在《英雄》的电影里歌颂的“为了天下苍生而杀戮建和平”的思想是一贯的。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和他的合作者论述清王朝入关建立统一国家后,“迅即着手于边疆事务”,促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高潮”。他们这样写道:“疆域的开拓,各民族文化壁垒的破除,总是伴随着流血与苦难。清廷征回疆,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准噶尔部原有六十多万人口,十分之三死于屠刀之下,染疫而死的又有十分之四,天山北路一片荒凉;清廷改土归流,为平定苗民反抗,烧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座,屠戮苗民达一万七千余人。但是,这巨大的苦痛,却是历史文化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中华文化系统内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次高潮便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历史运动中出现了。”[54] 这种对历史灾难的轻易接受,反映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一方面它无助于我们反思历史的罪错,从而防止类似的悲剧在未来重演;另一方面,它在把蒙古帝国和满洲帝国纳入中国王朝体系代际发展而变成元朝和清朝时(不是“亡国”,而只是“易朝”),也剥夺了蒙古人、满族人作为多元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定位;汉人官修历史和汉人历史学家一旦把所有的非汉族建立的帝国“接管过来”,也就把所有的历史包袱继承下来,结果强化了在今天中国境内的非汉族裔的“被牺牲者”意识,也造成了部分汉人形成的“加害者”的历史认同和愧疚的心理负担,甚至罪恶感。
第二是“不公正历史无效论”。当汉人(尤其是近代以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代政权)给自己加封“历史的主人”的时候,非汉族的少数族裔也容易接受和强化自己“被征服者”、“被奴役者”、“被牺牲者”的自我暗示。汉人和边疆地区的历史互动就成为了一部非正义的、不公正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在此,我并无意否认汉民族作为最大的族群,并非如官方所修历史所言是“爱好和平、不对外侵略的”。除了我们已经讨论到的满族、藏族、维族和蒙古族的苦难外,2007年我在湖南的湘西吉首苗乡参观过一个民间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得到的结论就是:一旦汉人爆增而又引进了玉米、红薯和土豆以后,汉人就和少数民族族裔发生冲突以争夺土地。苗族先是从坝子被赶到丘陵,而后又被赶上山,最后被赶上树。以致苗族开始了向南的大迁移,扩展到今天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地(那里的Hmong People)。但我要强调的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的互动,尤其在小区层面上,大多数时间是和平和互利的。古代历史进化到近代,近代历史接受了现代化。部分西方学者构建了“西藏作为香格里拉思维模式”,把西藏呈现为一片神秘的净土;[55] 部分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华人也有极度浪漫化藏人的倾向,似乎贪婪、狡诈、仇视和犯罪和藏人都无缘;他们中的部分人又和藏人中的极少数狂热主义者合流,彻底妖魔化汉人、汉文化甚至中国。例如,有人直言,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藏人与共产党政权的矛盾冲突(所谓的“共藏冲突”),而完全是“汉藏冲突”,因此,有人提出西藏独立、切除藏文化中的汉人元素,用共产党的党文化来概括和本质化千年的汉文化。和后殖民主义下殖民地与宗主国”西方-反西方”的关系有相似处,藏-汉关系也没有完全摆脱阿玛塔亚•森所说的“被殖民心态的辩证法”:倾慕和不满会同时存在。[56]
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揭示的,历史上许多文明死亡了、消失了,许多文明合流了、发展了。没有一个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享有在一个地理空间一直生存的特权。如果文明不再具有活力和再生能力,其消失和死亡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很难选择历史的某一个节点来宣称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历史有参照价值,因此可以帮助我们当下创造历史时更有公正意识;但历史只能在当下和未来创造。诚然,我们无法认可中共的宣传,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内涵有不同界定,争论分歧在所难免;但我们也同样难以认定,“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且不说西藏早已参与了在今天中国时空里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帝国和满清帝国的有机部分,尽管当时主权观念还未进入东亚,所以很难界定主权意义及其归属。但1950年以后,西藏丧失了主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理下的一部分却是历史事实。在过去500年的国家关系史上,很不幸,“权力即公理”基本是一条国际准则,到21世纪还未彻底走出来。西藏悲剧的形成就有这个历史大背景:英帝国(以及后来独立的印度)、俄国、三届中国政府(大清政府、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做出了阻止或漠视西藏追求全面主权独立的事情。[57] 在理想层面上,我们可以谴责历史的诸多不平之事,但在现实政治政策选择和社会运动策略上,我们还必须依赖权力的变化(中国国内和世界格局)来矫正历史的不公。
从近代以后汉民族的角度观察,“民族”的概念在19世纪引入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在满清王朝统治下,所以,民族的概念是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日趋明晰的,而且首先提出“中国民族”概念的梁启超,至少在1898年当时,是把它和“汉族”对等的、与满族对立的。1902年梁启超写道:“民族主义者,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58] 在中文早期使用中,民族包含了血统因素。但后来,“中华民族”又有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的。章太炎写道:“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59] 似乎地域、血统和文化都可以成为界定民族认同的标准。但中国学者所强调的文化仍然以汉文化为主,又没能摆脱族群和地域的限制。不幸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都犯下了相同的错误:以本质主义的民族观来对待少数民族族裔,出现族裔关系的不平等,甚至实行以小吃大的种族融合。
被国共两党都尊为“国父”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在他的众多演说中谈及,“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因为自秦汉以来,“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60] “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在“自然力”里面,孙中山强调的是“血统”:“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另外四个力量是“谋生方法”、“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孙中山提到强调“亡国灭种”的危险,并提到元朝和清朝就是“亡国”的例子,但中国同化了这两个少数民族,所以没有经历“灭种”。但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可能有这种风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口号,但后来中华民国并不愿放弃满洲大片领土,但“大汉族主义”也并未被放弃,所以在单一的“国族主义”之下,国民党和蒋介石试图把少数民族最后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概念中,或者是一种“五族共和的大一统”。[61]
中华民国的统一不仅遭到不同族裔的抵制和挑战,例如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都曾宣布独立或独立建国,最大的挑战还来自于日本人的入侵和中国共产党的颠覆。中共乐意混水摸鱼,借花献佛,所以多次公开在它的政策声明和未来建国理念中谴责国民党反动的“民族压迫”和“大汉族主义”,重申支持“民族自决权利”。不仅西藏、新疆、蒙古这些地区,连青海、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苗族、瑶族、彝族都得到了共产党允诺的“民族自决权”。中共许诺在一个“联邦制下”,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自由退出或加入,享受与汉民族的完全平等。[62] 历史证明,“民族自决权”只是共产党用来给国民党添乱、建立统一战线、最后夺权的工具,和动员受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手段。在共产党建政后的十年时间里,反对“大汉族主义”很快就转移到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强制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引发了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和傣族的大规模外逃。文化大革命更是制造了众多冤案和屠杀,民族关系紧张加剧。在经过1980年代的宽松调整以后,1990年代中共的维稳治国发展到21世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幌子下,中共实行了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不仅激化了与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矛盾,也刺激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离心倾向,台独的老话题又加上了香港民族党提出的香港独立或建立城邦国家。
当今中国面临着至少十种以上的分裂主义挑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海两岸同时存在了六十年,而台湾的本土意识不断强化,为这一族群认同代言的民进党已经三次赢得总统大选,台湾从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变成法理上的独立国家的机率日增。具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认为,大陆奉行的“大中华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加“民族主义”,对台湾和其他国家都形成威胁。他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权分治”,“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和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63] 在香港的“一国两制”逐渐被空化,出现了“香港大陆化”甚至“共产化”以后,香港的城邦自治口号提了出来,2016年陈浩天成立香港民族党,号召反对大陆对香港的殖民、主张香港独立。此外,大陆和海外还出现了“西藏自由运动”、“东突运动”、南内蒙古独立运动、上海民族党(沪民党)、河南的“豫民党”、“巴蜀建国运动”。来自大陆、侨居美国的政论作家刘仲敬更是全面反对中华民族概念和大一统格局,主张构建“诸夏各民族”,从而解构中华民族和汉族。他的“诸夏复国伦”可以分割出至少下列的国家:满洲国、晋国、齐国、江淮尼亚、荆楚利亚、巴蜀利亚、夜郎国、湖湘尼亚、赣尼士兰、吴越尼亚、闽国、坎通尼亚、桂尼士兰、大不列滇,等等。刘仲敬还号召大家积极跟随、争做“国父”。[64] 我个人认识的一位严肃的民主运动人士王清营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人需要被分裂300个国,殖民300年不如分裂300国。分裂权才是第一大人权!没有分裂权,任何其他人权都不存在了!没有分裂权就始终是奴隶。”后来他又写道:“中共、中国人、中国文化是同一个东西。是一个整体。所以,灭中共,必先解体中国,解体汉族,消灭汉族。”最后,消灭汉语又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实际手段。看来绝望文化和狂热主义是西藏自由激进运动和中国民主激进运动的共同精神分裂症候。
随着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殖民,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输入到了世界各地。这些概念的内在矛盾也困扰着前现代化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理想,即每一个民族都应有与此对应的主权国家,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纷争和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和民族主义有关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山权威汉斯•科亨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民族主义时代的结果和高潮”。[65] 世界上少有国家像日本和朝鲜/韩国那样具有民族的高度同构型,因此,日本大和民族和日本国、朝鲜族和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不幸的是他们也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具有几乎是完美的吻合。事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多个民族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下(例如中国、印度、俄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即便瑞士、阿尔巴尼亚、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都避免不了多民族共存),或者一个民族生活在多个国家主权下(库尔德人、蒙古人、德意志民族等)。从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后,世界进入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时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收尾,全球性的民族国家高潮过去了。但随着苏联、南斯拉夫和一些专制体系的崩溃(印度尼西亚、衣索比亚、苏丹等),又有一些民族国家建立,尤其是在中亚的前苏联的几个“斯坦”国的独立,给中国境内的分裂力量以新的想象力和意志力。
所以,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还继续讨论着各民族在中国的命运,独立或统一和民主化及民主的关系。这里涉及个人自由、国家民主、世界多元、经济发达等多重因素。总之,汉民族不总是祸害别人,蒙古人、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也曾是数以百万计。打一个不太妥当的比喻: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口已成一锅汤(也许调成了一碗色拉更合适),成吉思汗、忽必烈、努尔哈赤、康熙、乾隆恐怕是中国这锅汤的最大厨师,他们撒的盐、加的料不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少。汤做成了,如何还原成白菜、萝卜、牛肉、土豆?当我们把一个水族馆里的生猛海鲜变成各种海味美食,恐怕还不太难;但要把一桌的海鲜变回水族馆就具有挑战性了。这两个过程可能都是悲剧性的,而前者也许还有功利目的,后者更是唐吉诃德的征战,所以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和讨论。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不仅对汉人有利,对其他民族也有利。毕竟汉人占到90%以上的总人口,而非汉人民族若以少数民族地区来计算占领土的64.3%。[66] 甚至在内蒙古汉蒙人口比例达到8:1,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人口只占1/3。[67] 在中国的藏人总人口大约是641万(2010年数据,现在可能接近七百万)[68],其中二百多万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其他大部分分布在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的藏区(藏人习惯所说的安多、卫藏、康三区)。在达赖喇嘛的故乡青海的藏人占当地总人口的1/4。据达赖喇嘛在1987年所说,在藏区汉人的总数(750万汉人)已经超过藏人总数。可能出现的种族屠杀会多败俱伤,但少数族裔恐怕会受到不成比例的伤害。但不幸的是,许多大小各式民族主义的独派倡导人似乎认为这些现实灾难都可以在浪漫化语境中被化为乌有。
东西合璧的新视角
在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国共两个政党对现代性的追求都犯下了妄自菲薄、食洋不化、买椟还珠的错误。所谓的“妄自菲薄”指的是国共两党在追求现代性、构建民族国家时抛弃掉了亚洲和中国自己的优良传统。所谓的“食洋不化”是指国共两党在构建现代民族概念时,未能认识到欧洲用了几百年战争的暴力手段(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方式把成百的城邦小国或部落公国整合成几十个中小国家,通过先“国家建设”后“民族建设”的方式完成“民族国家”政治工程,然后又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建立了超国家的欧洲联盟;而中国国家的形成在两千年前即已开始,[69] 超大国家的整合早已用武力方式完成,而近代“国家建设”(现代化问题)又是在殖民主义挑战的国际环境下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双向交错互动,以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用民主的方式来转型,把传统的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转型成现代民主共和制的、多层级、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但至今,这项民族国家民主化的目标还未实现。所谓的“买椟还珠”指的是国共两党,尤其是整个历史上的共产党都未能接受下列一个重要思想:“公民权”。公民自决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基础、民族自决权是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手段而且是用一个高于个人的更大的制度框架以保护公民权。而最后一项批评也针对藏汉两族在二十一世纪都可以看到的狂热分治/分裂主义思潮。它们只是从族裔或地方认同的角度出发反对中共的极权专制,甚至心怀私利,做着小国“国父”、“王公”的美梦,而根本没有把公民权作为人类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础,甚至没有个人主义的人权和自由意识。没有彻底的自由主义导向的任何政治运动、宗教运动、甚至反抗运动(例如反共事业)可能永远无法跳出“王朝周期律”的怪圈,或者无法超越各色专制、极端主义在不宽容、无自由的同构体机构中相互折磨而无积极的社会公益。从苏联的崩溃留下的俄国和中亚各国的新专制主义来看,如果这种地方割据似的分散新专制制度取代一个“大一统”,其实质无非是“杀了一条红龙、催生一堆毒蛇”,很难说是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历史进步,而我又不得不说,这样的结局只是浪费了又一次历史机遇。
对上述批评,如果我们藉助当今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可以有更深刻和更宏观的认识。为了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我会着重选择具有亚裔背景、学问横贯中西的学者,主要有两位:历史学家杜赞奇和经济学家阿玛塔亚•森。最后我也会联系另外几位思想家,交叉论证我试图阐明的核心思想。
印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长在印度、受过哈佛教育、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2011年我还有幸受到时任所长的他的邀请在那里访问研究)、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是亚洲研究协会会长。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框架下,就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冲突,现代性内在的危机(世俗与宗教、民族与国家、个人与小区、国家与世界),杜赞奇都有系统和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下面四部著作里:《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北部中国农村》(1988年)、《从国家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述》(1995年)、《主权和真实性:满洲国和东亚现代》(2003),最后是他在前三部著述上的一个理论提升和总结性的著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性的未来》(2015)。[70]
杜赞奇的丰富思想可以从欧洲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开始。由此开启的“现代性”包括“工业化”(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逻辑)、“民族国家”(有限的疆界内的最高主权)、“世俗化”(从宗教脱魔出来),沿着这三条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逻辑,历史以目的论为指引走上线性的、“隧道般封闭和狭窄的”、进化论的、甚至是历史决定论的方向。基于亚伯拉罕的宗教传统(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属于“圣书”《The Book》的宗教),一神论、创世说、原罪论、忏悔规仪、末日审判、天堂永生和地域惩罚等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世俗与神性的二元对立由此建立起来。随着这同根的三大信仰体系逐渐教会化、制度化,“忏悔型的宗教”出现了二元对立更激进化的趋势(“激进化的超越”)。尔后西方产生的民族主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发展出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忏悔型的民族主义”部分取代了宗教的超越地位,“国家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民族主义出现了滑向绝对主义的危险。然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以西方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遭遇到了全球性的危机:过度消费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生态危机)、民族国家主权的的僵化和效力递减等等。针对“现代性”的危机,杜赞奇在时空上进行了两个调整:在时间上,他把眼光投射到“轴心时代”,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主要宗教相继产生(印度教、犹太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的多元时代。在空间上,面对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文化),他从西方中心观扩张到亚洲。亚洲/亚洲传统成了为他重构历史观的重要资源。为此,杜赞奇提出了几个核心思想:“循环”、“动态”、“分叉”、“相交错”和“竞争性的历史”、“对话性的超越”、“循环的理念和力量”、“网络的区域”、“分享的主权”(“新的普世主义”)等等。无论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亚洲佛教、帝国主义、边缘土著居民、泛亚洲主义、地下教会等等,都揭示了跨国、跨地方的思想观念、权力和物质的流动和互动。杜赞奇写道:“历史是未来行为充满活性的各种可能性的循环的、动态的蓄水池。某些流水何时、如何被启动取决于理念和其他历史力量结成的关系的节点。”[71] 在这样的思维下,杜赞奇是认同从个人、国家到世界主义和超越的不同台阶的。杜赞奇的“世界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在这一理念下,全人类无一例外的属于一个共同体。因此,当这样的归属感可以和其他各类认同的共同体(例如地方、国家或宗教等)分享时,世界主义的共同体必须能和其他任何的亲和力团体分享主权。换言之,世界主义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和代言人必须能够就政治社会某些相互接受的领域制定主权性的决策。” [72] 从个人的“修身”/“修心”、地下或边缘人群的反抗、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再到帝国、泛地区运动和全球主义/世界主义,而后追求超越/出世/神性/永恒等等,最后神秘主义/不可知理论又把超越和人心联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真实性和神圣性的相互论证。与其说有一个绝对主义的神灵/造物主,不如说真实性/神性更多存在于“对话型的超越之中”。在杜赞奇看来,“对话型的超越”意味着“超越了一个不再定于一尊全能的神、真理、或末世的自我。对话采纳渐进主义和地方需求与普世要求之间的协商谈判,是和那些能够卷入当下千变万化的需求的、来自活的历史的宝库的思想紧密相连的。它今天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接纳的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它的第二个要求是:它有文化能力创造出个人和集体的承诺,而这恰好是希望和圣仪所拥有的问题。”[73]
作为一个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分析历史学家,杜赞奇的学术可以从抽象和具体两个方面被嵌入我的论述中。从抽象的理论层面上来看,具有印度裔背景的杜赞奇吸纳了甘地的思想,并以此为资源批判现代性、资本主义和不可持续的消费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但遗憾的是,杜赞奇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达赖喇嘛在他的所述议题上的重要贡献,以致他在论述佛教、中国、印度、超越、生态危机和帝国/民族国家对边缘族群的压迫等等,都没有引用任何达赖喇嘛的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显示的,达赖喇嘛的思想贡献在中印文化、宗教和世俗、东方对西方、各宗教对话、帝国和民族国家、抵抗和超越等重大问题上都架设了桥梁并占据了中枢位置。而我在此能将达赖喇嘛和杜赞奇的思想融会贯通起来,也恰好证明达赖喇嘛的思想贡献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学术和科学影响。就这一点,限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展开,但我还是愿意指出,伯克利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许多著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印证了“万物归一”、“生命相互依存”、“阴阳互补而非对立”、“理性和直觉两种知识”以及神秘主义作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哲学背景,等等。在《物理学的道》一书中,卡普拉写道:“意识到自然世界万物相连在生态环境表现特别明显。相关联、关系和共同体是生态学的根本概念。相关联、关系和归属是宗教经验的核心。我因此认定生态学是科学和灵性的理想桥梁。”[74] 在《转折点》一书中,卡普拉抛弃了牛顿的机械力学观、达尔文主义,提出了运用系统思维、全息整体思想、非线性进化来认识世界,包括社会生活,并写道:“作为开放体系的各种有机体通过与环境的密集的交换而保持生存和运作,而这一环境本身也部分由这些有机体构成的。因此整个生物界,我们星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高度整合的由生命和非生命形态构成的网络。尽管这一网络是多层级的,交换和相互依存也存在于所有层级之间。”[75] 在《生命之网:生命系统理解新论》中,卡普拉运用“深层生态学”、“复杂理论”、“混沌理论”、“熵理论”等(杜赞奇也运用了部分新科学理论)来建构一个“认识心灵、物质和生命的统一观点”。 [76]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重要创始人、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揭示了动物、社会、机器和其他非生命的实体都有系统、信息、控制、反馈和沟通、控制模式等,而模式是生命的重要特征。他写道:“我们不过是一条不断奔流的河中的各种漩涡。我们不是固存的东西,而是自身保存的模式。”[77] 另外生态学也揭示了下列六个重要原则:相互依存、资源的循环流动、合作、伙伴关系、灵活性、多样性。它们使得自然界充满智能,能够和谐、动态演进、自我调适来达到可持续性的体系平衡和生命力。基于这些思想,卡普拉把生态系统和人类共同体做了如下比较:“在生态系统中,网络的复杂性是其自身生物多样性的结果,因此,一个多元的生态共同体就是一个有弹性的共同体。在人类共同体中,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起着同样的作用。多样性意味着许多不同的关系,就同样的问题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一个多样性的共同体就是一个有弹性的共同体,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形势。然而,只有在一个由关系的网络支撑的真正生机勃勃的共同体中,多样性才能成为一项战略优势。如果这个共同体分裂成孤立的集团和个人,多样性就会容易变为偏见和摩擦的根源。但如果这个共同体意识到它所有的的成员都是相互依存的,多元性就会使得各种关系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也会使得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每一个个体成员更加富足。在这样的共同体,信息和思想在整个网络自由流通,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求知方式,甚至各式各样的错误,都将使得整个共同体更富足。”[78] 从上述思想,我们可以轻易看到现代科学和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亲和性,卡普拉也明确赞扬“佛教哲学包含了对人类的状况最为清晰的解析”。[79]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达赖喇嘛把佛教分为“佛教哲学”、“佛教科学”和“佛教信仰”等,并在过去几十年里积极强调与现代科学家对话,促进科学、佛学相互学习补充。
杜赞奇作为一个专攻中国的历史学家,他的有关中国革命、满洲国等的案例研究,也为我们思考西藏问题提供了许多灵感。满族作为中国历史最后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在清朝覆灭后,并未能像蒙古皇族一样退回故土残据。满族在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努力下借助日本的帮助也曾在今天的东北、过去的满洲里建立了满洲国(1932-1945)。满人属于通古斯语系的游牧民族,和蒙古人也有密切联系,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契丹(907-947)、辽(947-1125)、金(女真)(1125-1234)、清(1616-1911)等王朝。满洲国建立后还得到13国的外交承认,包括法西斯意大利和梵蒂冈。但为何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国家历史并曾维持世界上第一大帝国的民族却无法在自己的本土上建立和维持住一个民族国家?而且二战期间日本并未公开宣称满洲国为其殖民地,而是推行了一项“建设民族国家的政治工程”,还把大量的国民和工业转移到满洲国,推动了当地以“发展型国家”为特征的工业化,拥有了比后来独立国家还要优越的经济基础,这一失败就更显得神秘了。所以,杜赞奇认为,“满洲国提供了一扇窗户来窥视民族形成、国家建设和认同构造的现代过程。”[80] 满洲国的成立和灭亡必须在全球、地区和地方的多层层面上来理解:首先满洲本身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国家认同必须承认和接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汉族、满族、鄂伦春、朝鲜等);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中国民族主义在满洲卷入冲突,他们政治、军事较量的胜负(这有取决于全球的战略联盟)左右了满族帝国的命运;第三,上述因素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泛亚洲主义、文明的对话和认同、精神超越和民间宗教信仰等使得民族国家的构建更为复杂,满洲国成为“东亚的争夺地带”、“试图同时代表边疆和国家、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的独特空间”。[81] 满洲、日本、中国、甚至朝鲜都试图把这一空间呈现为各自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机制”。杜赞奇定义道:“真实性机制是一种符号的权力机制,它通过预先的呈现和符号化神圣民族的能力来先声夺人地消除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者们的挑战。这种机制并不仅仅拥有消极的或压制性的权力,它也允许它的监管人去塑造身份认同和管理对资源的使用。”[82] 真实性机制成为国家建设、扩展政府性和维持主权的关键因素。他最后得出结论:“根基深的民族是由真实性机制来保驾护航的,不管它是如何脆弱或是防范性的,只要它有潜能去强化边境和在道义上把整个世界驱离出去。”[83] 问题在于,满洲国面对内部的多元分歧和国际环境的恶劣无法建立这种能力去实现民族国家的梦想。在民族主义高涨而中国(中华民国)依然孱弱的时代,这一历史的失败对当下的西藏有许多现实意义。
当然,中国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段能够最终压服边疆的各种建国努力,并不意味着中国本身没有经历民族国家建设的危机。在研究国家权力和文化的纽带关系中,杜赞奇从地下活跃的所谓“邪教”或“会道门”组织中看到了一个不断自我神化的国家的问题:当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与传统的宗教信仰体系脱钩、甚至成为后者的敌人(尤其在共产党政权下)后,国家政权就停止与地方精英分享文化权力资源,而国家强化推进现代化、资源吸取能力使得地方精英不再愿意仅仅成为国家压榨人民的工具,结果地方恶霸、土豪劣绅兴起成为国家的辅助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资源,包括被官方斥为“邪教”的民间宗教信仰系统,为民众提供了超越性的空间,国家和民众对立形成的空洞也会削弱国家权力基础,使得国家权力内转衰退进一步恶化。从这一视角,我们看到满洲国采取较国民党和后来共产党都更宽松的接纳政策,利用了民间宗教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而国民党失去政权、共产党一直处于与宗教力量的持久战都和权力与地下宗教文化的敌对有关。宗教,尤其是民间地下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面临的颠覆性组织权力,这也是汉藏问题的部分内容。杜赞奇总结道:“在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国家里,现代化的目标孕育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而正是它至少从1870年代以后就已经不断扩展国家干预的规模。但国家建设的过程正逐渐由国内秩序中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提供合法论证。这些国家被绑进了一个新的合法论证的逻辑,亦即他们必须在自我强化的期盼攀升的时代提供不断延伸的公民权所许诺的现代性利好。这个‘现代化合法过程’的辩证法变得更加急迫,因为现代化过程已经致力于破坏合法过程的传统基础。因此很清楚,至少从某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得以理解。”[84] 同理地,汉藏冲突和西藏问题也必须放在现代化的逻辑和过程中才能得到更好理解。否则,我们就无法解读满洲国的大规模铁路建设和当今青藏高原的公路铁路和航线的建设到底只是殖民计划还是现代化进程,或者兼而有之。
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构建作为现代化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有封闭疆界的主权。但矛盾产生于认同的不同等级和比例(“梯状的身份认同”让我们联想到地图的比例尺和等高线)。在杜赞奇看来,认同形成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国家层面,也有“次国家”和“跨国”的层面。“考虑到民族的形成有自愿性和渗透性,它们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就不具有种族民族主义宣扬的天注定和排他性。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有能力发展出多元文化的国家,依据两个认同的不同比例尺度, 亦即‘领土-国家的’和‘次国家-跨国家的’,来组织自己。嵌入到了不同叙述和制度的两种比例尺度在价值层面上应该是相互吻合的。但无论是因为全球竞争性、权利意识、或者是对这种意识的反动,各种身份认同还是容易滑向关闭的政治,两个比例尺度还是经常处于冲突之中。”[85] 就这一冲突,印裔美国经济学家阿玛塔亚•森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作为目睹印巴分治以及随后的大屠杀的学者,他对西方大现代化思维和族群狂热主义在他的《身份认同和暴力》一书中给予继续批判。他指出西方和东方的一些分析家都陷入了同样的“单一性的误区”(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 或者solitarist perspective)。森无不自我解嘲地说:“对一些人来说似乎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来认识到我们能够、而且也确实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同时属于许多不同的各种重要集团。”[86] 在单一的标签下,人们容易用本质化的方法、还原论者的思维(reductionist thinking)把“多向度的人类”变成“单向度的动物”,制造固化的认识、偏见,强化“我们-他者”的差异和敌对,并由此“培育仇恨”(正如“武术”一词所显示,武力是一种艺术),使得世界充满火药味,并最终相互去“屠杀杀害我们的敌人”。森认为,“有了适当的煽动,某一群人培育出的认同感能够变成残害他人的强力武器。”[87]
文学家王尔德说过,“绝大多数人是其他人。”[88] 如果政治人物要操弄各种差异性,并利用他们来传播差异、仇视和恐惧,把仇视注入政治冲突并以此为燃料动力来驱使政治发展,人类就会进入无休止的屠杀之中,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是自杀,整个地球就是坟场。为了避免如此惨象,森提出了他的设想:“当代世界和平的前景也许在于承认我们属性的多元化,并运用理智把自己作为大千世界一个普通居民来思考,而不是把自己关进狭小的笼子里成为囚徒。最重要的是,我们头脑清楚地明白自由的重要性,我们用它来决定我们的先后选项。要有这样的理解,我们需要正确地认清有理智的公共声音在各国内和各国之间应有的作用和效能。”[89] 关于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甚至个人可以选择和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自由。文化的自由当然包括拒绝自动或被强迫归属某种传统(宗教、种性、语言、地域、职业等等),尤其是对年轻人,他们有自由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公民个人的自决是优先于民族自决的,而后者通常是保护前者的制度手段。[90] 抽空或漠视个人自决的民族自决极有可能沦为最终奴役人民并剥夺他们公民权的一种集体暴政,中共这样做了,也许还有其他的宗教或族裔集团也想这么做。关于理智和公共理性思考,一个重要内容是“自我反省的能力”和理性至上的认识,因为“即便我们在对理性的重要性提出异议,我们也要摆出理由”。[91] 只有坚持多元、自由和理性,我们就可能逐渐进入“民主的全球性状态/国家”(a democratic global state): 它由无数的制度和成员构成,包括联合国、非政府机构、公民组织、全球媒体、全球商业/企业、社会运动和个人,等等。[92]
对于未来理想的世界,从康德到罗尔斯,无数原则和方案都被提出来了。在《永久和平》一书中,康德提出,一个公民的宪法应该是“共和制的宪法”,它是建立在下列三项原则基础上的:“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所有人作为从属者依靠于一个统一立法的原则”,“所有人作为公民平等的原则”。只有这样的宪法才是源于最初的契约观念,也是所有的立法都需依据的基础。共和制的宪法提供了“永久和平”的希望,因为如果公民必须同意或反对参战,他们会不愿意加入这样的“邪恶游戏”。[93] 如果各国都有了和平条约,逐渐就可以建立“和平联盟”(the Pacific Union)。通过“联邦化的过程”,它会扩展到更多国家,最终可能演进到“万族世界国家”(world state of all nations)。[94] 康德还指出,“真正的政治如果不尊重道德就寸步难行。如果政治本身是一项困难的艺术,那它与道德的结合就不是一项艺术,因为如果二者发生冲突,道德可以解开政治无能为力的最难的死结。”“道德的政治”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人民统一联合入一个国家只能根据自然法的自由和平等原则”。[95] 已故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是康德、密尔以来的最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和《作为公平的正义》(2001)给我们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理念和思想去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同时,他的著作也建立了一套民主、多元和宽容的程序原则来参与公共的理智辩论,提供了世俗的、却又不反宗教的思想基础。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就是承认“合理的却又不兼容的若干广泛的教义的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又是“在一个宪政民主自由的制度框架内行使人类理智的正常结果”。[96] 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和教派分裂产生的宗教宽容是一个分水岭。罗尔斯提出了一个“二元主义”把“政治自由主义”局限在政治领域里的观念,以别于休谟和康德的“综合的自由主义”,同时与“综合的宗教的、哲学的、伦理的教义”想区分开来。在政治自由主义下,人变成了公民,不仅他们有相同的政治地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且他们也是“通情达理的”、“理性的”、具备两个重要的道德能力:辨别是非公正、具有良善观念。和森在这一点上有共识,罗尔斯也认为,“公共理性”、“公共的理性探讨”、“协商型民主制”应该成为解决冲突、形成共识、制定决策的根本方法。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试图通过“作为公平的正义”来找到人的理想从而提供一个“评判社会基本结构的阿基米得基点”。[97] 罗尔斯不仅试图为自由民主社会找到道德基点(“基础的理智”),也试图建立“万民之律法”,为非自由的人民以及他们与自由人民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原规则。他提出 “对等互惠”和“公共理智”两条法则。[98] 无论时间、地点或文化渊源,下列四个原则都是不言自明的定律:“合理的多元主义”、“多元的民主统一”、“公共理性”和“自由民主和平”原则。[99] 在政治层面上,人们不必对“综合的教义”进行争论。他说,“在政治中试图体现全部真理的狂热是和民主公民权所拥有的公共理性不兼容。”[100] 所以政治自由主义层面的追求目标与其说是“真理的”,不如说是“合理的”。而我们社会为了维持公共理性,需要“通情达理之士”,而不是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通情达理之士”需要符合两个特征:他们准备好了提出大家作为平等公民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尽管有时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并非最好选择;他们理解、承认和接受裁决的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结果,形成民主社会中的理性的宽容。[101] 最后,罗尔斯认为,“没有人群(民族)有建立在征服其他民族基础上的自决权或分离权。”[102] 未来世界可能并非会走向一个“世界政府”,而是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和体系共同遵守“万民之法”,负责管理世界人民的合作和履行相关的义务。[103] 很显然,这些思想与甘地和达赖喇嘛的思想完美地呼应、支撑。在思考和解决西藏问题上,我们不仅有藏文化、佛教文化的原创思想,有印度文化的古老和新近思想理念,也有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做指路明灯。
结论
讨论西藏命运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话题,讨论中国前途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话题。两个主题交错再牵扯上蒙、维(吾尔)、回、满、台、港等诸多热点,问题之复杂、历史之久远、情绪之对立、偏见之深重、代价之巨大,都使得本书作者难以给书收尾,难以给收尾的结论收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我此时的心情。行走中道,左右撞击,是我此时的担忧。我无意在本书中提出一套系统、权威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所以,我只是认为,我的文字和观点都是作为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在公共理性思辨和讨论过程中尽的一点世界公民的义务。
正如本书书名所体现的,目见高山,心升景仰。在最后一篇长篇理论总结里,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拨开迷雾、呈现高山。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方古代宗教理念、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当代甘地和达赖喇嘛的教导最终都可以融会贯通,为我们理解西藏、中国、亚洲和世界,理解我们的族裔、身份认同和民主自由追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内洽的理论体系。西方的奥林匹亚山的视角,东方的喜马拉雅山的意境,促成我们找到阿基米得基点,来解释和构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原则。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尽管我们有许多人热心关注西藏、中国、和中国相关的一系列话题,但我们缺少认识和沟通这些重要事务,这些生死攸关大事的智慧。不可否认,政治是大家之事,每一个公民都有参与和发言的权利。从这一点上来看,政治的门坎很低,在民主社会里,甚至基本不存在。但民主政治强调公共舆论、公民投票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辅之以思想库、公民美德教育、领导能力、职业文官等重要建制。民主制不会沦为民粹主义、甚至暴民制,更不会成为毛泽东式“大民主”的幌子,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专业分工和教育培训促成的开放的民主精英阶层。因而现代民主政治催生了政治科学的诞生。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之中,政治科学是与经济科学、社会学、法理学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学科。公民参政议政不需要门坎,但以政治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观察、认识、分析和解决政治问题和冲突却是必须要有系统专业培训的人才和智慧。很不幸的是,政治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未被建立起来。无数参与政治辩论的人还只是以门外汉的身份、热血文学青年的知识或至多以评论人的思维来讨论政治。希腊哲人柏拉图曾说过:人们的鞋坏了,会去找鞋匠修理;人们的推车坏了,会去找工匠修理;但国家坏了,每一个人都会跳出来说,我可以做国王,修(治)理国家。所以,柏拉图要找哲学王。在成吉思汗完成霸业之时,他就有幸遇到了柏拉图这样的智者。耶律楚材是有功于成吉思汗的千秋大业的,但一位西夏善于造弓的工匠却嫉妒而生不满,向成吉思汗质疑道:“现在重要的是打仗,要耶律楚材这种读书人有什么帮助呢?”耶律楚材反问道:“造弓都还需要造弓匠,治理天下难道就不需要‘治天下匠’?”幸亏成吉思汗有历史英雄的智慧,所以能更加器重耶律楚材得天下、治天下。可悲的是,在自媒体泛滥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称为“哲学王”或“治天下匠”,对政治夸夸其谈却又从来不知道政治的科学道理,而且又根本不通古今、不晓东西,却不思进步。当中国处在黑暗之际,我们看到了一大群萤火虫,尽管他们自鸣得意地宣称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却无法明白他们自身却只是在黑暗中毫无方向地打转。当然,他们更无法明白远方灯塔的存在,更无法抬头望见熠熠生辉的北斗星。我要说的是,康德、罗尔斯、甘地、达赖喇嘛就是灯塔,他们指出的超越宗教的普世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同情、慈悲天然情感基础上发展出的“对等互惠”、“公共理性”和“非暴力、包容”就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阿基米得基点。更进一步说来,从达赖喇嘛、杜赞奇、哈贝马斯和现代量子力学等看来,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点”,而可能只是一个“虚空”、“网”、“关系”或者“对话的逻辑”和“协商的民主”。
遵循超越宗教的普世价值,许多人们纠缠不清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在公共空间讨论的程序和规则需要体现民主的生活方式。尽管中国人还生活在专制体制下,但海外的华人已经生活在自由民主多元空间下,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努力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公民。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用自己的“圣书”来评判他/她人的“综合性的教义”或无神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多元宽容需要我们放弃在“你的神”、“你的圣书”和“我的主”、“我的经典”的层面上进行原教旨主义争论。而且,无神论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理念”,所以,政治社会的民主讨论不要试图解决终极层面的、各种都有合理性的文明间的差异。我们也不要幻想,通过分裂、切割,我们就可以消除差异。印度的例子证明了分裂就可以解决差异的无效。印度在穆斯林从东、西巴基斯坦分出后,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西巴基斯坦最终也无法留住东巴基斯坦(后来的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兄弟。美国总统林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得很清楚:“从(蓄奴还是废奴─引者注)这些问题里产生出我们的宪法争论,然后我们就此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少数派不默认,那多数派或政府就要终止。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要让政府继续存在,要么一方默认,要么另一方。如果此时少数派不默认,而是要退出分离,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先例,以后这个先例会让他们分裂和毁灭。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少数派如果也不愿被多数派控制,也会从他们中间分离出去。例如,为什么新的邦联的一部份在一两年后不会任意地从邦联分出去,就完全像今天联邦的一部份所声称的要退出联邦?所有那些抱有分裂联邦情绪的人现在正被教会做这种事的脾气。在所有的各州里,难道有完美的利益吻合只造就出和谐而且会阻止分裂重启?直白说来,退出的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多数派受制于宪法的制约和限制,随着公共舆论和情感的变化而会轻易改变,它只是一个自由人民的主权者。无论谁摒弃了它,必然就飞向了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主义。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统治作为长久安排也是不允许的。因此,摒弃多数原则,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主义了。”[104] 从林肯的这段话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分裂”、“退出”不会成为一种解决分歧和冲突的方式,只会引向无穷无尽的分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历史所体现的统一的联邦的重要性,以及联邦政府多次用武力来捍卫统一的必要性。美国独立后经受的混乱,尤其是谢斯起义引发的恐慌,推动了联邦宪法的制定,一个强化了权力的联邦政府和总统制替代了最早的邦联。内战中林肯再次挽救了联邦,并进一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在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非裔人口要求通过民族自决在东南部(或弗罗里达州)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州。美国的两党没有一届政府答应过这个要求。如果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一个“种族大熔炉”都极力维护独立,并愿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由此可见一个统一大国的价值。
美国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三个启示:第一,“分离”/“退出”可能会产生出更多的反动或保守的国家(美国的例子是奴隶制国家)。第二,水火不兼容的地区、人种、阶级和社会制度都可以在民族的框架下磨合成一个统一体。第三,民主制度作为维护统一进程的主导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那么,问题是:当今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下的暴政政体,维护国家/民族统一还有价值吗?把中国拆成碎片难道不是解构专制的一种战略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区分。[105] 在英文里,最简单的区分就是“liberty to”和“freedom from”。比如《大西洋宪章》里的“四大自由”,前两项是“言论自由”和“敬拜自由”,属于积极的自由(liberty to speak and to worship);后两项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and from want)。我们时常听到的“西藏自由”(Free Tibet或freedom of Tibet), 如果说这个口号要求的是言论自由、敬拜自由、迁徙自由、结社自由、选举权和公民权、免于共产党的暴政等等,那么,藏人和汉人以及其他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甚至境外的(台湾)居民都有了共同的目标。从共产党争自由可能成为团结所有居民、塑造共同历史传统、重构新的民族认同和维护统一国家的机会。如果这项自由主要着眼于“freedom from the Chinese”(或者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本土分离独立,或者内蒙古人、维族人、回民从藏人和汉人分裂独立出去,或者汉人内部的上海人、广东人、四川人等等与其他地区分离独立),那就会成为几十个族裔/宗教/地区/语言单位(如果还有希望划分出清晰的、合理的单位的话)的相互争执和内讧,可能成为仇家。假如我们可以肯定分家不会带来仇杀和内战(印度和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相反的结论),假如我们都可以接受灾难的结果(人类的基本慈悲和同情、世界所有大的宗教都会反对),是否分裂后的国家都会、或至少绝大多数都会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呢?奥斯曼帝国崩溃后,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几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是集中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苏联崩溃后(而且是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俄国人首先想从苏联离开),今天绝大多数的前苏联人口仍然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印度分成四块后(先是缅甸分离,以后是巴基斯坦分离,在以后是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分出的较小国家都走上了与民主若即若离的道路,而唯有印度一直坚守了民主制。所以,民族自决绝不自动带来民主,也就是说在更多的国家更多的领导人产生后,人民的权利可能完全没有得到实现,甚至可能倒退。而要真正实现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公民自决权、个人主义的公民权利必须高于和先于民族自决权,甚至可以完全与民族自决权脱钩。由此可见,现居中国境内的所有居民,无论族裔/地域/宗教/语言,团结一道推翻中共的暴政显然是共同获得自由民主公民权的最佳选择。而只有在公民权获得保障的前提下,只有在公共理性空间存在,通情达理的公民可以通过非暴力和宽容的方式讨论国家构架和民族关系的情况下,民族自决才有行使的可能,而较小民族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可能性才会出现。所以,即便各个民族(包括汉族)要想实现彼此分家,也必须共同合作,在民主化过程中协调集体行动,首先建立宪政民主。在中共暴政依然是所有中国人共同敌人的条件下,超越历史阶段性而鼓吹各民族的独立,只会把中国人与中共的尖锐矛盾掩盖起来,并转化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宗教与宗教的矛盾。而一旦在政治层面14亿中国人都卷入到“综合的教义”之争,那打开的就不只是潘多拉的盒子了,而是地狱之门。对于中共这个已经数次把中国人送到地狱的政党来说,民众的分裂和内乱恰好为他们的国家利维坦提供了合法性。不难理解,为什么分裂压倒民主的历史主题,会和救亡压倒民主的历史经历一样,会延续专制的王朝政治,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无限的奴役。我们也容易想见,为什么我们恍恍惚惚看到某些所谓的“异议人士”经常被中共所容忍甚至鼓励在国内去传播更激进的“西藏独立”,或在海外组织各种独立运动。这对中共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利好:一方面可以利用厚黑手法在目标、组织、人员和行动上分裂反对派,并以此制造分裂、猜忌、内讧和仇视;另一方面,可以让反对派在14亿中国人面前看起来丧心病狂,因为毕竟中国的统一已有千年的历史,而汉族占据90%以上的总人口,这和前苏联(俄国人只占到50%多一点的人口)是完全不一样的国情;而且即便在现代军阀混战时期,也没有听到军阀独立建国成为主流。事实上,所有民国期间的军阀都有支持统一的意愿,只是谁来统一的差别。所以,我批评的是现在不去向共产党要自由,而是把汉人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从而瓦解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中共暴政继续保留存在的空间。
民族自决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民族自决的积极意义必须要和公民自决(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相匹配,才能成为历史的进步手段。而且,即便所有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包括汉人有脱离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并非必然会导致民族独立。打个比方,现代婚姻制度一个重要的权利就是离婚自由权。必须双方同意才能组成婚姻家庭,但只要一方要求就可离婚,这基本已成现代社会的通行原则。离婚自由主要的价值并不在于赋予人们走出婚姻、解散家庭的权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结婚的目的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制度化相互的承诺。但离婚权是保障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机制。正是因为有了离婚权,婚姻双方才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参与谈判协商,提出要求、施加压力,等等,使得婚姻质量和状态能够得到及时调整和修复。同样的,在民主国家里,某个地区也会有独立诉求(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大不列颠王国的苏格兰,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等,甚至我居住的斯德顿岛,也是理士满县,在上世纪80、90年代要求从纽约市独立出去),之所以这些独立运动最终都未成为现实,有的可能已经被永久化解,主要就在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大民族在国家权力结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割等政策上能够进行让步或补偿。例如加拿大政府实行的三种形式的集团差异性的公民权:自治权利(联邦制、特区、自治区等)、多民族权利(语言、文化、宗教等教育补贴等)和特别代表权利(议会里设立民族院为上议院、保证女性代表等等)。[106]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自决权有时更多是一种吵架的权利、而非独立的前奏。一旦中国完成民主化,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所有这些建制都会最终得到落实和贯彻。另外,根据我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系已故著名教授丹夸特•罗斯托的观点,在动态性的民主化模式中,一旦有了国家统一这个前提,这个国家就已具备民主化的条件,而冲突的爆发其实是民主化过程的一部份,一旦大家相互怨恨却又无法摆脱,就会进入谈判阶段,这就是制宪过程,而最终结果就是民主建制。[107]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动态民主化过程。
从上述关于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民族分裂还是统一是攸关中国民主化进程成败的大事。有部分人之所以坚持要把中国分成七、八块、甚至几十块,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统一就等同于“大一统”。所谓的“大一统”,就是秦汉体制、以及后来不断修复重建的隋唐体制、元明清体制和当下的中共体制。用金观涛和刘青峰的术语来说,就是“超稳定结构”,其核心是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全权主义。其实把统一国家自然等同于“大一统”,这样的思维无意中陷入了中共(甚至几千年的皇权思想)长期打造的“大一统-乱”的二元论里。“乱”是中国专制传统建构的核心概念,以其恐吓效应来达到“两恶相权取其轻”的目的。而普通民众、甚至某些政治评论人都完全不知道“乱”(或无政府状态、自然状态、丛林法则)的真实功过可以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视角来检视。佐治亚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王飞凌在《中国秩序:中央王国、世界帝国和中国权力的本质》一书中,用长程大历史观得出结论:秦汉体制有利于官,并不一定有利于民;澶渊体制(澶渊结盟后建立的宋朝时期的国际秩序)无利于官,但并不一定无利于民。所以,战国时期、南宋时期、清朝末年-民国时期都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繁荣期。[108]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也注意到“乱”可以建构在两个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亚里斯多德(传承至洛克、康德、罗尔斯)和霍布斯(上承《圣经》里的圣保罗、马基雅弗利,下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亨廷顿)的两个平行传统(似乎和儒家、法家与道家、墨家的分野有可比之处)。在霍布斯看来,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就是黑洞、无底的灾难、文明的灭亡;而在亚里斯多德、洛克看来,政权的崩溃、无政府状态、乱并不彻底消灭友谊,摧毁家庭、教会、小区等组织,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重新讨论和建立社会契约的机会,或者说是关机后重新启动的机会。[109] 苏联崩溃后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共产党极权政权垮台,其后续期间人民死亡可能是很低的、甚至是不流血的;但如果有人要利用民族差异,挑起族群冲突,即便印度这样非暴力赢得独立的国家也会目睹上百万生灵涂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所有论述中(包括在其他中英文著作中),我并不非常担忧中共专制政权崩溃后的转型期,但是我却充满焦虑地警告所有的中国人不要培育、煽动和挑起族群危机和冲突。即便共产专制政权崩溃后,民族差异和矛盾会上升为转型正义需要解决的话题,而统一的各种构思,包括达赖喇嘛、罗尔斯等的设想,会引导未来的中国各民族通过协商民主制(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和式民主制(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例如瑞士、比利时、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实践),建立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的民主治理网络体系,从而与亚洲民主国家和谐共振,建立亚洲民主共同体,最终与世界民主国家联盟一起构建具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全球自由民主和平。至于具体的细节,除了本章前面已经讨论到的以外,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系统的“联邦中国构想”,[110] 刘晓波领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提出“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11] 其他学者诸如张博树在他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王天成在他的《大转型》,王力雄在他的《递进民主》等书中,藏人行政中央出版的《流亡藏人宪章》、《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及有关重要资料汇编》、《自治和藏人视角》(Autonomy and the Tibetan Perspective)、《西藏自治权和自治: 神话或现实?》(Tibetan Autonomy and Self-Government: Myth or Reality?)等书中也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思路。我们也许不能肯定,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就已经排除了中国、尼日利亚、印度、加拿大、西班牙、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分裂成多个国家的可能性,因此还会有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但世界历史基本已进入后现代性、后民族性时代,历史大环境已不利于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类治理实践的积累,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理念的突破,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纠缠的出路。“大智慧”已经产生、还会继续产生。一旦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思想自由、言论学术自由还会催生新的智慧。
如果我们要遵循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能使得最激进的分裂派(汉人、藏人、维人、港人、台湾人等等)能够在中国这个架构内吵架,而不是都要掀屋顶、拆房子,“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概念就必须厘清重构。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并不具有种族内涵的概念,所有的生活在中国境内(无论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为参照,为此,这两个政治概念都应被废除,而简单用中国)的居民都是中国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又多次融合成为一个再生的民族。既然中国首先和归根结底是一个变动的历史和地理并延伸进未来的概念,所有当下生活在这个空间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可以和“中国人”等同的概念。就像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国家建设所经历的,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不是印度教/印度语人的印度,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印度尼西亚人的,而不是爪洼人的印度尼西亚。而为了表达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我们不妨可以学习美国,考虑使用“汉族中国人”、“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总之,“中国”的概念不应该被政治化。
对于所有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都必须肩负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的责任:行慈悲、不作恶。任何散布族裔、宗教、地域、语言和文化偏见的做法都应该自觉自我收敛和受到外部抵制。再说,民主化的过程就是要清除部分汉人拥有的邪恶性。如何成为“好汉人”成为问题的关键。目前的问题是,达赖喇嘛给汉人一个承诺 :我们愿意和”好汉人”一起生活,而许多汉人不去思考我们如何能做好汉人,同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夸大 和恶化汉人与其他族裔的矛盾,把“中共”和“汉人”等同起来。令人警惕的是,在海外自由环境下,制造族裔憎恨的人大有所在。但是,简单化地泼污“中国”、“中国人”、“汉人”、“中
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是不负责任的。说得轻一点,对14亿人的历史文化和身份持完全虚无主义,是理论界的一种黄色下流暴露派,其目的是以博得眼球、证明自身存在和价值。说的严重一点,这不仅是一种文化死亡,而且是文化自杀,是“文化恐怖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自由民主理论基本上都鼓励更大的政治单位出现。前者从阶级看问题,族裔、性别、宗教之类的社会裂沟都会被最终的阶级革命抹平,因而倡导国际主义,它也和后者一样看到现代化大生产对更大市场规模的需求。但自由主义有共和、平等、博爱的理想,在“世界政府”、“全球主义”、“民主和平”等理想中都有世界主义的情怀。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民族融合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印度、美国、巴西可能是世界上先行一步的国家)。当然其前提必须是民族和谐共处、交融,个人有自由选择自己多元的身份认同,而国家不能采取强力来任意贴标签。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和平的根本保障。自由当然包括汉人的自由和其他民族的自由,其核心是个人主义的,而不必是族群的。但民族和谐可能被两股力量打破:未获得民族国家的相对弱小民族追求自己民族独立国家的努力;在多民族国家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民族试图推行强制性的种族融合、甚至种族灭绝。汉民族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非汉民族就构成了这一对冲突的两面。
在专制政府下,屠杀的发生是容易的。如果在毛泽东的共产党统治下可以在”土改“、”镇反”中轻易屠杀上百万,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至少三、四千万,文革中受害人上亿,在藏区屠杀几十万(可能近百万)。为什么汉人在自己的国家,藏人在自己的家园还遭到戕害?而与此对照,十几万藏人流亡海外(主要在印度),他们通常以难民的身份侨居在当地国。为什么他们在印度、欧洲、美国等地没有受到屠杀、甚至迫害?在美国有几百万的华人安居乐业,为何没有听说过民族自决、独立建国之类的诉求?根本原因在于有无下列四点:第一,个人自由;第二,国家民主;第三,社会正义;第四,世界多元。无论我们思考西藏问题、中国问题、或者世界问题,认识和把握住这四点,就找到了世界永久和平的钥匙。
[1]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讲述,《佛法与现代世界》,台北: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2007年,第136页。
[2] Clifford Geertz,Primordial and Civic Ties, in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31页。
[3]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44 (1960 Eighth printing), 第14页。
[4]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in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18页。
[5]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92-3页。
[6] Catherine Belsey, Poststructu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Seyla Benhabib,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254页。
[8] Jurgen 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1998 first printing), 第105-107页。
[9] Hans C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10] Liah Greenfeld and Jonathan Eastwood,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States, Civil Societies,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Thomas Janoski, et al,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252页。
[11] 同上,第259页。
[12] Seyla Benhabib,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第143-144。
[13] 同上,第153页。
[14] 同上,第3页,第126页,第175页,第182页。
[1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第3页.
[16] 同上,第6-7页。
[17] 同上,第5页。
[18] Benhabib, 第4页
[19] Benhabib, 第270页。
[20] 同上,第272-273页。
[21] Richard J. Payne and Jamal R. Nassa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12, 第71页。
[22] Satish Inamdar, ed., Mahatma Gandhi 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Non-violence and Compassion, Dharamsala, India: DIIR of the CTA, 2004, entry for September 14.
[23] 各种数据可参见:Barry Sautman, “’Demographic Annihilation’ and Tibet” in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 Contemporary Tibet, 第230-257页;[法]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第138-140页。又据历史学家李江琳在《当铁鸟在天空中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台北:联经,2012年),“1958至1961年,玉树州人口减少69,419人,比1957年减少了44%;果洛州至少减少35,395人,达35.53%,超过1953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118,172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资料。”“从中共军方资料中统计出藏人在战场上的死亡俘降不完全数据:三十四万七千余人。”见前言第11页、第16页、第430-432页。达赖喇嘛在1991年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提供了120万的数字,可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讲述,《佛法与现代世界》,台北: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2007年,第148-149页。1960年代中印边界紧张和1962年的边界战争带来的边疆贸易中断带来的粮食短缺,可见Sulman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第113页。
[24]达赖喇嘛传授,印度达兰萨拉尊胜寺影音工作坊制作,《道次第之前行开示》(台北:大千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25]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讲述,《倾听达赖喇嘛》,台北: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编印,雪域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6] Satish Inamdar, Mahatma Gandhi 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Non-Violence and Compassion, Dharamshala, India: DIIR,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05.
[27] 达赖喇嘛尊者与澳洲华人会面演讲节选。也见:The Dalai Lama, My Spiritual Autography: Personal Reflections, Teachings and Talks, collected by Sofia Stril-Rever, London: Rider, 第1-2页。
[28] 可参阅:The Dalai Lama, The Middle Way: Faith Grounded in Reason, translated by Thupten Jinp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达赖喇嘛传授,印度达兰萨拉尊胜寺影音工作坊制作,《道次第修心之宝践》(台北:大千出版社,2008年)和《道次第之前行开示》(台北:大千出版社,2011年)。
[29]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9, 第41,47页。
[30] 同上,第184-185页。
[31] 同上,第198-199页。
[32]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ward a True Kinship of Faiths: How the World’s Religions Can Come Together (New York: Doubleday Religion, 2010),第157页。
[33] 同上,第182页。
[34]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Beyond Religion: Ethics for a Whol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第28页。
[35] 同上, 第45页。
[36] 同上,第70页。
[37] Iris Marion Young in Benhabib,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第126页。
[38] 同上,第126-127页。
[39]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64页。亦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网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arxist.org-chinese-stalin-1912.htm。这一定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官方使用可以从下面三本不同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皮纯协、徐理明、曹文光主编,《简明政治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主编,《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70页;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有必要指出,《政治学概要》是由当今中共最高意识形态主管、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参与主编的标准政治学教科书,而金观涛和刘青峰则在香港和台湾完成他们的研究,代表中国体制内能生存下来的最自由化思维。
[40]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页。
[41] 沈福伟,《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也见其2006年再版,2014年新版。
[42]葛兆光,《宅兹中国》,第41页。
[43]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44] 同上。
[45] 林语堂,同上,第13-14页。
[46] 同上,第15页。
[47] 也参见:李章斌,《试论“华夏”作为认同的起源与形成过程》,《文化研究@岭南》,第九期,2008年。检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9/iss1/2/.
[48]冯天瑜、何晓明,《中华文化史》,下卷,第736-7页。
[49] Christopher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一章;S.L.Kuzmin, Hidden Tibet: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Occupation,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第15-19页。
[50]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e Mongols and Tibet: A Historical Assess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 Empire and Tibet (1996 and 2003), Tibet and Manchu: An Assessment of Tibet-Manchu Relations in Five Phas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2001 and 2008), both are DIIR Publications, Dharamsala, India: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51]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上卷,第41页。
[52] Carrie Rickey, “A Historian Critiques `Emperor`”, January 07, 1988,Knight-Ridder Newspapers, at: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88-01-07/features/8803200415_1_china-bernardo-bertolucci-movie; 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该片顾问等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840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B%E4%BB%A3%E7%9A%87%E5%B8%9D/7933;
[53] William L. McBridge, “Existentialism” in Robert Audi,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第343页。
[54]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40-841页。
[55] 见: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itor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M.E. Sharpe, 2006, 第224页;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00.
[56]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第85页。
[57] 在下列许多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西藏在大国地缘政治争斗中的困境:S. L. Kuzmin, Hidden Tibet: History of Independence and Occupation,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2011; Karl E. 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1990); Sulmaan Wasif Khan,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Gyalo Thondup with Anne F.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Gurgaon, India: Random House India, 2016.
[58]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562、244页。
[59]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60] 《国父全集》,见: 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7gs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535225598997。
[61] 可参见:Suisheng Zhao,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五章。
[62] 同上,第175页。
[63]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源流,1999年,第241页。
[64] 参见:维基百科全书,“刘仲敬”条目。
[65]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44 (1960 Eighth printing),第x页。
[66] Suisheng Zhao, 第178页。
[67] 同上,第184页。
[68] 参见:http://tibetdata.org/projects/population/;
[69]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的发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中指出,“现代国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国后就已经出现。
[7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1]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第9页。
[72]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第20页。
[73]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第282页。
[74] 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the 5th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2010, 第9页。
[75] Fritjof Capra,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London: Flamingo, 1982, 第297页。
[76] Fritjof Capra, The Web of Life: A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6, 第xix页,
[77] 同上,第52页。
[78] 同上,第303-304页。
[79] 同上,第294页。
[80]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第2页。
[81] 同上,第5页。
[82] 同上,第25-26页。
[83] 同上,第254页。
[84] 同上,第255页。
[85] 同上,第252页。
[86] Amartya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第45页。
[87] 同上,第xv 页。
[88] 同上,第xv页。
[89] 同上,第xvii页。
[90]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New York: Praeger, 1960, 第73页。
[91] Sen, Identity and Violence,第161页。
[92] 同上,第184-185页。
[93] Immanuel Kant, “Eternal Peace”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edited by Carl J. Friedri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1949),第482-482页。
[94] 同上,第490-491页。
[95] 同上,第541页和第517页。。
[96]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3), 第xviii页。
[97]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第584页。
[98]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第121页。
[99] 同上,第124-125页。
[100] 同上,第133和138页。
[101] 同上,第177页。
[102] The Law of Peoples, 第38页。
[103] 同上,第36页。
[104] Abraham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861, Washington, D.C., from: http://www.abrahamlincolnonline.org/lincoln/speeches/1inaug.htm.
[105]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edited by Robert E. Goodin and Philip Pettit,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7, pp. 391-417.
[106] Will Kymlicka, “Three Forms of Group-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in Canada,” in Benhabib,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p. 153-170.
[107]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in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edited by Lisa Ander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41.
[108] Fei-Ling Wang,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Albany, NY: The SUNY Press, 2017.
[109] Ming Xia, “Triangulating human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reorient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16, Vol. 1, No. 3, 405–426, http://dx.doi.org/10.1080/23812346.2016.1212541.
[110] 严家祺,《联邦中国构想》,台北:联经,1992年。
[111] 李晓蓉、张祖桦主编,《零八宪章》,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April 6,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