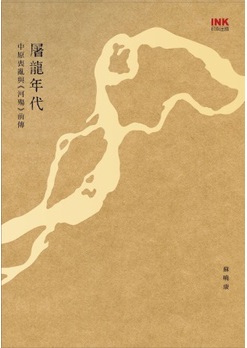 诗人布罗茨基以一种贵族式的骄傲看待自己的文字:“笔在世纪中能留下更长的犁沟,胜过你们提着香炉的永恒生命。”我喜欢布罗茨基,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流亡美国之后,布罗茨基跟其他的俄国流亡作家几乎没有联系,他厌恶流亡者圈子里那种抱团的氛围,以及那句像国歌一样的宣言——“朋友们,让我们挽起手来,以免孤身一人地倒下”。也许再也找不到比布罗茨基更爱美国的俄国人了,他毫不犹豫地加入美国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就是我们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个人主义精神。因此,当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国人。”我想,这就是布罗茨基到美国后创作又攀登上新的高峰的关键原因;同时,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流亡作家丧失创作能力的根本原因。
诗人布罗茨基以一种贵族式的骄傲看待自己的文字:“笔在世纪中能留下更长的犁沟,胜过你们提着香炉的永恒生命。”我喜欢布罗茨基,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流亡美国之后,布罗茨基跟其他的俄国流亡作家几乎没有联系,他厌恶流亡者圈子里那种抱团的氛围,以及那句像国歌一样的宣言——“朋友们,让我们挽起手来,以免孤身一人地倒下”。也许再也找不到比布罗茨基更爱美国的俄国人了,他毫不犹豫地加入美国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就是我们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个人主义精神。因此,当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们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国人。”我想,这就是布罗茨基到美国后创作又攀登上新的高峰的关键原因;同时,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流亡作家丧失创作能力的根本原因。
由于妻子遭遇一场严重车祸,六四之后流亡美国的苏晓康从九十年代初浮华的海外民运中抽身而出。二十年后,他重新拿起昔日那支横扫千军之笔,写的却是个体的创伤与救赎。从《离魂历劫自序》到《寂寞德拉瓦湾》,多年没日没夜地照料失去行动能力的妻子,以及反抗突如其来的抑郁症,就是一场卡夫卡说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一个人需要怎样的勇气与信心,才能横渡这片深不可测的海洋?不幸也是一种幸运,即便这个说法过于残酷,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严酷的命运馈赠给他以同代人中罕有的反思能力,使他在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时,有外科医生式的冷峻。正是因为六四屠杀的枪声与血泊,以及个体命运的顿挫和破碎,苏晓康从虚骄、自恋、怯懦的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破茧而出,成为布罗茨基那样“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国人”的“自由人”。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宏大叙事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之后,苏晓康的《屠龙时代》,会带给少年时代深受《河殇》启蒙的我,以怎样的启示呢?
中原何以沦丧?
《屠龙年代》的副题是“中原丧乱与《河殇》前传”,其实它不仅是“《河殇》前传”,也是苏晓康对自己在整个八十年代的创作生涯的回顾,更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横断面。
而所谓“中原丧乱”,指的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带的沉沦。苏晓康在河南生活多年,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就是河南省委机关报一个跑农村的小记者,算是半个河南人,于是故事就从他搜集到的、被正史遮蔽的“豫南垮坝”事件开始。
一九七五年,河南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垮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当时前去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说,垮坝造成的损失“相对于一颗小型原子弹”。河南垮坝死亡人数高达二十三万,与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长春围城以及唐山大地震并列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惨案。
这一溃坝惨剧,可追溯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跃进和大饥荒。大跃进时代所兴建的水利工程,多半偷工减料、浮皮潦草,是豆腐渣工程,不垮才怪。河南也是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中受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这场“人相食”的惨剧的始作俑者,中央有毛泽东、河南有吴芝圃、信阳有路宪文,河南饿死数百万人,仅信阳一地就饿死上百万人,正如苏晓康所论:“四九之后,大陆凡贫苦之地,又必成乌托邦迷狂之乡,坠入地狱之深重,非民国时期可比拟,河南又是其中的渊薮。”在这个意义上,河南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从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到七十年代的溃坝,再到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艾滋病泛滥,当代的河南可谓苦难深重。官府的凶残、环境的恶劣、资源的匮乏,使得民众如鱼游于鼎沸之中,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一面遂如溃堤般喷涌而出。苏晓康追问说:“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这现象当作何解?”谁有答案?
我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心脏地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并未在其诞生之地酿成巨祸,反倒传播至尚未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经过彼得一世改革一百多年仍被视为“东方”的俄国。俄国文化传统中理性的缺失和个人主义价值的淡薄,使得共产主义大行其道。进而,这套现代极权制度,越往东方发展,就显得越邪恶、越残忍、越卑劣,如毛泽东的中国和金家王朝的北韩,其疯狂、愚昧、血腥,让列宁和斯大林也会为之瞠目结舌。
具体到中国,暴政之暴,最为突出的地方,则是现代的共产极权主义与儒法互补的专制主义传统结合最为紧密的地方,如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偏偏是斯文丧尽、人心幽微之地,这是何等大的反讽。苏晓康指出,当年习仲勋在勤政殿里指着河南省委说:“你们就是大轰大嗡。”可谓将五十年代河南之迷狂倒错,一语道破。鲁迅说,“瞒和骗”是中国人“活着”的“必要之恶”,而《屠龙年代》则揭示出浮夸和说谎积淀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遗传基因。
黄河的咆哮与黄色文明的反省
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若以一个人、一部作品和一个观念而论,既影响学界又渗透到大众层面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序列: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及“救亡压倒启蒙”论;刘晓波、《审美与人的自由》及“自由就是美”论;金观涛、《兴盛与危机》及“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等。影响力更大、渗透面更广的则是:以苏晓康为总撰稿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及《河殇》中提出的打破黄色文明的封闭保守的思路。
少年时代的我,几乎读完了苏晓康的所有作品,最喜欢那部透视庐会议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激荡与纵横的《乌托邦祭》。后来,当我在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园里读到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才重新印证了《乌托邦祭》中一个个充满镜头感的画面,那些场景绝非出自作家的想象,而是如同法医般严谨地对“犯罪现场”的还原。
然而,对于以报告文学成名的苏晓康而言,他初次“触电”写成的《河殇》解说词,偏偏成为让他此后时时刻刻如影随形的“第一代表作”。《河殇》是苏晓康八十年代创作的所有报告文学的主题的汇总。因为《河殇》,他成为王震等中共保守派元老的眼中钉;因为《河殇》,他被动地卷入八九学运;因为《河殇》,他由家喻户晓的良心作家成为改名换姓的通缉犯,六四枪响之后流亡海外,人生的跌宕起伏由此开始。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以黄河为代表的黄色文明与以海洋为代表的蔚蓝色文明,是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的最佳比喻。《河殇》的缘起,是苏晓康受河南溃坝事件的震撼,而河南溃坝事件绝非单一、偶然的“自然灾害”,它折射出中国政治结构的致命症结:从魏特夫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社会之关系,到毛泽东发起大跃进的乌托邦思想的形成,其间的草蛇灰线,被苏晓康一一梳理出来。《河殇》创作于八十年代末,今天来看并未过时,苏晓康指出:“豫南垮坝,江河治理狂热,一路挺进到‘高峡出平湖’的长江三峡大坝,也洞开了南水北调、开发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卷起是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一股好大喜功——原来,资源高消耗型发展的‘中国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坝。”
苏晓康的父母青年时代受共产党指派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在二二八前夕返回中国,得以幸免于难。半个多世纪之后,流亡海外的苏晓康则赴台湾访问,对台湾的民主与文明心有戚戚焉。父子两代逆向的人生之旅,也算是黄色文明与蔚蓝色文明的分野与交错。台湾史学者李筱峰比较台湾的海洋文化与中国的内陆文化时,举了一个洋务运动中的例子:刘铭传在台湾开办铁路工程,第一段从大稻埕到松山的铁路完工通车,德国制造的第一个火车头“腾云一号”开出时,围观民众不像大陆人起来反对,而是惊喜万分,纷纷称呼火车头为“黑色妖马”。民情反应的不同,仿佛注定了中国与台湾在洋务运动以及此后一百多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
今天,中国仍未洗涤黄色文明的黄沙滚滚,融入蔚蓝色文明的清澈与宽广。以习近平而论,虽然在福建、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任职多年,其精神底色仍然是知情时代在陕西的窑洞里烙上的“黄色”。所以,他比起多少受了一些徽商传统影响的胡锦涛来,更左、更保守,中国也更多向毛时代摇晃。
图腾崇拜:龙与毛泽东
这一切,都是因为八十年代的那场屠龙之战,失败于六四的枪声之中。受制于时代氛围和传播平台,《河殇》打着文化反思的旗号,背地里从事政治解构的实践,可称之为“暗渡陈仓”。《河殇》从解构黄河、长城、龙等中国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文化图腾下手,苏晓康说:“从八零年代的龙认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泛滥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一统、偶像崇拜。这四样,因背离普世价值,恰成专制统治的隐形支点。”一部《河殇》,其实是五四之后第二次“屠龙”的尝试,只是那时谁也不敢说破:五四屠的那条“龙”是皇帝,《河殇》屠的那条“龙”是毛泽东。难怪杀人如麻的王震在中共中央的大会上突然跑题,气势汹汹地对《河殇》破口大骂。六四之后,《河殇》被当作学运的催化剂而遭到火力凶猛的批判,“庇护”《河殇》亦成为被罢黜的总书记赵紫阳的一大罪名。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祖龙不死,国难为已。所谓“祖龙”,古为秦始皇,今为毛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因言曰:”今年祖龙死。‘“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而毛泽东确实在多次公开讲话中以秦始皇自居,毛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所以,我曾经说过,毛主义的本质是”秦希斯主义“,是集秦始皇、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大成的、古今中外极权主义之顶峰。
毛泽东曾自我定位说:“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苏晓康的解释是:“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的人物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毛为争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不惜让中国死三分之一的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没有他的气魄与野心。这是极卑之人的疯狂的自恋,哪有什么理想主义成分可言?所以,哪一个信誓旦旦、忠心耿耿的毛主义者,不是尚未成为暴君的暴民?
六四屠杀,下令开枪的是躲藏在幕后的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缩小了一号的毛泽东,苏晓康指出:“回首当年,从六四血光之灾中,依稀仍可辨认那‘人龙’的身影:毛泽东这种‘极卑之人’,当道二十七年,天下早已糜烂,然而,我们当年难以逆料的是,‘毛堂’里那具僵尸的遗产,仍在继续糟蹋中国;诚如史学家余英时所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毛的中国。习近平携所有政治局常委拜谒毛的僵尸,成为宛如古代皇帝拜谒祖庙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仪式。摇滚歌手崔健说得好,“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浪还是在往同一个方向涌动。换言之,躺卧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依然操纵着左右中国人生死存亡的那个红色按钮。
《河殇》的那一页历史并未翻过去,因为屠龙的事业还未完成。元代诗人陈孚有《博浪沙》一诗:“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我愿意与苏晓康一起心向未来、以笔为枪。祖龙必亡、自由必胜。
文章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