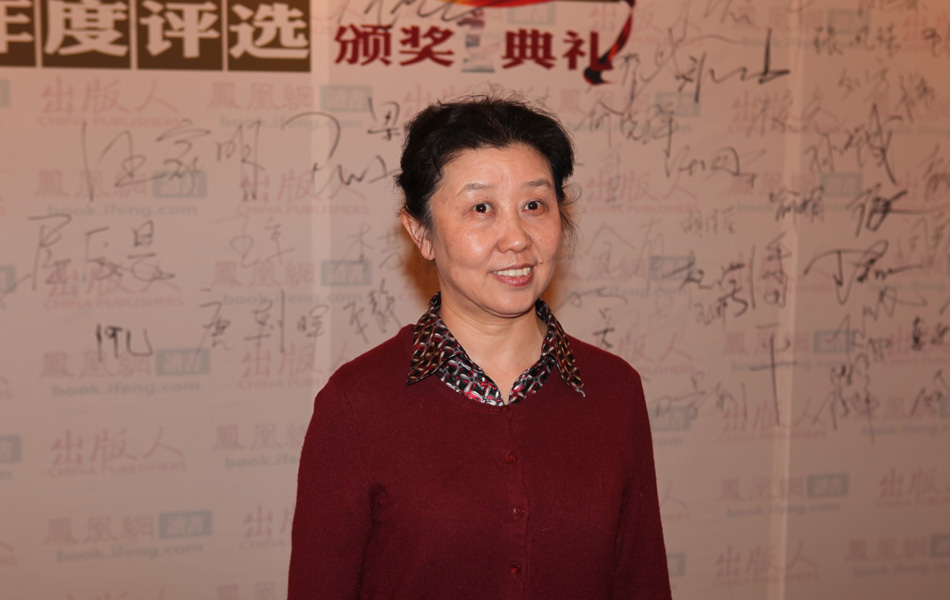秦川雁塔 2017-06-07
长期以来,苏联党史都在讲述这样的观点: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宫胜利后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无偿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属于人民的财产,并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
颁布《和平法令》
据说这一举措解决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得到农民的拥护,进而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于是在国内战争遇到敌人反扑时,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参加红军,成了革命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人对此容易理解,因为根据官方教科书的解释,土地革命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由于“解放区”的土改和“减租减息”获得农民支持,才保证了解放战争胜利。这就使我们感觉到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十分相像。
但是俄国《土地法令》的叙述中有很多含混和语焉不详之处,难道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吗?是该法令宣布以后农民才获得土地的吗?土地是“人民的财产”?什么样的人算“人民”?注意法令里只说是“劳动者使用”,那所有权归谁?是公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所有?是以什么标准分配土地的呢?这些问题现在仍好像是一盆浆糊。
实际上中俄两国的土地构成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土地私有,平民地主的土地大都来自购买和继承。而俄国地主的前身服役贵族的土地是国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连带上面的劳动力的方式形成的,虽有少量购买土地但其基本土地构成是国家给贵族土地作为征战的交换条件,俄国的兵制始终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俄语“地主”(помещик)一词原意为“主人”,并无汉译中土地所有者的意涵。
《农奴与自己的主人》 谢尔盖·伊万诺夫作于1908年
在农奴制时代的村社制度下,沙皇把若干公社划给某“主人”作领地,公社成员作为农奴受其束缚供其役使,但这只是一种“统治-服从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18世纪以后哥萨克军队和普鲁士式普遍兵役制兴起,贵族兵役制的作用衰落。
宣布,贵族的服役不再是强制性的,此后兵役和土地使用权相分离。此前农民对贵族的“劳役”关系并没有解除,形成一种权利与义务不相等的状况。农民们认为贵族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为了戍边征战扩充版图暂时让贵族拥有使用权,既然不打仗土地就应该“物归原主”。
1861年的农奴解放,农民的份地中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因此“分贵族土地”在1861年后是一种民间共识,沙皇政府也多次商议如何解决土地矛盾,其实早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与贵族的关系恶化,据说这个“反动沙皇”差一点就要剥夺贵族的“土地使用权”了。从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组织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这些名称就可以得知当时“分田地”的呼声有多高。
《颁布农奴解放法令》
自由主义尽管经济观点倾向市场与私有制,但也反对以强权化公为私。1905年立宪民主党成立时就对农民宣布说,“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土地+自由。”1906年新建立的俄国国家杜马围绕土地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农民议员团提出“劳动团104人”议案,要求国家剥夺“地主”。当时在杜马中居优势地位的立宪民主党对此表示同情,他们在国家杜马中呼吁要“纠正现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过立法无条件、强制性废除大地产。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无“平均地权”的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主义会消灭小农,代之以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农业资本主义化被理解为自由私产破除“共同体躯壳”即私有化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厌恶作为传统“共同体”的公社,支持私有化,希望加速农民分化。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885年劳动解放社党纲对农业只有“唯一要求”,即鼓励农民自由退社,而根本未提“地主”。至于“土地国有化”更是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动主张。
普列汉诺夫警告:“人民专制”下的“革命”可能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普列汉诺夫
当时俄国杜马中,只要稍微带有左派光谱的党派,从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民粹派后续组织的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党团的“劳动派”,无一不把“公平、公正解决土地问题”视为第一大要务。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几个党派提出:尽快尽早完成农民多年来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谓“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贵族割占原公社土地,“收回割地”就是把这些土地从地主那里夺回来还给农民。
当时就连那些被认为是保守的右翼党派也不敢放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原始链条的清白,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土地并不是合法积累起来的,只是强调“地主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不要盲目摧毁,或者用社会震荡较小的国家“赎买”方式来化解这一社会矛盾。也就是说,从1861年以后“分地主土地”是一种全民共识的“政治正确”,不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该派甚至一直疏离农民运动。
俄国农民是自发地仇视地主,而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言人是社会革命党。1907年沙俄在镇压了民主运动后推行“警察式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又使1/5的农民成为“独立农场主”,导致农民两极分化破产状况严重,农民对地主的仇视发展为对当局的仇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意识到农民的情绪可用。尽管如此,列-宁一派仍然未能有效介入农民当中。列宁承认说,“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主张”。
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特别代表会议并没有讨论分地问题。更何况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农村也只有203个支部,4122个党员,与在农村具有百万之众的社会革命党无法匹敌,所以即便它想去抢占农民运动的潮头,也无法与之争夺领导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民怨沸腾,沙皇权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笼罩在沙皇身上浪漫光环消散,基层法制松弛,各地已经自发地兴起“夺地”运动,政府已无暇顾及农民抢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来自国家的划拨和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化公为私的“割地”,而私有农民土地则来自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瓦解。这两次专制制度下的化公为私改革很不得民心,民间“开倒车”的“反改革”呼声一直就很高。战争期间政府自顾不暇,民间自发地就出现了利用传统村社剥夺地主和“富农”——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私有农民的浪潮。而这时地主早已成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给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为“不在地主”,要么贱卖抛售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继1905年的第一波夺地运动之后,1916年开始第二波分地高潮,各省的乡委会要求: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并把“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给乡委会支配”。皇权松弛后,农民提出来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复公社对独立农民的权威,重新回归农村公社。
史料明确记载,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意志并不在于消灭地主的肉体,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然而乡委会约束不了农民的行动,农村每天都会发生“农夫对老爷实行暴虐”事件。但是有组织杀人的案例并不是很多,也没有群众性“斗地主”的“情感渲染”,除了土地,被农民拿走的主要是农具和农业设备。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台而不受保护也都被当地的村社占有。总体而言,比起中国的“暴力土改”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当然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给农民土地。这是多年来反对派承诺过的主张!现在轮到他们第一次可以大展鸿图圆农民的梦,怎么能轻率行事呢?连列宁也承认“二月革命就已经向农民保证要给农民土地”。
临时政府答应,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战争状态下毫无规划的“乱分”,前方正在打仗时怎么分?如果在全国丈量、统一规划没有出来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张分土地,擅自改变土地制度,势必会造成农村和前线的双重紧张和动荡,造成不同区域间的苦乐不均,将直接关乎到战争输赢的结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农民稍作忍耐,等到战争尘埃落定,等到临时政府能站稳脚跟,就召开了立宪会议,进行了全国摸查,一定能够完成俄国农民等待了几百年的夙愿。“临时政府坚持认为重新分配土地必须以慎重和合法的方式来进行”。
3月13日清晨选出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前排右一为罗坚柯,左一为后来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后排右二为风云人物克伦斯基
临时政府针对农民自行占有土地的行为,在3月19日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中说:“土地问题不能用任何抢占的办法解决,……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土地问题”。它要求农民在法律的框架下有秩序有步骤合理地“分地”。
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农民停止焚烧地主庄园和分地活动,呼吁“不要把土地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变成随意私自占有土地”。其党魁切尔诺夫说,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幸的,他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有秩序地分配土地。切尔诺夫反对各地“自行夺地”。他号召农民耐心等待一个合理合法的时机,不要在战争中带来后方的“震动”。
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同意临时政府的主张,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擅自行为夺地、分地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
此时,农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后来者唯恐叫别人占了先机或者拿到土地者害怕得不到承认,于是发生了农民情绪的激进化的过程。绝大部分人赞同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据统计,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9·8%委员会维护地主的利益。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前,农民们已经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土地”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
也就是说,在列宁的“革命”一年前,在他还待在瑞士流亡地哀叹此生可能再见不到革命的时候,对斯托雷平改革满怀愤恨的俄国庄稼汉已经在后方“自发革命”、即展开了自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风潮。“到了1917年秋天”即临时政府末期,“农民骚乱已经遍及俄国县份的91%”。不但对地主5800万俄亩土地的夺占早已告成,而且对退社农民土地的收回重分都已经接近尾声。
19世纪末的俄罗斯农民
早在十月革命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俄国的土改就已经开始并完成了大半,这项运动既不是临时政府也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是农民依托传统农村公社组织集体行动,才造成如此大的冲击。现在俄国学者普遍认为,“在沙皇末期的1916年秋到1917年春,农民攻击地主的行动已基本完成,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并无影响”。
然而,主张合法分地的党派延误了时机,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钻了空子,当时党内的策略是:“抢占先机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在1917年8月底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才弥补性提出,在土地问题上承认“农民夺取土地的既成事实”。他们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进行阻抗,谁将会丧失群众的支持,因此在革命动员过程中,要不遗余力地拥护农民已经基本完成的“土改行动”。
鉴于革命后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地权”,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这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整看作是“土改”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的土改先于革命,而且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是农民自发完成的。这是与中国土改最大的不同,它也直接导致了俄国的战败。
布尔什维克天花乱坠的画饼,让农民心驰神往,一下子被认为是最理解农民的政党,但是他们策动革命的宣传目的达到之时,也就是许诺寿终正寝的时刻。就在1918年刚刚完成分地运动的农民,马上就面临着新政权“余粮收集制”的残酷打击,他们这才感觉到之前的许诺与支持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