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论俄国革命(八)
1932年10月23日,奥托.鲍威尔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一一对多尔富斯的回答》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鲍威尔对时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在议会中对他说的“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您从来没有真诚地信仰民主主义!”那句话的答复。鲍威尔是这样表达他的观点的:
“……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并不是仅仅在于策略上的考虑,即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以俄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为根据的,西欧和中欧不能模仿。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比一切策略上的考虑大得多,它是原则性的,是以我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观点为基础的,这就是:我珍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无可代替的价值。
“在人类最优秀的人物献出了自由和生命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中,欧洲各民族从国家和教会那里夺取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保证。”
……
“我的信念是:社会主义不应当摧毁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而必须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最珍贵的遗产保留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在摆脱了一切资本主义的伪造和一切资本主义的桎梏之后,才会得到充分发展并将显示全部创造力。
“每当我看到,俄国的专政排斥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兰诺夫这样的人,不准他们发言,仅仅因为他们在这个或者那个个别问题上持有与独裁者不同的意见,而他们丝毫不可能向俄国人民口头或者书面宣传他们的反对意见,或者在俄国人民面前为它辩护;每当我看到,俄国各地的一切学者在撤职、逮捕和流放的威胁下如何不得不根据独裁者的示意来放弃或者修改他们的社会学和哲学观点;每当我看到,可以不经法律手续,而用行政方式逮捕任何一个敢于发表不受政府欢迎的意见的俄国工人、农民和职员,并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正是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价值的珍惜把我和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
“为了个人精神自由的缘故,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制,它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议会制,并不只是法律机关的总和。它对我来说是为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提供最可靠保证的国家制度。它对我来说,就像我曾经在一篇被欧洲所有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用欧洲的所有语言加以传播的论文中说过的,是精神自由的珍贵容器。”
……
“但是,尽管我珍视精神自由,我也带着不可扑灭的仇恨痛恨资本主义。……
“……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通过行动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向世界人民证明:一国人民能够在自然资源和劳动手段不再属于资本而是属于社会全体、生产不再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支配而是受社会计划支配的社会制度下获得幸福,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在全世界获得难以抗拒的宣传力。那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
 “我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但我会不会忘记,是什么把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的?不会的。但是,我确信,如果苏维埃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在俄国取胜的将不是个人自由,不是精神自由,而只不过是白色专政取代红色专政。与此相反,如果苏维埃专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如果它能够逐渐战胜经济困难,改善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食品和商品供应,从而使危害当前建设工作的危险的紧张状态逐渐消除;如果从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接替了精神状态还是扎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老一代,那么,专政就会成为多余的并且可以取消。那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会重新掌握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没有这种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专政试图建立的、经济生活中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也不致遭到危险。
“我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但我会不会忘记,是什么把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的?不会的。但是,我确信,如果苏维埃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在俄国取胜的将不是个人自由,不是精神自由,而只不过是白色专政取代红色专政。与此相反,如果苏维埃专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如果它能够逐渐战胜经济困难,改善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食品和商品供应,从而使危害当前建设工作的危险的紧张状态逐渐消除;如果从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接替了精神状态还是扎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老一代,那么,专政就会成为多余的并且可以取消。那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会重新掌握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没有这种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专政试图建立的、经济生活中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也不致遭到危险。
“多尔富斯先生,这就是我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
(奥托.鲍威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缘于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无限向往。他虽然痛恨资本主义,但从他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中人们可以看出,他不是唯暴力论者。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正是他对个人精神自由价值的珍视把他与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者表示:“我不理解!”因为他知道这些被压制的人士实际上和他是同类人,他们并不是“阶级敌人”。在严酷的年代,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敌对势力施以专政,这是鲍威尔也理解并赞同的。但在政权巩固后,布尔什维克党却将暴力镇压施加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身上,活脱脱显示出一个独裁专制者的嘴脸,这是鲍威尔无法容忍、不能理解的。他说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认真研究了15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苏俄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相悖的。他在1934年发表的《民主制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民主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又提出了一些见解。)
这里摘录其要点如下:
我们把无产阶级民主制亦即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当作目的,这种民主制产生于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接受享有全部自由权的人民的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监督。但是我们可以预见,资产阶级的阶级反抗可能迫使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去运用一些手段,使无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会是怎样的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中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消亡,而是一种处于革命形势中的民主制、一种处于武装的无产阶级群众压力之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不再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像无产阶级民主制那样在保障全体公民的一切自由权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它在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劳动群众把民主制变成其意志的工具时用恐怖手段粉碎他们的反抗。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也是一种民主制。它是根据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来的,是以民主的自治机构和享有自由权为基础的。不过它也是革命形势中的民主制、内战中的民主制、武装工人监督下的民主制。这样的民主制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镇压资产阶级服务一一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像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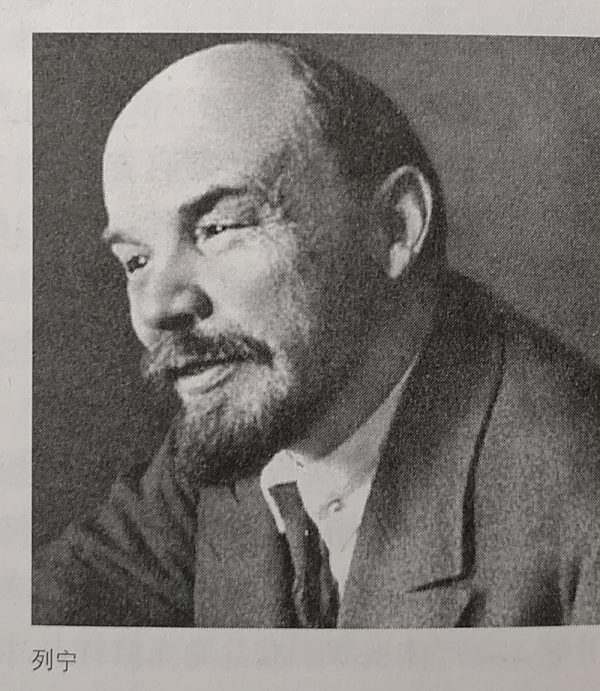 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设想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意义的。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直到1917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种专政理解为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而不是连劳动人民的民主也取消的一个党的专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一从罗莎.卢森堡到马尔托夫一一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而是反对俄国的这种专政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但是在俄国的条件下,发展成这种形式看来是必不可免的。……只有“极权”专政能使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并且反对任何的特殊利益,贯彻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措施。
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设想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意义的。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直到1917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种专政理解为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而不是连劳动人民的民主也取消的一个党的专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一从罗莎.卢森堡到马尔托夫一一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而是反对俄国的这种专政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但是在俄国的条件下,发展成这种形式看来是必不可免的。……只有“极权”专政能使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并且反对任何的特殊利益,贯彻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措施。
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必须采取哪种形式,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中取得政权,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就转变成无产阶级民主制。如果无产阶级民主制在对资本家和大地主实行剥夺时遇到反抗,那么无产阶级民主制就进一步发展成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如果这种反抗采取公开的国内战争形式或者甚至采取资本主义外国干涉的形式,那么劳动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极权”专政。
……只有当剥削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已经消灭,他们的反抗能力已被摧毁,全体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集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的“极权”专政才可能逐渐改造成劳动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在阶级对立消失了的时候又继续发展成社会主义民主制。
……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目的,也不能是目的。它只是工人阶级在其历史道路上必须用以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创造前提的手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过渡时期的制度。这个过渡时期将持续多久呢?
专政在苏联已经维持了17年。至今丝毫看不出它开始“自行消亡”,开始转向逐步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延续得像俄国一样长久。
……
因此,可以指望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不必延续得和苏联一样久。它应当延续多久当然是取决于人民群众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中进入专政。……一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愈高,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愈快地完成它的职能,因而愈快地“自行消灭”。
这样一种考虑决不是多余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我们愈是能使广大群众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一种仅仅暂时地、仅仅在不可避免的时间内采用来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即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创造前提的手段,我们就将能够战胜愈加广大的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反抗。
(鲍威尔在用了大量篇幅论述社会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思想、道路形式分歧后,注意到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分裂而产生的最大恶果:德意法西斯势力趁机崛起了。他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论述了他的“整体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一节中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
他在书中不无痛心地写道:
社会民主党人和CP人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斗争毁掉了阶级团结的感情。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一起反对CP的冲击,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它为了在议会的交易中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改良而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合作。社会民主党觉得自己与资产阶级政党比与CP的阶级同志更加贴近。……因此,尽管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但社会民主党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支持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拥护)制度的政党”。……
CP人在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援引俄国苏维埃的榜样作证。他们闭口不谈1917年在俄国使无产阶级能够取得专政的特殊混乱的局面,他们表现得就像只要无产阶级信任他们的领导,它就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间取得专政。他们闭口不谈苏联内部变革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一一即使在苏联不得不经历极度贫困的那一时期,他们也把苏维埃俄国说成是“工人的天堂”。他们没有把唯一能在俄国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伟大转变过程中的恐怖专政看作是为争取一个实现最完美的自由和人性的社会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没有把对个人自由、对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对全体人民自主的压制看作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一种沉重的、但是暂时不可避免的牺牲,而这是为了获得最完美的个人自由精神和全体人民真正的自主的,他们却诉诸群众的憎恨、暴力和仇恨本能,大肆赞扬专政和恐怖,大肆赞扬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主的压制,就像它们不是社会革命暂时的不可避免的手段,不是必须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一样。当面对法西斯反革命而捍卫自由已经变得很有必要时,他们还讥讽信奉自由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但恰恰因为CP人每天都在援引苏维埃俄国为证,才把社会民主党置于苏维埃俄国的对立面上。大多数社会民主政党都对俄国伟大的社会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不理解的态度。因为CP人把苏维埃俄国称为“工人的天堂”,所以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应该只向群众描述恐怖统治的残酷,描述俄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因为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期望和愿望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他们反对这一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开始实现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就完全黯然失色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力就这样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方面,人民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虽然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个“制度政党”,它的活动仅限于为工资和社会养老金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它认为CP人的名誉已经败坏:CP人利用绝望的群众没有判断能力而进行煽动,采取了肆无忌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政变策略,却没有权衡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导致了无产者阶层的失败和巨大的不幸。所以当1929年危机爆发,人们陷入贫困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未能利用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却被法西斯主义钻了空子。
作为危机的后果,当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威胁到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民主的合法性。……
而CP人的表现却像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法西斯主义直接威胁到民主时,他们仍旧把民主视为他们要打倒的敌人,仍旧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主要敌人”,而不是法西斯主义。……
但是当希特勒上台时,两大工人政党同时丧失了斗争能力。两者都屈服于反革命,甚至不敢尝试反抗。德国CP的革命者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一样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丧失了反抗能力和斗争能力。法西斯反革命恐怖使两者遭受同一命运。CP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长达15年之久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只剩下CP人的工人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的互相憎恶;这种互相憎恶即使在集中营里,在虐待双方的纳粹冲锋队的鞭子面前仍旧可耻地继续存在。
(鲍威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去世。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纳粹法西斯在德国上台执政一一这本来并非不可避免。当时各国CP都是严格按照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命令行事,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敌人,这就削弱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为右翼独裁政权铺平了道路。结果法西斯一上台,首先遭殃的就是CP。鲍威尔在上文论述中已指出,当时德国三大政党斗争非常激烈,莫斯科方面总是坚定地持宁愿要纳粹党也不要社会民主党的立场,禁止德国CP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在1932年11月那次关键性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CP在国会议员席中共有221席,而纳粹党占196席。如果CP与社会民主党实行合作,希特勒就不可能爬上政府总理的位置。正是由于CP人拒绝与社会民主党人联手反对纳粹党,结果使希特勒上台执政,摧毁了德国的民主政体。
鲍威尔虽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他仍对苏联抱有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情怀。他在文章中预言:“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同苏联结成了联盟。如果苏联参与战争,那么,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苏联能否胜利。它失败了,就会使无产阶级的最大希望破灭几十年;它胜利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将是不可抗拒的。……”
鲍威尔的这个预言在二战后基本实现了:战后不到五年,苏联、东欧八国及中国、北朝鲜、北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种共产主义鼎盛之势能维持壮大吗?
历史是不会依某些“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续完)
苏联政治笑话(34)
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街头,一条以色列瘦狗对一只来自苏联的北极犬问道:“你怎么也移居到我们这样贫瘠的地方来了呢?”那只北极犬回答道:“哦,在苏联虽然不愁吃,但我无法忍受的是,在那里既不能吠叫,更不能咆哮。”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27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