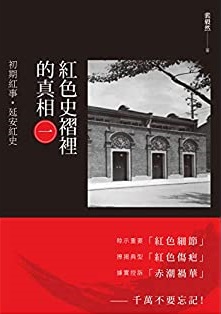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吴法宪回忆录》撩起长征真相一角
诸多中共红色神话中,二万五千里长征被长期神化,直至完全诗化的〈长征组歌〉——铁流滚滚所向披靡,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与藏彝民族关系融洽,云云。但是,许多负面史实被长期掩盖。港版《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7年)以亲历者撩起帷幕深深的一角,世人得窥那一截真正史实。
本来,数万红军乃江南客军,进入西南滇黔川康,一切吃穿用度必须就地解决,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是常识。由于刻意塑造高大形象,必须将红军说成始终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许多史实便成了不得不掖掖藏藏的「阴暗面」,成了必须「照顾大局」的政治禁区。空军司令吴法宪中将(1915~2004),最后十年写出回忆录,披露这一截史实,缀上红军长征史上一直缺失的一块补丁。
1935年6月,红军翻过夹金山进入藏区,等越过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已见不到一个汉人。
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藏民们都跑光了,家里东西却没法带走,粮食牛羊猪鸡,样样都有。一开始红军还能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庙里与藏民家的东西,但走了几天,从芦山、天全带出来的粮食吃完了,部队眼看就要断炊,心里不免矛盾起来——
一方面要讲纪律,另一方面部队又确实没有吃的。红军也是人,也必须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去行军打仗了。(页78)
一开始,红军从藏民地里挖些豌豆苗填肚子,但不能解决饥饿,下一步便发展到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
有人说那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能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页78)
再往前走,藏民得知红军一路「就地找食」,便把食物埋藏到山上,甚至锅碗瓢盆都带上山,藏寨一个个空空荡荡,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
没有吃的怎么办?为了生存,只能公开违犯纪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时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麦!凡是挖到这样的「大家伙」,一个部队拿不了,就赶紧通知另外一个部队来驮。有时油盐等物品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挖了以后,没有留钱,也没有留什么条子,只要能弄到就行,大家分了吃了。(页79)
由于红军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抓藏民牛羊、去挖埋地粮食,「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页79)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阿坝附近,被藏族骑兵打得一塌糊涂,向前过不去,后退又找不到吃的,饿了七八天后,六团官兵从上到下都不成人样,路都走不动了。全团1300人,只剩下五六百,死了一大半。
前往凤梨茨的路上,一些掉队红军士兵全被藏民杀死——
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进行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页82)
红军中还有不少逃兵。在凤梨茨,一个班对革命前途失望,集体拖枪逃跑。据博古、邓发、王稼祥等人说,「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出发的八万余人到遵义会议的三万余,大量减员主要就是逃兵。[1]进入藏区后,逃兵自然少了,离家远了,红一方面军兵源多为赣闽湘农民,没什么文化,不认路,回不去了,不可能逃了。
这一时期,红军没打什么仗,却严重减员,原因就是「找粮食」。一次,红二师五团政委带领团直属队去搞粮食,被藏民打死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十余人。师长陈光派人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赎人。藏人说不要钱,只要红军不再去搞粮食,他们就放人。
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到处搞粮食。刘少奇同志就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页84)
红军为了生存用尽一切办法寻找吃物,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朱瑞等则提出整顿军纪。吴法宪难捺怨气:
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还有什么纪律不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页85)
红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死一头猪,刘亚楼整顿纪律,全团大会上指控通讯员犯了纪律,枪毙了他。六十多年后,吴法宪还为这位通讯员叫冤:
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红一师三团首长黄永胜、林龙发上师部出席军纪整顿会,回团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页86)
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红三团停留三天,专门搞粮食。上级要求每人必须搞到15斤左右。但前面部队已将能搞的粮食搞尽了——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惟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
红军将这些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个摘下来,搓去外壳。吴法宪弄到大约八斤。由于青壮藏民都跑光了,红二师过草地只找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大娘当向导,一路上需要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
因为缺粮,过草地时红军多有饿毙,实在没吃的,一些掉队战士拨翻粪便、拣吃里面尚未完全消化的青稞麦粒。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吃进去青稞麦粒,拉出来还是麦粒,雨一淋,麦粒便在粪便中露出来,到河里洗洗,就能吃第二次。许多战士饿得实在无力行走,只能在草地「革命到头」。(页94)
吴法宪:
这一阶段确实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
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页96)
显然,吴法宪的记述很真实,可以用常识检验,合乎「求生本能」。笔者无意指摘红军那一阶段「军纪败坏」、「抢掠藏民」,也可以理解红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我不能容忍指鹿为马的捏造虚假,无法接受明明抢掠藏民粮食家畜,还说成「秋毫无犯」,尤其反感用艺术掩盖真相。直面这一截惨烈过程,有助于全面数点赤色革命所支付的代价,反思革命的必要性——代价的价值与意义。
回忆录还提及鲜为人知的一大负面事件。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之前,师参谋长周昆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领取全师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隐名埋姓,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页185)
再据范长江1936年访陕通讯,可知为何飞夺泸定不说对岸川军兵力?勇夺天险腊子口也不说守军兵力?原来,守备大渡河的杨森川军仅一营,且大部布防于渡口安顺场。本来南岸无船,安顺场团总自有一船,以为等红军来了再跑还来得及,不料红军神速,团总行动笨拙,被红军占了渡船。然河水太大,无人敢划船,红军重价征船夫,每划对河一次,领洋一百!重赏出勇夫,有人应命。可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攻杨森守兵,再顺势奔袭上游川康孔道泸定桥。
甘肃岷县白龙江腊子口,两岸绝壁,凿石壁间,至不能再凿处,乃架一小桥至对岸绝壁。如将小桥拆卸,数万红军至此,只能徒唤奈何。甘肃守军仅置一班兵力守险,缩踞小桥两侧碉堡,桥亦未拆,戒备甚懈,被红军奇袭而下。原来均是守军恃险轻敌,兵力极微。
中共长征史书均不介绍上述关键细节——既有损红军无往不胜的形象高度,亦有损军民鱼水的「阶级情」。此外,会理西昌一带,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之前,彝人打死近百红军,也是中共史书不愿记载希望淡却的一截。[2]
初稿:2008-2-14~15;增补:2009-8-18
[1] 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23。
[2]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90~191。
原载:《开放》(香港)2008年7月号(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