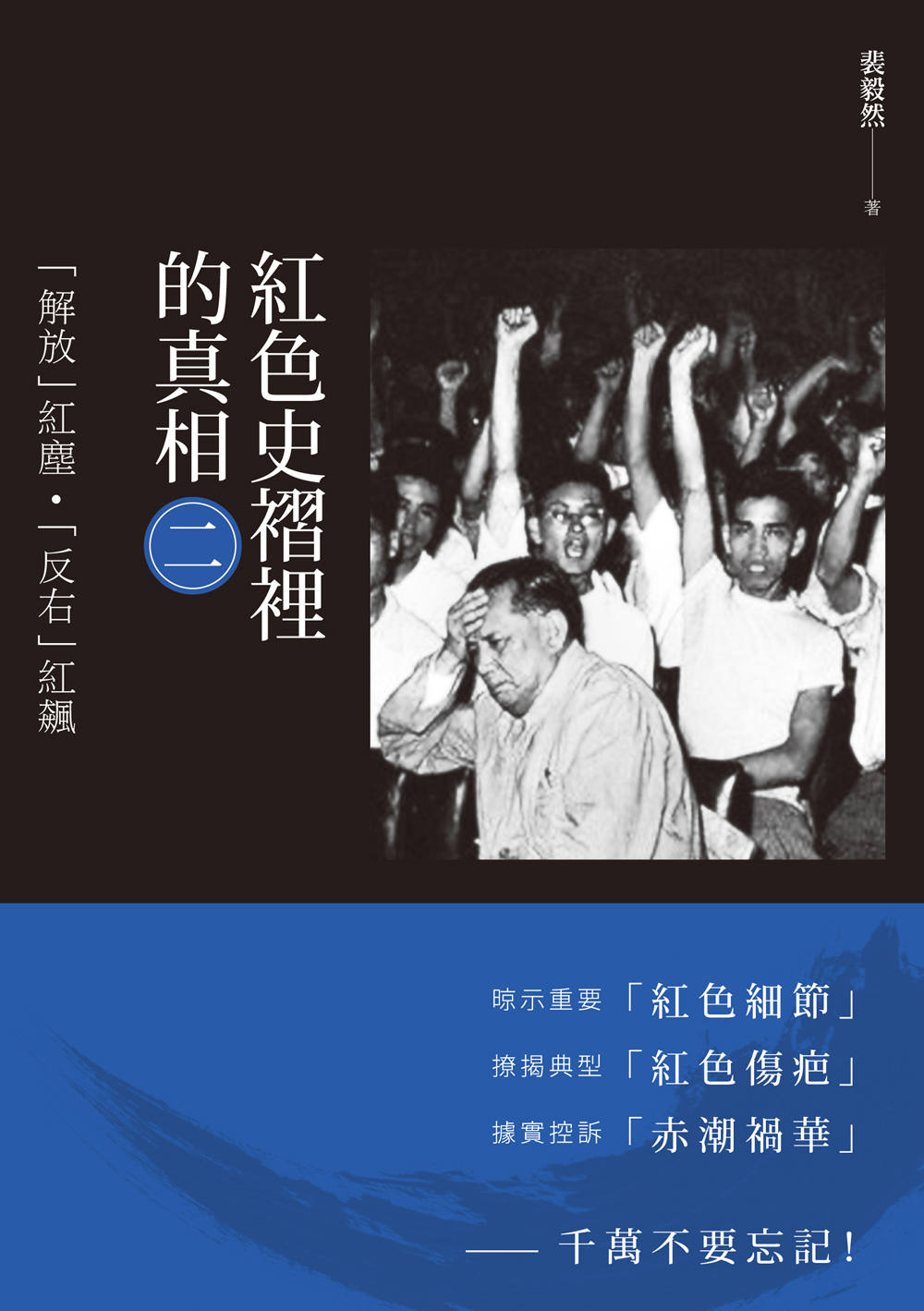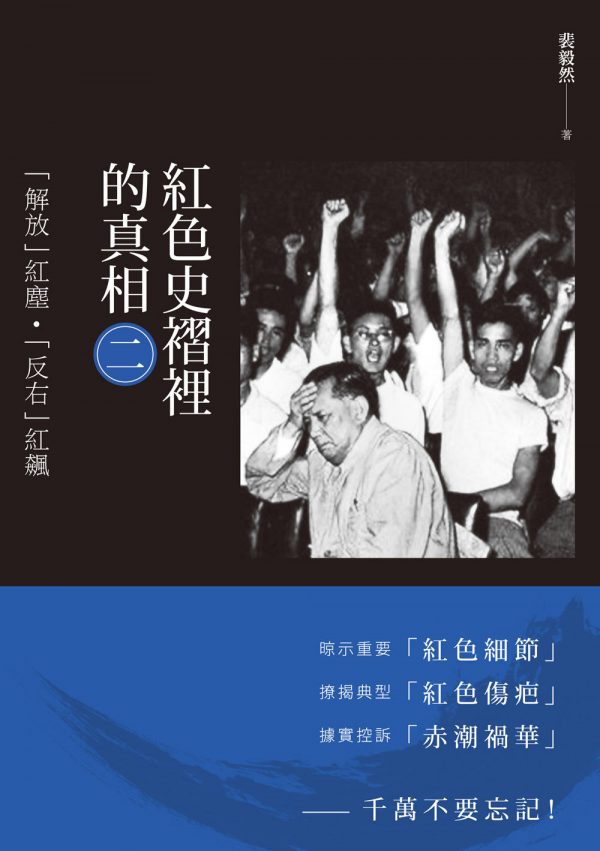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5)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5)
前后“十六字方针”——中共地下党的宿命
一、前“十六字方针”
抗战初期,延安对国统区地下党发出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为“前十六字方针”。[1]这一白区工作方针抗战前已具雏型。1936年3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就向部属发布这十六字。[2]1937年3月,闽西游击区领导人方方赴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也面喻此十六字,作为白区工作原则。[3]1940年5月5日,中共书记处电令各地省委:为隐蔽身分,加入国民党不必事先通过组织。其时,地下党乃中共不可或缺的“第五纵队”——搞情报、策兵运、扩组织、输物资、播赤化、发动学运工运折腾国民党、争取国统区民心、影响国际舆论……中共夺权尽管以武装斗争为主,毕竟还需要城市地下党的“第二条战线”,既需要白区帮着搞钱,也需要白区媒体的舆论配合,更需要白区知青“入伙”…… 1943年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4]
白区地下党员行走在监狱与刑场边缘。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内流传两句话:“二万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万五千里指长征,苏区武装斗争;三千六百日,指白区地下党,凶险十年。[5]
1938年3月入党的马识途(1915~ ),中央大学工学院二年级生,1941年初鄂西特委副书记,因叛徒出卖,特委书记何功伟、秘书刘惠馨(马识途妻)被捕,马识途遭追缉,上级钱瑛指示“远走高飞”,马识途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隐蔽潜伏。西南联大百余名党员及“红”出来的学生全撤离,党支部也没了。[6]1942年,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1909~1984,即郭华伦),被捕后叛变,致三十余名地下党员被捕(包括廖承志),周恩来在南方局重申“十六字”。闽西南大部分党员避入深山开荒,刘永生(1949年后福建省军区司令)等在永定老吴子深山垦植,粮食自给,还招待来往同志。[7]
二、后“十六字方针”
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二野”请示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原地下党?中央回电:“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是为“后十六字方针”。地下党系统从此遭整肃、受压制。由于明显过河拆桥,“后十六字方针”绝对机密,仅传达至大区负责人一级。[8]1949年后,地下党系统的干部一直感觉不对劲,冷风飕飕,频遭南下军干挤兑,整体吃瘪,但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万万想不到“母亲呵——党”竟会有这么一条“后十六字方针”。
1998年7月2日,马识途慨曰: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主力,却是先驱,起了号召、组织、发酵的作用。解放以前党的许多文件,都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也的确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新政权建立以后,原先满腔热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却往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对他们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天下”的时候,这些人英勇地对反动势力作斗争,尽了很大力量。“治天下”的时候,更需要他们贡献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偏偏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基本上是挨整的。……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通。[9]
随着政治运动递次展开,地下党逐渐公开沦为党内“异类”,一直受审查,没完没了,几无“漏网之鱼”。文革甚至传出:凡没成仁成烈的地下党,不是叛徒就是潜特。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登报为南京地下党平反。若非冤屈太深,影响太大,这种“家丑”,中共岂愿“广而告之”?
共军渡江,接收“烂摊子”,百废待兴,干部缺口百余万。1949年,中共党员300万,70%来自农村,仅11%受过教育;这11%中,仅1%大学生。[10]国民党时期官吏总数200万,中共此时仅72万合格人员,缺口2/3。[11]偏偏弃用熟悉城市的地下党知识干部,或控而用之。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200名干部及南京军管会名单来宁,37席职位,仅5名原地下党,且多为副职。[12]攻占上海后,毛泽东明确接收城市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确保嫡系对各地的绝对掌控。[13]
整肃地下党的公开理由是大批新党员乃国民党大势已去时加入,“动机不纯,成分复杂”,混入不少国民党“第五纵队”。另一不便说出口的理由:我们共产党不就这么干的——“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不是有着名的前后“龙潭三杰”?[14]1946年夏,西安地下党的电台甚至设在国民党的“剿共”司令部。[15]
三、邓小平报告
1949年9月17日,南京四千人大会,党支书及排以上党员干部出席,“二野”政委兼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长篇报告〈论《忠诚与老实》〉,意在解决南下军干与南京地下党日益显豁的矛盾冲突。邓报告打压地下党,明确要求地下党必须服从南下军干,为全面整顿南京地下党造势。
1946年恢复南京市委前,中共南京地下党员仅二百余,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发展至近两千,“重大业绩”这会儿成了大错误。邓政委报告中:“南京是否两千多党员,一个应该清洗的也没有呢?”邓还将柯庆施散播的谣传拈出爆料:
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就当厂长”……这样说你保管好总统府,将来岂不是要请你当当总统吗?[16]
陈修良气极,递条上台反驳。[17]邓接阅后立即揶揄:
我们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听了不舒服,那么,让他不舒服好了,将来等到他变成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舒服了。[18]
老资格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1908~1988,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不久告知陈修良:邓小平对她“印象极为恶劣”。后来,刘晓又通过沙文汉(陈修良丈夫)提醒她,“在邓小平、饶漱石面前说话当心点”。[19]
邓在报告中警告新党员:“党有严格的纪律,如果别的都可以,就是『自由』这一点我还要,那可以不必入党。”邓着重分析了毛泽东所说的三种党员:“一条心”——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忠诚者。“半条心”——组织入党而思想不入党,求官或要求党“给生活”;入党后还想保持言行自由、传布反党言论。“两条心”——钻进党内的破坏者(潜特)。邓特别指出:“南京党内两条心是有的,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谁就要使自己解除武装丧失警惕!”邓还说“半条心”是“两条心”的掩护者,举了两则失实事例。[20]有关几条心的说法,延安抢救运动就已出现。
陈修良听完邓政委的报告,“气得发抖,但没有办法能够向这样一个‘大人物’进行辩论,澄清真相,讨回公道。”她既震惊,又莫大痛苦,这么一位战功卓著的中央级领导,竟会根据几条谣言公开恶评整个南京地下党。会场走光人了,她还呆呆坐在那里。[21]她万万没想到“胜利会师”,竟会遭遇自己人如此“误解”。
邓报告中还称部队军干、南下干部为“大儿子”,南方游击队、地下党为“小儿子”——
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北方来的党叫做主力,在南方的党和部队叫游击队,会师就是主力和游击队的会师。你说毛主席偏心吗?不是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这就叫“老老实实”。
干部配备是以什么为主呢?应该以解放军来的、解放区来的干部为主,不仅南京、上海、杭州这样,将来到西南也必须这样。
邓特意谈到攻占南京的功劳:第一是毛主席;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南京地下党;地下党只是起了“适当的作用”。邓严厉批评地下党对军队干部的不服气情绪。[22]
邓报告1.8万字,邓氏篇幅最长的文章。1988年出版《邓选》,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拟收入这篇〈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党史办征求陈修良意见,陈逐条批驳错误,明确反对收入。历史最终证明南京地下党未混入一个“两条心”,这篇最长邓文未入《邓选》。[23]此时 ,“总设计师”健在,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
四、南京整党
城市地下党有文化有经验,熟悉城市,但不像军干及根据地工农干部那样听话。陈修良偌大场合递条上台,也只有深具平等意识的知识分子才做得出。估计邓小平很少遇到这样的下属,因而对陈“印象极差”。
上有毛泽东的“后十六字方针”,下有工农军干庞大基层力量,华东局顺势打压地下党,便是时代大气压下的“历史必然”。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南京一“解放”,立即“降级安排”,降任市委组织部长。邓报告后,陈修良又在与军干关系上挨批评,1950年初调离南京。反右时,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陈修良与丈夫沙文汉(浙江省长)一起划“右”,陈修良还是“极右”。陈修良1926年入团,次年转党,向警予秘书,她划“极右”须经中央审批,得经过总书记邓小平。
1949年9月~1950年,南京整党未查出一名反革命,但仍“战果辉煌”,除随“二野”赴西南走了约500名党员,1400余名南京地下党员,466人受处理,其中205名开除党籍。[24]其他处理等级:取消候补资格、劝退、停止党籍待审。此后历次政治运动,南京地下党干部几乎一网打尽,少数“漏网之鱼”,或明或暗“控制使用”。
随“二野”西征或南下的南京地下党干部亦未幸免。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云南省委撰文纪念西南服务团,该团以南京地下党及红青为骨干。该文复述邓小平1949年南京讲话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划分六类——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引起原西南服务团老同志强烈抗议。云南剿匪中,西南服务团牺牲九十多人,幸存者不少仍沦为“右派”,发配穷乡僻壤苦役,有些人无声无息死在远方 。 [25]
这次南京整党,公安局发现一名地下党员曾为蒋介石接过电话,便认定“特务”而逮捕,文革后才洗清冤情,从流放地回南京,人生主要时间都消耗于监狱。另一名工作出色的地下党员,南京“解放”后任公安局邮政科长,同单位一名南下军干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一次吵架,科长将手枪往桌上拍了一下,被指“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科长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陈修良调查此事,确认误会谣传,不是“反革命”,但邓小平仍在“四千人大会”上拎出,举为地下党不服南下军干的例子。整党运动中,这位地下党出身的科长被整得死去活来,自杀了。[26]
五、全国情况
南京市委组织部有人听传达:中央点名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其他未被点名地区的地下党亦难逃劫数。
1949年7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判定本省地下党质量不高,80%一年以内新党员,预备党员占60%,发展过快,明显“拉伕”,个别地方伪县长、民社党、自首分子都进来了,组织性差、阶级立场不稳,必须严格政审与组织清理;[27]对地下党员的任用,尽量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群众关系多的长项,一般不宜留机关,有能力者一般也只应配置副职,确实德才兼备且工作上不可缺少者,“应视作特殊情况,经过党委研究提交上级批准后,可以分配负责工作。”[28]
抗战后成立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以知青为骨干,最后发展成五万余人,县区民兵十万余,十二块游击区,攻占91座县城。[29]1949年后,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文革等运动,云南地下党与“边纵”一直是重点审查对象,定性“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122名省管干部划“右”。文革时历届地下党工委委员、边区委员、“边纵”地委、支队领导“都属叛徒、特嫌”,大批长期关押,不少迫害致死。“代表人物”省纪委书记郑伯克(1909~2008),1929年入团,1935年入党,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边纵”副政委,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谢富治整肃,几乎开除党籍。连坚持实事求是、不肯无中生有“揭发”的南下干部、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也被打为“郑王反党集团首要分子”。1982~92年,云南复查地下党及“边纵”2.9万余人次,改正80%。[30]
1978年,闽中地下党负责人仍被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福建地下党冤案涉及千余地下党员,大多为厦门大学、集美等学生。四川地下党员约1.2万名,次次运动挨整,1980年代初只剩下2000余人。江青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文革中,一位军区司令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广东、海南的地下党也遭“反地方主义”整肃。广西抗战期间的“学生军”冤案、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冤案,都是1980年代才得昭雪。[31]
文革前,地下党因熬刑、牺牲颇能体现红色意志与革命艰难,《红岩》三年印行400多万册。[32] 马识途以鄂西地下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印20万册,《成都晚报》、《武汉晚报》连载,中央及几个地方电台连播。文革开始后,《清江壮歌》与《红岩》一起沦为大毒草,地下党题材作品与地下党政治脉跳“同呼吸共命运”。[33]
1982~84年,笔者供职浙江省政协,一批新四军“三五支队”浙江地方干部,深怨前省委书记江华对他们长年压制。浙江四大“右派”沙杨彭孙——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检察长彭瑞林、财贸部长孙章录,除彭瑞林,均为地下党出身。
熬过毛时代的地下党幸存者,文革后才有机会崭露头角,如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出身的王汉斌(副委员长)、何东昌(教育部长)、清华生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
六、求证坐实
受了三十年冤屈的地下党员闻知“后十六字方针”,当然很有“兴趣”知晓其详。2004年秋,穆广仁先生从友人通信中与闻“后十六字方针”,便和几位南方局地下党出身的老干部开始“求证”。
穆广仁(1925~ ),1947年入党,南方局地下党员、新华社前副总编。因档案封闭,穆广仁等只能寻证知情人。陈修良之女打电话咨询消息来源的老H,老H告知信息来自昆明M。昆明M再告知穆老,“情报”来自一位见过“后十六字”文件的西南局老同志。一位1950年代安全部门的老同志也说闻知“后十六字”。一位搞党史的南京老同志告诉穆广仁,19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负责人C查阅档案时,发现南京易手不久一份电报,中央某领导向毛请示对全国地下党的处置方针,毛批下这十六字,限达大区负责人。
李普应穆广仁之请,咨询1950年代初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1913~2015),杜老回答亲见“后十六字方针”文件。2006年2月,杜润生向李普确认亲见此件。李普(1918~2010,新华社副社长):从“后十六字方针”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行文习惯一致,只能是他的手笔;从内容上,他人没有资格与胆略敢发布这样的指示。再根据毛对知识分子一贯偏见与1949年后历次运动矛头,前后衔接,逻辑一致。李慎之认为“后十六字方针”并非仅仅针对南京地下党,而是针对全国地下党。[34]
大陆史家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收入“后十六字方针”,附长篇确认性论述。[35]根据大陆“国情”,中宣部对党史审读极严,“放”出如此重大情节,表明官方认可。
综上,“后十六字方针”基本坐实。档案一旦解密,当能查到电报原件。
七、悲愤出集
忠诚的地下党员晚年得知“伟大领袖”早就准备淘汰他们,开国之初就规划如此这般对待革命摇篮的地下党,将他们第一批送上“无产阶级专政”祭坛,文革则是“淘汰”的最后一章[36],那份锥心之痛……当年出生入死、舍身为党的壮烈价值,全都漂起来了。
何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等地下党出身老干部历经二十年努力,2005年后陆续出版“晚霞工程”——《红岩儿女》(六卷本)。这套传记丛书,大陆只给出1949年前“英勇奋斗”的前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不给出1949年后“含冤蒙难”的后两卷。“伟大母亲”只承认他们的前半生,却“回避”时间更长、更有“价值”的后半生。第三部《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2008年只能出版于香港。
红色女杰陈修良(1907~1998),1926年春入团,1927年4月向警予介绍转党并任向秘书,留苏生;1994年5月5日、1998年10月8日,江泽民两次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榻前探望。[37]其自传《拒绝奴性》亦不能出在“莺歌燕舞”的大陆,2012年只能露脸于“资本主义渊薮”的香港。大陆官家至今害怕自己的历史,不便“见公婆”之处太多。
八、深层原因
李慎之、李普、燕凌、穆广仁等“两头真”晚年认识到“后十六字方针”的根子在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毛从实践中认识到工农干部听话、麻烦少、没威胁。起于深山草莽的中共,主要依赖农民与军队“说话”。利用历史形成的多数工农干部去整肃少数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干部,亦合1949年后中共人事上的既成态势。1955年上海“潘扬事件”,也是这一背景下的“历史产物”——起于不信任的大冤案。
1980年代,穆广仁随上海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出身的外长吴学谦出访埃及,有一次深入的“开罗交谈”。他们为地下党的集体命运感慨不已。地下党不仅为中共夺权作出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培养大批干部,1950~70年代正是他们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段,却成为党内第一批祭品。较之“一二·九”延安一代,地下党系统的命运悲惨得多。等到胡耀邦时代提出知识化,地下党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大多岁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很少一部分出任重要职务,这部分地下党员干部昙花一现,很快离休。[38]
当然,革命早就在吃自己的儿女了。十年“闹红”,各根据地“肃反”杀掉自己人近十万,远比国民党监狱杀的共产党多得多。1932年1月~1934年夏,湘鄂西苏区“肃清改组派”,冤杀上万名红军与根据地干部,领导人夏曦连自己的四名警卫员都捕杀三人。九千余人的红三军杀得最后只剩下三千余,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位。一位湘鄂西根据地开创者临刑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根据地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都是反革命?夏曦答曰:“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了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了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39]如此悖谬逻辑居然成为大开杀戒的论据。夏曦甚至差点对贺龙下手。
李锐——
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误杀了4.5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地,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40]
延安整风审干,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打“红旗特务”,整得死去活来,自杀前留下绝命诗——
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
后为中纪委书记的韩天石(1914~2010),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延安“抢救运动”也打为“红旗特务”,1949年后划入“高饶反党集团”。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抢救运动”中险些“入围”,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力保,才成“漏网之鱼”。[41]
地下党的集体命运,难道唏嘘一番、叹一口气就算了?不该找找里面的原因么?中共不是最讲客观规律与必然性么?这会儿怎么不言言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乃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民主自由是他们争取的目标。1940年代入党的南方局系统学生党员,未经延安“整风”、“抢救”,不知运动厉害,有话直说,不加防范,1949年后成为“槛上芝兰”。[42]当他们被赤左大潮裹挟至反右、文革,发现“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而且比原来都不如,来不及了,眼睁睁看着战友一个个被“合法冤枉”,最后冤枉到自己,株连亲友后代。此时,他们只能啃嚼苦果,熬着受着了。
工农“打败”知识分子,马识途认为根子在于治国策略上发生原则性错歧,即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因素上发生原则性分歧——
这样,革命知识分子就与小农意识、封建意识深厚而又居于支配地位的那些人发生矛盾了。那些人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非要“改造”、打击这些知识分子不可。本来,进城之后更应改造的是农民意识、封建意识,这些没有改造,反而用这些意识“改造”知识分子,怎能不出麻烦?……超越阶段,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搞出个充满农民意识、封建意识的社会,弄成个事事高度集中、专制盛行的国家,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挨整是跑不脱的。……几十年来,各地各级仍然有大大小小的“皇帝”压在人民头上,不少乡村里,至今还有。[43]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分歧呢?先后就读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的高才生马识途无法回答,因为已接近“两头真”的反思底线——赤色革命的正义性、中国共运的价值性、马列主义的合理性……一开始就错了?哎唷,天都塌了喂!折腾这么一大圈,撵“国”立“共”,最后还是绕回来,红色专政比白色恐怖还厉害、更升级,这?这!这……
九、“红岩一代”的局限
笔者曾与几位“两头真”老人接触,小心探问,摸知他们反思的两条底线:一、马克思主义;二、革命价值。“红岩一代”(即“解放一代”)意识到自己带有根本性弱点——1949年前不怕牺牲争取民主自由,1949年后竟容忍新式独裁专制;1949年前张扬个性、桀骜不逊,1949年后竟沉陷个人迷信、乖乖成为“驯服工具”;他们自问:“明明被整得死去活来,为什么久久不觉悟”?承认“浪费青春”,但拒绝被评“上当受骗的一代”。他们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自评:“他们理想中的目标大部分未能实现,但却很难说他们当初就作了错误的选择。”[44]
他们最后的底线:推翻国民党还是必要的,后面没建设好“新中国”不能成为否定前面红色革命必要性的理据,1949年前后得分开来——
能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来证明四十年代共产党的民主说辞都是假的吗?用后来的情况推论过去的动机,用后来的表现评价过去的对错,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对待历史的态度。[45]
他们的论点当然经不起轻问:既然大部分目标未能实现,又怎么证明当初选择的正确?既然后来的结果背离此前宗旨,再美好的动机还有什么意义?天翻地覆、伏尸千万的革命,能用“动机”来论证价值么?难道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么?
回避理论归纳与人生“总决算”,似成“延安一代”、“红岩一代”捍卫一生价值的“最后防线”,或曰代际局限吧?李慎之、谢韬都已承认“英特纳雄耐尔”不可能实现,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要送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东西”,[46]就是未对一层纸后的马列主义、国际共运(包括中共革命)的价值进行总判认总决算。
赤潮祸华,最实质性的伤害是拧歪了数代士林的思想,错误架设他们的判断标准。“延安一代”、“红岩一代”至今还在用阶级论研判社会,还在用赤色观念运行思维、影响今世、“教育”后代。
结语
很清楚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党专政、禁止私产、一切公有、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已被证谬,难以“继承”。一开始就走歪的赤色革命,以阶级划敌,当然不可能走向“和谐”。先打倒别人,再打倒自己,实为地下党的历史宿命。反右~文革,难道不是再熟悉不过的鸟尽弓藏?一齣旧戏耳。
这场“先打倒别人,再打倒自己”的革命,当然也是一笔“丰厚”的红色遗产。缴纳如此巨额历史学费,难道还不该好好利用?——深究赤因,刨去祸根。否则,后人很有可能还会在原地跌摔第二跤。
初稿:2010-12-22,补充:2013-11-22~25,修订:2014-1-10~13
[1]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8月新版,页709。
[2] 张友渔:〈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革命回忆录》第2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5。
[3] 方方:〈三年游击战争〉,《红旗飘飘》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年,页137。
[4]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六十周年〉,《人民日报》(北京)1981年7月3日。参见山西省社科所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
[5] 杨超:〈在西南四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页42。
[6] 马识途:《风雨人生》,《马识途文集》第九集(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364~365。
[7] 谢毕真:〈战斗在闽粤赣边的刘永生〉,《革命回忆录》第16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18~119。
[8]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09~710。
[9] 马识途:〈有感于四十年代民主运动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01。
[10]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27。
[11]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英)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76。
[12] 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8期,页75。
[13] 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79。
[14] 抗战前“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家、胡底。抗战后“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15] 庞智:〈古城斗“胡骑”——西安地下斗争片断回忆〉,《红旗飘飘》第16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61年,页217、240。
[16] 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载南京市委编印:《南京通讯》第四期(1949年10月),页17~19、9。参见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67~268。
[17] 2014年1月11日,陈修良之女沙尚之函复笔者:其母亲此时向主席台递条子。
[18] 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市委编印:《南京通讯》第四期(1949年10月),页11。
[19] 陈修良遗稿:〈关于邓小平问题〉,未刊稿。载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77。
[20] 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市委编印:《南京通讯》第四期(1949年10月),页8~10。
[21] 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73。
[22] 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市委编印:《南京通讯》1949年第4期,页18~19。
[23] 陈修良致南京党史办公室的信(1988年2月24日),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68、271。
[24] 南京市委党史编写领导小组吴文熙1985年6月24日给陈修良的信,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陈修良传》,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278。
[25]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8月新版,页713。
[26] 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8期,页76。
[27] 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我们进入湖南与地下党会师的几个问题〉(1949年7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党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二卷,2006年9月,页34~36。
转引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401。
[28] 湖南省委:〈关于与地下党会师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1949年9月12日),〈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二卷,2006年9月,页39~40。
转引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401。
[29] 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二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8月新版,页736。
[30] 〈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冤案纪略〉,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上),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80~81。
[31]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12~714。
[32] 旷晨、潘良编著:《我们的195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6年第二版,页311。
[33] 马识途:《风雨人生》,《马识途文集》第九集(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288、327~328。
[34] 穆广仁集纳:〈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09~710。
[35]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400~404。
[36]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载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14。
[37] 沙尚之主编:《沙文汉、陈修良画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页18、21、162。
[38]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714~715。
[39] 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97。
[40] 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58。
[41] 穆廣仁:〈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燕淩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713~714。
[42] 謝韜:〈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燕淩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上),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15。
[43] 燕淩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下),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703。
[44] 燕淩執筆:〈《紅岩兒女》第三部前言〉,《紅岩兒女》第三部,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3~4。
[45] 燕淩:〈謝韜一代人的追求〉,燕淩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上),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32。
[46] 謝韜:〈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燕淩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上),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頁29、27。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4年8月号(删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