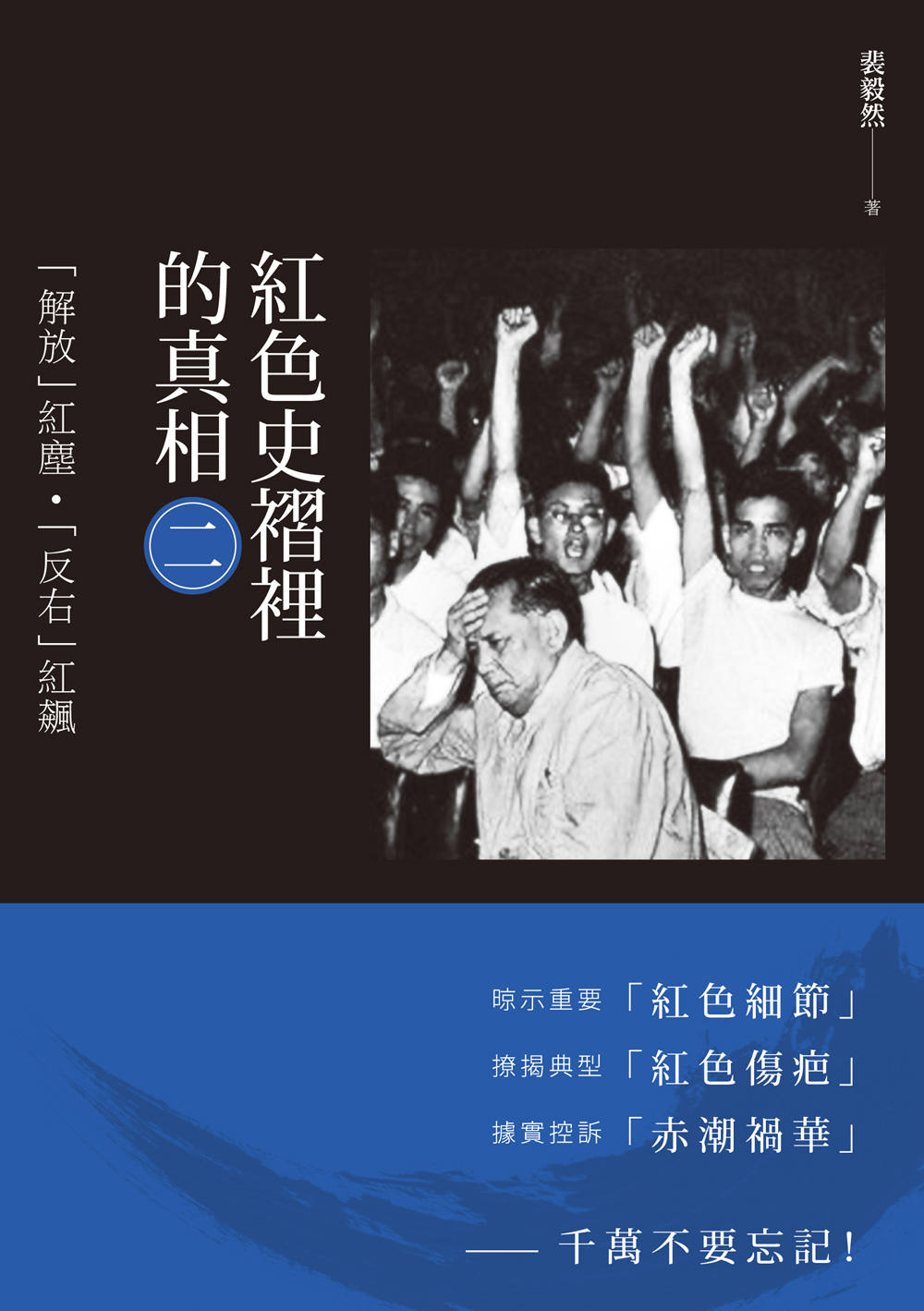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5)
“右派杀人犯”与白茅岭冤案
出身雇农的黄宗奇(?~1958),1948年加入中共,1954年以调干生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绩优秀。因是1949年以前的党员,甚得重用,“反右”领导小组长。“反右”伊始,他反对人身攻击、允许批判对象申辩、不搞动手武斗,被指“同情右派”,竟亦划“右”,从革命力量沦为打击物件。怕他想不开,安排同学看押,限制自由。1957年6月下旬被捕,1958年枪决。案情如下——
黄宗奇划“右”后,实行“群众专政”,同学轮流看管。他情绪激动,因冤而愤,无法转弯子,吵着嚷着要自杀。一天,他企图从厕所跳窗,看管他的同学从后面一把抱住,情急之下,黄宗奇掏出铅笔小刀,向后一划,划破“看守”的脸,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一把削笔小刀怎能杀人?但为证明“右派”的凶残与反扑、证明“反右”的必要性,这点小事硬被渲染成“右派杀人”,做足文章,枪决镇压!绑缚刑场前,黄宗奇交待妻子:
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9年“右派”改正,落实政策,承认杀错人,赔偿其子两千元。[1]
法院为判刑“右派”平反,前提原单位必须先撤销“右派”,法院再根据原单位的“错划”宣布“错判”。原单位如“坚持真理”不予改正,法院也爱莫能助。而各单位掌权者多为1957年“反右”中青年骨干,正年富力强,申冤者又是自己一手打下去的“阶级敌人”,要他们自纠错误,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拖捱赖蹭,最后再耍一把当权者威风,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痛快给你办“改正”。黄宗奇因“错划”而“错判”而“错杀”,错度越大,纠错越难,阻力越强,衙门层层,关隘重重。
中共名义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羊头挂得很高,口号响彻云霄,实质向无追责制。“反右”乃全国政策性错误,“右派”改正并不具体追责任何个人,所有罪误都归于一个词——“扩大化”。一场塌天大祸的当代文字狱、殃及至少55万“右派”及其家人的赤难,最后竟无一人担责!能够为“右派”改正,恢复你身分待遇,替死者恢复名誉,已是我党又一次“伟光正”,55万右派及其家人领到的所有补偿只有三个字——“朝前看”!
与黄宗奇一字之差的清初黄宗羲(1610~1695),与满清皇朝对抗到底,屡拒清廷征召(包括康熙钦点),白纸黑字写下大逆之语:“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康熙也没拿他怎样,85岁天寿终老,且以明臣殡仪安葬。三百年后的黄宗寄,所谓“反动”不过自杀时划破阻拦者一点皮,“待遇”相差如斯!毛共自称彻底反封建,竟远比封建时代更封建更残暴。
北大西语系学生“右派”顾文选(1934~1970),1966年夏从河北清河劳改农场逃走,越境后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叛变投敌、出卖情报)处死。北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张锡琨,1977年企图越狱被处死,遗体由妹妹领回。[2]北大西语系学生“右派”贺咏增,大会宣布逮捕,文革在京郊劳改队屡挨批斗,生不如死,爬上几十米烟囱,大呼口号,当着围观者跃身而下,拍地而死。[3]
白茅岭冤案
皖东南郎溪与广德两县交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隶属上海劳改局,文革期间既看押服刑劳改犯,也为“劳改释放犯”提供就业,俗称“二劳改”。1977年,白茅岭总场公判大会,“现行反革命”姚莲蒂(26岁姑娘),判决死刑,就地正法。案情如下——
枫树岭分场关押女犯,发现“反标”(反动标语),狱方如临大敌,对笔迹、查档案,上海劳改局也派来项目组。但在项目组开来的吉普车上居然也出现“反标”,顶风作案,气焰嚣张。项目组豪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摸排过筛,出生反动家庭的姚莲蒂浮出水面。姚父乃国民党军官,判刑八年,刑满后就业白茅岭农场“二劳改”;姚母因对抗文革被枪毙。姚姑娘与无产阶级专政有“血仇”,被捕后,情绪极其抵触,常嚷嚷“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因此,认定姚莲蒂既有阶级根源,也有“相关口供”,最可疑。
审讯中,姚莲蒂对指控并不推托,一口嚷嚷:“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于是,这位上海女初中生成了办案者的立功资本。执行枪决时,上海开来医院面包车,停在刑场边,行刑一结束,两位白大褂立即挖去眼珠(可能要角膜),面包车迅速绝尘而去,大概某高干有“革命需要”。
行刑当晚,枫树岭农场一女场员自杀而亡,她才是“反标”作案人—— 一位被“政府”绝对信任的积极分子。此人良心发现,自行了断——“一命抵一命”。据说,上海方面有“停止执行”的急令,晚到一天,未能刀下留人。[4]
2008-4下旬·上海(后增补)
[1]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四卷,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页59~62。
[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8年第2版,上卷,页168。
[3] 张强华:《炼狱人生》,中国三峡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3。
[4] 张强华:《炼狱人生》,中国三峡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85~287。
原载:《前哨》(香港)2008年第11期(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