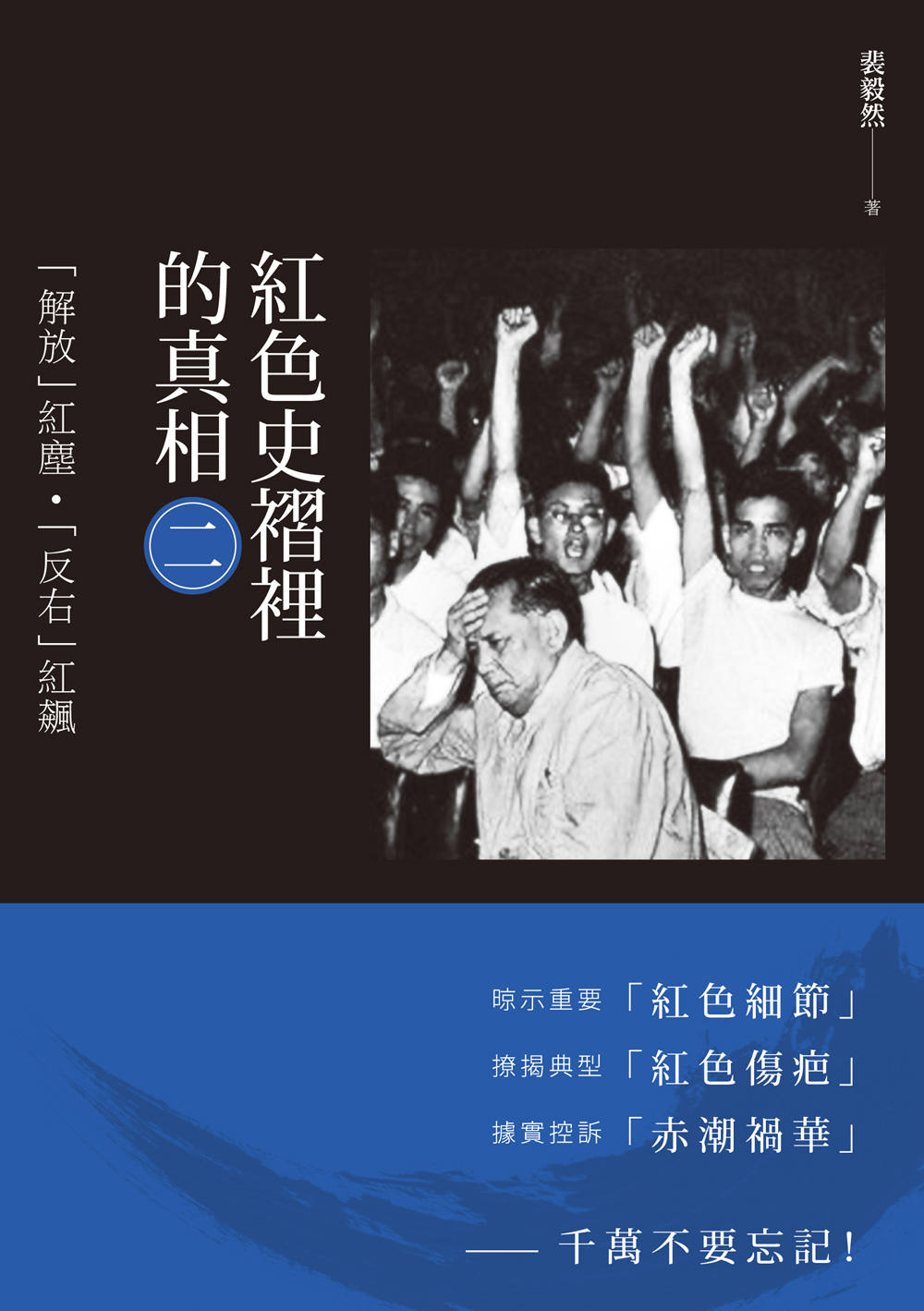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9)
顾准的人格
“伟大毛时代”,长夜沉沉,顾准一灯如豆。能在那个年代坚持独立思考,质疑计划经济、思考民主,为红色士林多少耸起一点脊梁的,只有一位顾准(1915~1974)。1965年9月,他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就读北京101中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红领巾。妻子汪璧(1914~1968)为了孩子,被迫提出离婚。顾准誉为“叫花子吃鸭子——只只好”的五子女,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坚决不认其父,革命群众更是痛斗痛打,真正众叛亲离。
离婚后,顾准瑟缩独居于集体宿舍,自谓“丧家之犬”,欲效法捷耶夫[1],数动死念。绝境中的顾准,人格仍熠熠发光,与其相处十年的吴敬琏记载了一则非常感人的故事。
1968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顾准一位老朋友兼老上司林里夫,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指斥他1930年代就是“内奸”,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弄得顾准百口难辨。直到周扬文革后平反,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顾准从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回京,对林里夫却多方照顾。考虑老友处境也不佳,寂寞凄苦,逢年过节总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吴敬琏很不以为然,认为顾准完全不必当东郭先生,对这样的人,不去回敬一拳已算仁慈。顾准却说:
你真不懂世事,他这种古怪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审干”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悲惨的人生遭遇形成他古怪脾性,应当同情才是,怎可苛责?[2]
古谚:“时穷节乃见”。能够在互斗互咬只求自保的漩涡中,清醒认识到对方负荷的压力,宽宥对自己的伤害,不仅需要仁慈人格,更是一种能力,才能达到入圣境界。林里夫(1909~2001),就读北大、留学日本,1920年代末加入中共,1930年代从事地下活动,抗战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宋庆龄主席)党团书记,顾准入党介绍人。
因顾准的“恕道”,老战友的情谊得以维系。1974年10月中旬,顾准病倒,林里夫每天赶到社科院经济所顾准宿舍,为其炊煮,照料生活。顾准住院后,经济所虽派专人照顾,林里夫仍每天三次看望照料。顾弟陈敏之从上海赶来,林里夫每天下班辄上医院探望,后又派其女每天上午顶替陈敏之照看顾准。其时,林里夫的政治处境也很艰难,经济条件尤窘。顾准遗嘱赠老友伍百元(相当一工人年薪)。
达到顾准的恕境,得有思想根源。顾准从现实中认识到不应一味强调斗争,应提倡宽恕。他认定世界最终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因此,他的座右铭——“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一次,女同事张纯音与顾准争论:
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再将右脸递上去,完全是一种奴隶哲学。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顾准答:
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斗争不已。如果大家都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3]
顾准借给张纯音中英文对照版《新旧约全书》,建议她读一读。顾准从实际生活中意识到:宽恕是必要的绝对的,斗争是策略的相对的。人格的背后是境界,境界的根柢是识力。只有智者才可能在那个赤烈时代成为清醒的“强者”。
临终前,党组织总算慈悲开恩,要求他在认错书上签字,然后床前宣布摘去“右”帽,但不恢复党籍。五个子女无一前来“临终一别”。1974年11月24日,其弟陈敏之接到幼侄顾重之来信,20岁出头的青年如此回答父亲盼望的“诀别”:
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11月27日,病榻上的顾准获知五个子女无一肯来,大恸四小时。12月3日零时,顾准走了。他托友人转告子女:
我已经原谅你们了,请你们也原谅我吧。[4]
[1] 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著名作家,代表作:《毁灭》、《青年近卫军》;1934年后历任苏联作协筹委会副主席、书记、总书记、理事会主席,1956年信念崩潰自杀。
[2] 吴敬琏:《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页383~384。
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651~652。
[3] 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721、647。
[4] 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今日名流》(武汉)1997年第11期。
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723~724、732~733。
2003-1-29 上海
原载:《羊城晚报》(广州)2003年10月3日
转载:《文摘报》(北京)2003年10月7日
《报刊文摘》(上海)2003年10月13日
《芒种》(沈阳)2003年第12期
《读者》(兰州)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