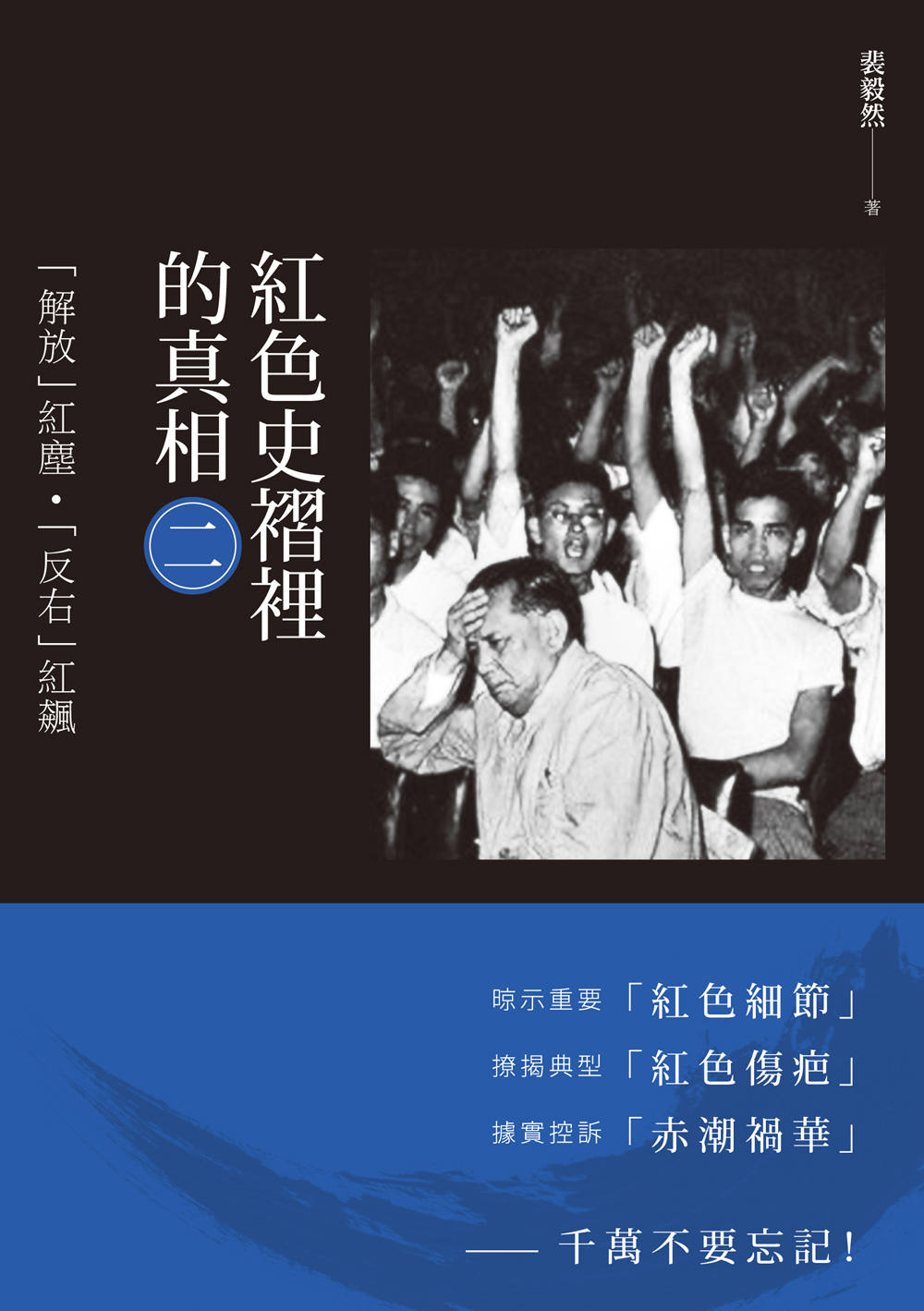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2)
反右对“五0后”一代的伤害
恐怖童年
笔者出生1954年,还在幼儿园,母亲就再三再四叮嘱:“大人家里说的话,绝对不能到外面说!”文革前,母亲叮嘱升级:“你在外面说话,直直要小心,多少人祸从口出!”最有说服力的是幼儿园密友之父,孤儿出身的新四军,杭州522厂(大型保密单位)二把手,从头红到脚的13级干部,竟划“极右”。那会儿,我弄不明白何为“右派”,只知道都是说话惹的祸,后果很严重。
“祸从口出”成为童年最浓重的心理阴影,母亲认为我最大的缺点——“话太多”。我问父母:“家里说的不能上外面说,那么能说什么?什么才不是『乱说乱动』?”父母尴尬互瞟,未给答复。应该说,我的“言论自由”从那时起就被剥夺了,从此生活在恐怖之中。更可怕的是:我一直以为这种氛围十分正常,因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一切金光闪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尤其美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需要我们去解救,我得快快长大……直至文革,我一直是十分标准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满脑红色思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红”……
反右威力,我是从那位“开裆裤朋友”父亲脸上第一次读到。他被开除党籍、直降六级,一下子也成了不能“乱说乱动”。那副悲哀愁戚,至今宛然在目。少年时代,我好说好问,母亲(杭州邮电局话务员)十分担心我惹祸,一再以这位新四军“极右”示范,要我“沉默是金”。憋屈的童年,空气中飘着不祥,连小学同学的绰号都带上“战斗气息”。笔者1961年上小学,三年级时两位男女同学父母去世,他们的原绰号作废,各有一个更响的新绰号:“阿爸死了活该!”“姆妈死了活该!”
自锢少年
文革爆发,我12岁,加入红卫兵要填成分。回家问父,父亲尴尬至极,转着弯告知其家庭出身血血红——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则墨墨黑,上了《公安六条》的国军少校,标准黑五类——“历反”。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何以再三再四严诫,底底儿原来在这里呢!我与十分向往革命的姐姐(杭女中初三生),那个绝望那个惊惧……只要巷口响起抄家锣鼓,姐弟俩便瑟缩发抖,生怕锣声停在自家门口。左邻叶阿婆站上洗衣石板,挂牌“逃亡地主婆”。
沦为菜场会计的父亲很识相,自踏三轮车请来单位造反派抄家。那晚,父亲破天荒嘱我晚点回家。我疯玩至二十点多才进家门,一上楼(就一间20平米的屋子),满地狼藉,母亲最珍爱的照片散落一地……我最近距离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
发小同学也论起阶级来:“富农”、“地主”、“资本”、“职员”、“革干”……这就是毛时代恩赐给我们“五0后”的“幸福童年”、“激情燃烧的少年”!
文革结束,上山下乡大兴安岭八年的我考入黑龙江大学。55号文件下达后,去那位“开裆裤朋友”家,其父从箱底翻出陈年稿纸——“极右”发言记录,他在省级机关处级干部座谈会上的“鸣放”。关键性几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央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他一口浓重苏北腔:
你现在是大学生,能懂了,我什么地方反党?中央领导有可能犯错误,毛主席、刘少奇也可能犯错误,错了吗?
他一脸悲愤委屈,深淀我心。当时就想:反右看来很值得研究,但还未出他家门,立即自我枪毙——怎么可以研究党的错误?岂非怀疑“党的领导”?否定“伟光正”?自幼形成的恐怖倏然升起,不敢再向前多想一厘米。
1980年代,“五0后”一江春水向西流,奔欧奔美。上海相声说有的沪青死也要死在西宝兴路(上海殡仪馆之一),因为带个“西”字。[1]
留英牛津生杨宪益(1915~2009)、英籍女性戴乃迭(1918~1999)长子杨烨,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湖北某厂,思想极左,和家里人都合不来,将父母的唱片什么的都烧毁了。文革结束后,杨宪益夫妇将子女陆续接回北京。但在他们监禁期间(1968~1972), 儿子杨烨对自己的身分认同产生很大问题,被诬英国特务,受不住周围压力,干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不愿意在家,总往英国大使馆跑。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一年后自焚伦敦寓所,又一位文革殉葬者。[2]
1983年春,笔者与拙妻正式确定关系前,她非常郑重告知:“我爸爸是『中右』,留党察看两年。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的出身比她更糟,当然不会“再考虑考虑”,但我明白父亲的“中右”一直结结实实压在她心底。
“六四”是“五七”的延续
真正觉得必须研究赤潮,源自“六四”。六四枪响,为中国“彻底”送走马列主义,“人民政府”失去所有“人民性”。指学生为暴徒,坦克当街碾人民,一个依靠学运起家的政党,竟走到向学生开枪,其间逻辑如何转弯?何以走出如此不堪的历史曲线?虽意识到其间价值,但慑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敢正面展开研究。1991年,入杭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选择了虽然敏感但非“正面进攻”的人性研究。1997年再入复旦大学攻博,撰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也算歪打正着,硕博期间的人性研究犹磁石引针,成为我由文入史的价值引导,认清赤潮祸华的根柢——马克思主义违反人性。
“六·四”后,老左派来打隔代新右派。笔者执教的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新任党委书记林和(1932~ ),1950年代哲学系进修生(?),听说那会儿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六·四”期间,我在杭州市中心武林广场发表演讲,为广场学生广播站审稿数日,公安局备案的“露头分子”。1991年11月30日,这位书记偷偷摸摸听我的课(隐坐高个学生身后),下令停我的课,要我“深刻检查”。我当时就意识到:反右还在沿续!从“五七”至“六四”,逻辑一脉相承,上一代“右派”遭受的红色恐怖轮到我们这一代品尝了。
2005年初,笔者首次访学香港,得阅港报港刊,接触“不同声音”,逐渐转移研究方向,离文学而入史学,以知识分子研究为切入点,追踪赤潮的起源、勃兴、衰落,尤其关注西方赤潮何以着床吾华。很快,研究成果陆续转化为各种港刊上的“不同声音”,包括对反右的研评。
研究赤潮的过程中,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也全身浸红,已无可能彻底洗净,不仅词汇库一片红,思维逻辑都是马列主义。每走一步都会自警“这不符合党的要求”、“那是不是太反动”、“阿会捉进去?”……吮吸“狼奶”长大,只能成为“狼人”。早年输入的红说、储存的红词、搭建的红理,加上反右以来深深渗入记忆的恐怖……一根根最结实的勒绳,我们这一代无法擦去的“代际底色”、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代独特的“代际能力”——完全熟悉“国情”、深刻理解中共、知晓每一处禁忌。
当今,大陆知识界仍笼罩在“反右后”的暴力阴影。红色高压虽然被迫松缓,但“中国特色”并未改变:知识分子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为中共守讳、回避敏感话题、掌握言论尺度。尽管中宣部未具体划定“红线”,大陆士林却对“红线”心领神会——默认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必须替中共各种“失误”寻找客观原因,只能劝百讽一,只能“歌德”(谀颂)不能“缺德”(批评)……
高岗“五虎上将”赵德尊之女,笔者大学同窗。1977年高考上线,因“犯官”成分不录取;1978年取消政审,勉强录取;第一志愿外语系,降录中文系;说是外语系毕业后要进外交口,不合适;中文系毕业当个老师,行啦。2012年其父去世,高岗女儿从北京奔丧哈尔滨,时时左顾右望,担心被跟踪。2015年5月2日,笔者劝请这位63岁的老同学忆录其父晚年思想言行,她仍有点紧张:“还不到时候吧?”
深远影响
反右是中共直接镇压士林的起点,有史以来最大文字狱。英俊沉下僚,老粗管老细,开启通往文革的意识形态甬道——从思想专政走向政治专政。反右直接影响我们“五0后”一代——含耻的少年(成分不佳)、黯淡的青年(上山下乡)、艰难的中年(贫穷困顿)。
若无反右,就不会有闯大祸的“大跃进”,全国经济不会大萎缩,粮食不会大减产,不会饿死四千万人,不会有掩盖大饥荒罪恶的文革,“五0后”一代也就不可能被“扔包袱”——上山下乡,我们的青春就不会虚掷“广阔天地”。事实上,1958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也是1957年反右的“胎儿”——毛共欲用经济绩效证明反右的正确,证明就是能搞成共产主义。
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经济萎缩—无法解决就业,我们这一代如此这般成为“包袱”,丢给农村,美其名曰“反修防修”。虚耗耽误一代青年,当然是最实质性的“国家犯罪”。红卫兵沦为二十世纪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代,结结实实承受文革后果。1949年后,中华文脉严重中断,国家大步后退至少三十年,还不算扳正“红色罪误”耗费的时间。“五0后”一代绝大多数有报国之心,无报国之门。我还未出初中校门,档案就装入那张烙上“阶级耻辱”的政审表,至今应该还在。惟“红二代”才是合格“接班人”。1980年代搞“第三梯队”,还不是新的血统论——提拔红二代。习近平上位,当然标志性说明“红色江山”的红色性质。
最近读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刘进、宋彬彬的“检讨书”。这些六旬红卫兵老太的检讨,表面真诚,内容空乏,对文革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无限怀念,拖着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但是”。她们至今仍未建立基础人文理念,对人性人权等普世价值十分隔膜,尤其对“生命第一”十分淡漠。正如她们所说“学生是老师的产物”,红卫兵当然是红校长的产物。卞仲耘、刘少奇实死于他们自己建立的红色逻辑。卞仲耘校长死讯公布时,北师大女附中某班全体鼓掌欢呼!不彻底肃清毛泽东思想、不追究赤色逻辑,“反右”就还未结束,也无法结束。何况官家至今仍捂着这截罪恶,遮着拦着不让谈论,企图让岁月“淡化”这笔倒账。只要“反右”仍被定性“扩大化”,“反右”就没完,完不了。
“五0后”一代的感受很有共同性。陈小雅(1955~ ),湖南师院历史系七七级,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其父方克(1918~2009),1978~82年《红旗》杂志副主编。1979年初,陈小雅偶然读到中央理论务虚会《简报》——
封建主义残余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公有制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军事共产主义和 “穷过渡”问题,一下子全提出来了。因为有感性经验的基础,我仿佛一下子就把过去接受的那套理论体系翻了过来。我给朋友写信说:“就像上帝给了地球最初的一击,于是就有了江河奔流,大海潮汐……”[3]
陈小雅这一震动性感受,在文革后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十分普遍。1979年,笔者在黑龙江大学,无法像陈小雅一样得到高层信息,对1949年后的“中共国史”尚懵里懵懂,这一历史震动感来得很晚,时间也拖得很长。1980~90年代,笔者都在“觉醒期”,45岁以后才从理性上完成大逆转,意识到:国际共运本身就走错了道,中共用国家在“赌”主义。
追究反右成因,必须追溯赤潮,刨挖赤说祖坟。如今,似是而非的赤论仍肆行大陆,甚至将报禁言禁、一党专政都论证成“社会主义优越性”,政府有镇压之权,百姓无评议之权(且不说监督权)……令人既哀痛又绝望,“反右”扭歪的社会价值标准,需要后人一点点找回来,这一历史任务至今“同志仍须努力”。
革命当然应该为了捍卫历史已经证明的正义,而非为了尚待验证的什么“主义”。中国为了一则外来赤说支付了数代人的悲剧,1949年后直接死亡至少七千万人。今天,面对悖论政局——“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而真反腐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必须让民众进入有效监督政府的票选制,而非被中共强迫“代表”。中共当然不愿意,这么不死不活歪歪斜斜拖着捱着,国人只能眼睁睁等着“大结局”。
送走赤色客人,廓清赤色废墟,为后代打扫出一片可以建屋造房的社会基础,而非歪歪理遍地、自由度甚低的恐怖社会。还有什么比此更重要的历史任务?
沉重笑话
1950年代“性禁忌”就开始了。北师大1953级女生王世巧,与同学范亦豪热恋两年才有初吻,“她一直幼稚地以为只要经常在一起,有感情,或接了吻,就会怀孕。”[4]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1947~2013),女友初中同学,他自沪赴川当兵,女友去了黑龙江生产兵团,通信多年——
……是不敢放任自己的情感的。恋爱是一个耻于出口的字眼,甚至要压制闪出这方面的念头……我们在恋爱中的信件,都可以公开在板报上贴出来,说的都是革命的语言。
1973年赵长天携女友同游莫干山,满山翠竹满谷林涛,鸟鸣泉声,静得只有他们两人,然而——
除了在下山的陡坡援手搀扶,我们没有更亲密的接触。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更不会住在一个房间。……什么是性行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对于性的常识,几乎为零。主流社会的声音,和“性”是完全绝缘的……第二年我们在新婚之夜,还不知上床是怎么回事,真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的年轻人只好当笑话听了,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绝不在少数。我们总算自学成才了。听说有结婚多年始终不孕,去医院就诊,才明白根本就没有同房。[5]
1980年代初一次调查,中国妇女60%无性高潮,仅仅视性为传宗接代的例行公事,10%有性恐惧,仅30%享受到性高潮。[6]
顾准五个子女拒绝“临终关怀”其父,成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不孝之子”,终身怀疚。然而,顾准之子高梁(1948~ ),居然是最坚决的毛派:
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7]
这位右派名士之后、吴敬琏的硕士,终身难出“左漩”矣。
对“五0后”、“六0后”来说,更可悲的是尚不自知的伤害。直到今天,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高层机构,仍未形成容忍“不同声音”的氛围,频频打断不同意见者的发言。“专政论者”认为捍卫真理就必须让对立者闭嘴。
虽然被严重扭曲的中国最终被一点点扳回来,“万恶”的孔子被悄悄迎回,圣经贤传粲然恢复,但生活在赤潮肆虐的二十世纪大陆国人,可是标标准准的“红色牺牲品”,至今仍习惯性生活在“虚假”之中。至于官家造假,比比皆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明明化装逃进美领馆申请政治避难,重庆市府“新闻办”硬敢向全世界撒谎:“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接受休假式治疗。”明明已不再搞共产了,可每次集会还在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真正平反
毛泽东自居“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认为个人独裁乃“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强硬推行未经实践证效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行“大仁政”,建“不世之功”,最后弄得“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史记·商君列传》)。尽管历史已将毛钉上耻辱柱——有史以来最大暴君,但整个国家毕竟为国际共运为毛泽东支付巨大代价,真正应该“千万不要忘记”,至少必须“年年讲”。尤其毛像尚未下墙、毛尸尚未出堂,赤色逻辑尚在大陆运行,十三亿国人尚强迫“被代表”,作为捍卫历史理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专制)不止,我们这一代不能实现民主自由,那就移交下一代,世世代代挖山不止,一定得移去这座阻挡中国前行的“王屋山”。
“东风”“西风”较劲,最后还不得看“产品”——培养出怎样的下一代。美国出了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裸捐的“共产主义新人”,欧洲也有一批拿得出手的当代人物,而“无限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什么新人?好像只有写写日记喊喊口号的雷锋、王杰。就是整个红色士林,文化程度都很低,理解人类近代思想都有难度。极其崇仰周恩来的韩素音(1917~2012),也说周根本不理解民主的价值——
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8]
如今,中共治国最突出的红色遗产乃是一茬茬贪官,倒台前一律高调自称“廉洁公仆”。“产品”比较,当然是真正的终极检验。
“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歌犹在耳,“右派”已然翻身,右言右论早被肯定,倒是毛共诸说“全军覆没”,均遭否定。这场公开失信天下的红色冤案虽未彻底平反,但天下之事并不全由中共包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反右”在民间已经结案,盖棺论定。只是委屈了相当一批“老右”,未能看到历史为你们说话的这一天!
[1] 柯达:〈王元化谈知识分子问题〉,《世纪》(上海)2012年第4期,页10。
[2] 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344。
[3] 高伐林:〈歷史記憶:”陳小雅答問(一)——張玉鳳要從頭講”〉(2005年),載”海歸網”。網頁連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6310d0b0101eplx.html
[4] 范亦豪:《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2014年,頁28~29。
[5] 赵长天:《曾经》,文汇出版社(上海)2007年,页184~188。
[6] 申渊:《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513。
[7] 彭淑等:〈顾准之子高梁言行录〉,《各界》(西安)2011年第11期,页26~28。
[8]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38。
初稿:2012-2-6~10;修改:2012-9-11;后再增补。
原载:《开放》(香港)2013年6月号(初稿)
附注:
2013-07-19 09:56 本文挂出笔者实名博客(新浪网)。
数次接网站通知:该博文被删入“回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