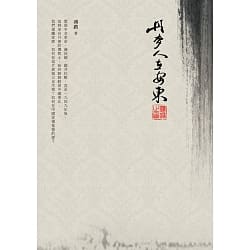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自北欧来到安东的一些丹麦人由该国民间和教会出资,在辽东地区传教,建立医院、孤儿院、中学、小学及园艺职业学校等慈善和教育机构,通过不到六十年有效扎实的工作,为安东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他们以质朴无华的人性之美,以无求回报的精神在远东展示了上帝的光照和慈爱。安东人在那一个历史价段中,经历著复杂的社会变动。其中有十多年的“满洲国”日本殖民统治(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到抗战胜利后国共政权纷争的拉锯乱世,动荡不安的状态一直就伴随着他们的生活。坐落于辽东半岛南部的安东市虽然拥有沿鸭绿江出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却常常因此而在许多方面处于一种边缘及偏远地域的境况中。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位于最前线的安东,社会状况骤然趋于极端。在安东从事慈善事业、对中国新政权十分友好的丹麦人被曲解为帝国主义渗透而遭迫害,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是安东历史上没有光彩的一章。丹麦人在辽东多年建立起的事业,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留下的痕迹,被逐步擦洗。“丹国医院”—在当时辽东民众口碑中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也悄然消失了。然而,对安东始终不忘的丹麦人,从一九七○年代末期,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至今,他们的后代仍然时常组团来辽东观光。其中无论是商业旅游性质的,或是被请来作“友好桥梁”的他们,都在努力找寻在一些记载中当年丹麦人的那些事物与当今社会在文化和生活层面上的关联。然而,还能有多少历史的印迹可供探索呢?其实,现代的“丹东”人,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当时的历史。没有人知道曾经为安东的教育及中国园艺发展做出重大页献的丹麦人吴立身博士在当年的工作是何等具有开拓性,却在“被赶走前遭大会批斗、被毒打”(吴立身女儿,文学家,丹麦作家协会理事吴坤美 Estrid Nielsen语);没有人能真切体会丹麦人郭慕深教士等善心人在把自己的毕生全部都奉献给中国普通民众后,却在她的晚年,遭遇了被扫地出门,离开她的孤儿院孩子们,孤身一人回到她那一切都是生疏的母国—丹麦—的窘迫境地。
鸿路所记载下来丹麦人在安东的故事,是在中国社会文明进展历程中有意义的真实历史。在当今社会条件里,有心、有力、乃至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可能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
我的父亲崔锦章以亲身的经历见证了“丹国医院”如何走向终结。在一个以革命口号为包装的当地当时社会基层权势运作下,公然以暴力和强权,以一些违反常识和逻辑不通的虚假作为驱动,编制出一场荒谬的戏剧。崔锦章,一个勤恳工作、受人尊敬、对当地民众“有用”的医生,虽然头上有被戴上“省人民代表”等光环,却在六个月内先是被委任为院长,又忽然变成罪行吓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使人们相信那些被捏造出来的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实, 该地方行政最高领导人,从市长到书记,联同省、市卫生厅局长等等全体出动,在当时从行政运作和专业事务上都不属“国家机关”的教会医院召集全院大会,大张旗鼓地宣称挖出反革命分子的重大胜利,以声势和威吓造成“铁板钉钉”的既成事实。就这样,这个教会医院就归于“人民”的掌管之下。
我的母亲王澄美,无数次向人们揭穿这种做法为“做扣儿”,胶东话就是设置圈套,“指鹿为马”、“请君入瓮”的意思。—“硬抢”,如果针对的是与新中国在一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就建立了正式邦交的丹麦国国民在中国的产业,地方政府官员们仍有碍于外交方面复杂性的考虑,及自身的政治形象而未敢妄为,毕竟在当时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尚寥寥无几。然而,以战时前线为由遣散外国人,随后诱导中国人以教会的名义从洋人手中“名正言顺”地接管医院,再“关门打狗”,一切就可随意而为之了。“拿下”医院,是省卫生厅一九五○年当年的重大“战果”;是当地政府“对敌斗争”的政绩及“抗美援朝”的胜利。崔锦章不幸被做在这个“扣儿”里。他虽在狱中历尽磨难,却始终不逾地搏命也要把那几个不属于他的不实罪名辩解清楚、扒拉下来。一九七九年,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终由中央有关部门干预而获得平反。其实,崔锦章一案早在反右前的一九五六年,经由省检察院复查而推翻原判,获平反并提前放人回家。这是他的第一次被平反。但是不知何故,却未有正式“文件”跟随。前《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宾雁在〈那黑压压的一片〉一文中,对中国的那个时期前后的社会政治情况有记载:
“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全国普遍恢复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制度。几十万精干的干部派往司法战线,清查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很多冤案已经平反,很多死囚已经脱去囚服。是反右号令一响,所有这一切都被推翻了。从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到各省市司法厅局长,大批主持正义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不下三分之一的律师由于替受害者辩护,也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从此中国就进一步落入了无法可循、暗无天日的世界。”
崔锦章的遭遇印证了刘宾雁的记载—他在“反右运动”轰起的一九五七年秋再度被捕,原因是被错误平反。多年后的一九七九年,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当年三月十二日的书面平反文件中,把过去的罪名全部都推翻了,撤销一九五○年的刑事判决,宣布崔锦章无罪。这实则是第二次为他平了反。平反判决书是一张轻巧的,比一个巴掌大不了多少的薄纸片。然而,平反书中却留下这样一个搞笑的小“尾巴”:
“原判认定申诉人崔锦章与一九四五年“九‧三”后编印反动歌集两千余册,其中有其亲自填词的“蒋委员长赞”一首,从事反动宣传。”
就此,崔锦章在给家人的信中解释道:
“作歌乃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当年的九一八以前,国共两党都未到安东时。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并非是什么反动宣传。印册五百,不是两千。……再者,我被捕并非是为了这些事,作歌是捕后我交代的。”
崔锦章毕业于英国人在沈阳开办的“盛京医科大学”。一九四○年代在安东设立诊所开业,挂牌是眼科专科。然而作为医科大学培养出来的基础全科医生,他以在危急情况下从为病人截肢到为产妇接生,以及夜半应门出诊等高度敬业精神在当时的社会上赢得口碑。“被事” 后,他本人在一九六○ -六一年冬最严酷的饥饿情势下,是靠食用妻子想尽办法筹集到的胎盘得以活命。在当时严酷的情形下,他仍参与救助一些垂死的犯人,以这种方式施展他的专长。当初他与曾经在安东生活和工作的丹麦人粘连在一起,并身不由己地成为丹国医院终结的重要当事人,是在一个特定时空中由诸多因素—宗教、专业和政治情势所造成的。他成为一个社会变迁的人质和见证者,不是他个人的选择。所发生的一切也远在他的逻辑和想像程度之外。崔锦章出生于安东北部山区五龙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他父母辈便是基督徒。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生活学习,是家中第一个走出山沟并成长为一个专业人材。他虽然经历了实属圣经所描述的“死荫的幽谷”,上帝却始终眷顾着他和他的家庭。在个人的品性方面,他有一个不大会“转弯儿”、被我母亲王澄美形容为“榆树疙瘩脑袋”,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认死理儿的“强驴子”—然而,却能够在生前亲眼目睹他个人,以及社会蠕动的曲折过程。这无论如何是他同时代无数人经历中的一个特例。
※崔世光,著名作曲家、钢琴家,生于辽宁省安东市,一九六二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一九七八年起担任中国交响乐团钢琴独奏家兼创作组成员。一九八四年赴美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获得钢琴、创作双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六年。曾在欧洲和北美四十多个城市和音乐节演出,创作钢琴协奏曲、组曲等四十余首。现居香港。
来源:博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