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0)

俄国各界的反思(40)
俄罗斯一些学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三个评价是:
3.苏维埃制度一方面为俄罗斯的发展做了不少事情,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又都是在极权强制下进行的,它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
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科伦泰认为,苏维埃制度一方面为俄罗斯的发展做了不少事情,如使它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使居民受到良好的教育等;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又都是在极权强制下实现的。 “为了取得这些进步,俄罗斯在经济、社会、人道和精神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代价不仅表现于千百万人的生活重创和伤残以及无尽无休的苦难,而且给社会留下许多深刻的烙印。所有这些合到一起,便是苏维埃时期的遗产,使得改革以及后改革时期穷于应付。”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季姆.梅德维杰夫认为: “实际上,在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观念的框框内,在我国建立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几乎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的经典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此完全赞同,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给予这一制度以否定的评价。对俄国社会所作的不带偏见的分析,使我们最终得出结论,遭到失败的是极权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体现,而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并把它的某些基本原则推向反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变成了平均主义,社会保障变成了依赖他人养活,对社会过程的自觉调节变成了对个人需求的压制。”
对于上面所说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与代价问题,阿.布坚科教授在他的《论国家行政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改革》一文第三节《如何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中作了深刻的剖析。请看此文的摘录:
……在国家行政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是否有由它建立起来的结构、形式成为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需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加以保留和继承?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已经不是代价问题,即苏联人民为取得那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还是十分昂贵的。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真正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否能够简单地加以继承,还是也需要改造,以及需要什么性质的改造?
这绝不是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的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对估价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前景具有根本的意义。戈尔巴乔夫说: “真实地了解我们的巨大成就也了解过去的灾难,对这些作出充分的正确的政治评价,这将给未来指出真正的道义上的方向。”
第一个问题是: 国家行政社会主义有没有什么成果?
我想,从发展生产力或者更窄一点,从发展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我们国家从落后的不够发达的(国家)变成了以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依托的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今天不管我们怎么批评这个基础,不管对其状况怎么不满,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国家巨大的物质技术生产设备是以往历史发展主要的正面成果。为了不丟弃这些文明果实,苏维埃社会应当找到保存和增加这一财富的途径。
于是这里自然要提出另一个问题: 过去我们社会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社会政治形式,这些也是以往历史的遗产,它们的情况如何?对这个问题,就得不到单一肯定的回答了。
我们先从农业集体化及其结果——集体农庄制度上来谈。
前面已经叙述了斯大林修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以及由于普遍没收富农财产并扩大到部分中农而引起的悲惨事件。是的,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为了用这种办法完成农户的合作化曾付出异常高昂的代价。
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不计算这种改造的代价,又应当怎么样看待其成果——在我国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制度呢?戈尔巴乔夫说,“……集体化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根本改变了全国大多数居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它为农业现代化和使农业转上文明经营的轨道创造了社会基础,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建设其他领域的需要腾出了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有历史性的后果。”
如果我告诉大家,揭示这些“历史性后果”时,许多作者只提出它的积极方面: 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提供了劳动力资源,等等。这些都是实情。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正确的。既然按照斯大林思想实行的集体化“意味着根本改变了全国大多数居民的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在宣称这种新生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同时,就不能不看到,实际上这里搞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基础”。集体农庄庄员披星戴月辛勤劳动,常常只能得到极其微薄的收入,根本与其劳动贡献不相等价(否则又从哪里弄到工业化的资金)。所以,按照斯大林思想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对“全国大多数居民”来说,不是社会主义式的,而是斯大林式的“全苏劳动学校”。在这里,劳动不是一种快慰,而是强迫的结果。所挣的钱不过是国家官员(从该农庄拿不拿走全部产品均由他们决定)留下的、施与他们的那些东西的平均分配。正是这所“全苏劳动学校”不断训练、再生产并为城市和乡村不单单提供了劳动大军,而且还提供了大批对能够诚实劳动、诚实挣钱完全失去信心的人,提供了大批不是因自愿选择新职业,而是按照命令和通知单进入工业部门的人——当然,这些人都很愿意从集体农庄那半强迫、甚至不能按其价值得到报酬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去。
三十年代在集体农庄就开始认识社会主义的“全国大多数居民”上了一所什么学校。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且还是一个大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工业化做一个分析也是重要的。毫无疑义,在参加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群众的信仰产生了奇迹般的劳动热情和英雄主义,他们准备牺牲并且也真正作出了牺牲。戈尔巴乔夫说,“党提出的体现了十月革命精神的计划、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口号和构想的生命力,在令世界惊异的劳动热情中得到了反映,千百万苏联人怀着这种热情投入了苏联工业化建设。在极其困难、没有机械化、处于半饥饿的条件下,人们创造了奇迹。他们投身于伟大的历史事业,这给他们以鼓舞。他们的文化虽然不高,但是,他们凭着阶级感情理解到,他们是何等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参加者。”
我在这里也提出个问题: 难道不正是这种舍己精神带来了忽视劳动者起码的生活条件、官僚主义滋长等一些不良的后果吗?难道对目无法纪现象奴隶般的顺从、对剥夺富农财产和大规模镇压不作反抗,不正是这种舍己精神的产物吗?难道世代技术至上主义者的培养、行政命令管理体系的扩大不都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只须稍加思索,就会得出结论: 用这种办法,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变成了“人的因素”的极大分解,它或早或晚,但必定将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新的消极后果。
所以,别的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巨大飞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苏维埃社会也是靠人的因素,靠人身体的过度紧张、政治压迫和精神解体完成的。所有这一切使情况更加严峻: 一个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使自己在这方面进步的可能性更加减少。
一般来说,今日的改革所遇到的情况和有鲜明特征的形势就是如此。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对它的进展不快感到惊奇。它的进展也不可能快。说到现有的困难,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苏联人民在几十年历程中向世界所显示的那些消极后果——舍己精神、长久忍耐和逆来顺受,不仅仅是很大一部分苏联人民由于斯大林及其在世时和以后当政官僚的作用变成的这个样子,而且也包括我们国家现在建设新社会时所遇到的人的因素问题。
有些“无忧无虑的乐观派”认为,只要党今天号召,人民明天就会起来在革命性改革中完成党所说的一切。对这种逞能的人,我想问: “过去你们在哪里?睡大觉了吗?没有看见人们的奴隶心理已经根深蒂固了吗?要是没看见,你们就去看看吧!” 同样,有些“垂头丧气的悲观派”看到劳动群众情绪消极,一时半会积极不起来,往往还不接受改革的这种那种观点,就对革命性改革的可能性本身缺乏信心。对这样的人我也想说: “你认为过去的一切立刻就能完全消失吗?你想仅仅用号召就能把几十年用不合适的做法建立、培养出来的东西在一天时间里肃清吗?”
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难题都证明,苏联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无可比拟的、极为艰巨的革命任务——通过革命性改革变国家行政社会主义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完成这一革命性的改造将是十分不易的。但历史不允许我们有其他选择!
看到布坚科教授的这篇文章,觉得用“振聋发聩”四个字来形容真是恰到好处。文章畅所欲言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具有特殊的说服力,深刻地指出革命性改革是苏联社会生存的条件,此外,别无选择。
下面再看一些苏联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剖析:
二、苏联剧变的原因
1.没有始终重视提高劳动生产力,导致苏联在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
莫斯科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鲍里斯.斯拉文认为,在俄国有过两种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模式: 列宁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无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验,‘由上面’用兵营式官僚主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列宁模式则“要求仔细研究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一切好经验,在实行广泛的民主和自治的基础上,‘由下面’来建立社会主义”。
斯拉文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权力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制度。而斯大林模式实行的是“粗陋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消极后果。斯大林模式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破产了,而且在经济方面也破产了。1993年5月5日,斯拉文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 斯大林模式“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竞争不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为人民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方面也比它们逊色。它为党和国家官吏建立特权,使CP更加脱离人民,其最终结果是: 党本身垮了,党建立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战略也一起垮了。” “如果我国彻底实行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如果不过早地消灭小私有经济和消费合作社,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和民主彼此对立起来,那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斯拉文1995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苏联领导人“过于夸大所有制关系的意义,没有把重点放在科技进步上,没有注意把科技进步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领导人未能很好地把握科技革命的成果,这导致了苏联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必将遭到失败,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会死亡。当劳动人民的政权官僚主义化时,当CP或劳动人民的党丧失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苏联曾经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可以说,是党的官吏们的特权和官僚主义扼杀了苏维埃政权”。
1999年,斯拉文在武汉举行的“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未能最终克服与所有制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异化”;“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从根本上走了样,犯了错误”;“苏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结果导致党内上层脱离了下层,党脱离人民,从而导致党的灭亡”。“苏共退出政治舞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在理论方面的教条主义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在苏共的行动指南,而是变成了为其辩护的教义。苏共不善于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以及改革时期涌现出的政治力量适时地作出批判的分析和评价;不善于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最新现象,依然一味信奉反映以往岁月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
斯拉文教授在武汉参加了两次会议,所作的发言不知中国同行听了有何感受。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应该有所触动,但又不好随声附和吧。
与此同时,斯拉文认为,必须坚决抛弃那些过时的论点和教条。例如,在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彻底的胜利”的提法;苏联时期所谓“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发达社会主义”的说法。他认为,“在一个手工体力劳动仍占相当大比例(约占50%)、‘劳动时间’仍是社会生产基本范畴的国家里奢谈什么‘发达社会主义’或‘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这就意味着大大地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
斯拉文2001年12月在一篇纪念苏联解体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为什么联盟解体了?第一,因为苏联在与西方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赛中没有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并相应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民主和国际主义。”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梅德维杰夫认为,社会主义危机“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而这些变化是与工业化时代潜力的耗尽,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西方在现阶段善于适应形成新文明的条件和要求。在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其中包括在人们的生活活动的许多方面实行社会化。而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却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自我改造和适应,从上面进行改革的尝试又遇到来自保守主义的、惰性的力量的顽强反抗。结果,危机转变成了崩溃。
历史学博士亚.普里亚伊斯教授在《苏联解体的辩证法和对俄罗斯的教训》一文中写道: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和东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自己的主要对手——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中,首先是在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越来越明显地遭到了失败。这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促使人们思考落后的原因,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摆脱莫斯科的桎梏和专政、取得真正的主权被许多民族共和国看作是摆脱一切灾难的万能灵药。”
学者H.纳乌莫夫1998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多民族的俄罗斯——历史和现状”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从国际视角看苏联解体》的发言中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阻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他说: “必须指出,在1914一1945年间,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在人力资源、经济和领土方面遭到巨大的损失。为了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克服在人口、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战争后果,苏联各族人民不得不在战后经济崩溃和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混乱无序的条件下开始恢复工作……”而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损失大大少于其他参战国家。“冷战”对于苏联和美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计算,苏联在1980年底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6%。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事开支为9471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5.6%。可见美国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少于苏联。美国的经济效率高于苏联,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利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此外,美国在北约国家军费支付的份额为30%,而苏联在华约国家军费支付的份额为80%。军备竞赛使苏联的经济畸形发展,军工部门占全部工业生产的80%,民用工业部门和农业成为苏联庞大的军工部门的附属物。军工部门的畸形发展到了70年代末使苏联的整个经济更加落后,从而使苏联军事技术潜力在质量上日益恶化,这导致苏联的国际地位遭到削弱。纳乌莫夫指出: “经济落后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苏联的经济体系名曰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官僚主义经济,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官僚垄断集团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当局为了寻求出路,称霸世界,必然要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苏联经济上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国民经济一片混乱。生产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工业畸形发展,轻工业、农业严重落后,供应紧张,财政困难,经济逐渐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同时给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他们长期处于商品匮乏、物资短缺之中。长期持续,上下人心思变,终于在1991年走上了解脱之路。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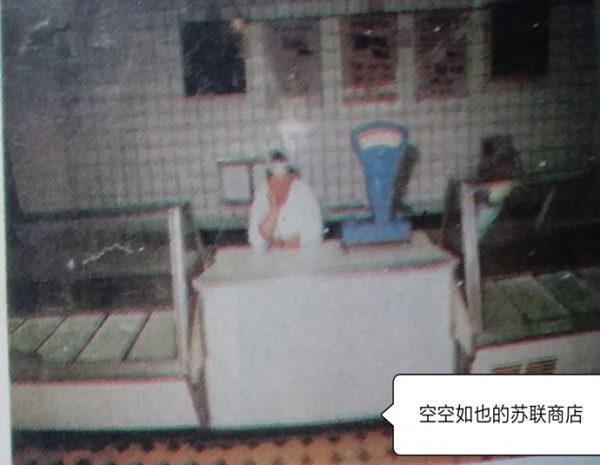
荀路 2022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