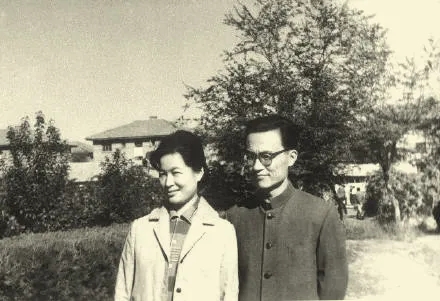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与天斗,与地斗,是否其乐无穷,我不敢肯定。至少从我本人经历而言,与天(我把它理解为政治统治势力,因为它主宰我们的命运)斗,与地(我指的是下乡劳动改造)斗,只有苦而没有乐的。只是与人斗有的倒确实有一些乐趣,不过细想起来,也只是苦中作乐而已。
在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就遇到了两件事,本来是应该吓得屁滚尿流的,但是凭我这个老运动员的狡猾,也就是革命小将们所说的老奸巨猾,居然安然度过,如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好玩。这里要补充一句,“老运动员”是革命小将给我的“溢美”之词,因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我大概因为在业务工作上得到领导器重,在反右运动之前,五十年代初期的历次运动,不论肃反、土改、抗美援朝等,他们为了要腾出手来领导,就把日常业务工作交我主持,这样我得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而在戴了“右派分子”帽子以后,我被排斥在革命群众之外,什么反右倾、“四清”运动,更没有我的份儿了,因此仅仅因为在一次运动中身陷罗网而被封为“老运动员”实在太抬举我了。
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还无暇顾及我这暂时在旁提心吊胆地逍遥的“死老虎”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商务印书馆革命造反派铁扫帚战斗队的一封最后通牒,勒令我这个吸血鬼限期退回一部译稿校订费人民币五百元。这部译稿是新华社对外部孙硕人、诸长福、贾鼎治等四位同志合译的《阿拉伯民族史》。这四位都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在对外部做定稿工作,翻译质量,自无问题。但是为了对工作负责起见,还是要我给他们通读润饰一遍,以免译名或用词方面前后不一致。核定后由商务另开一笔校订费共五百元给我。要知道在六十年代初期,五百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当时我的右派工资只有六十九元一月(比原来工资一百六十七元少了将近一百元),捉襟见肘,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后来幸而得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的照顾,由他出面打了招呼,给中宣部组织的反修灰皮书译些稿子,贴补家用。这时正好积了一些稿费,也有五百左右,我就一起拿到西单第一储蓄所,各开一张定期一年的存单。到铁扫帚战斗队来信向我这个老吸血鬼索回这五百元的血汗钱时,存单还没有到期。如果要退回稿费的话,家里没有余钱,需要到银行去提前支取,然后送到商务去。但送去不免与铁扫帚战斗队革命小将打照面,很可能发生当众受辱的结果。左思右想,不如把存单直接寄给他们,一点利息牺牲了也就算了。
在我寄出存单后几个月,我的另一张存单也到期了。我就到西单第一储蓄所去取了出来。在柜台上办理取款时,我忽然灵机一动,问那出纳员另一张联号的同样存单,那位出纳员翻了一下说“有”,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取?”。这么看来,铁扫帚队并没有把存款取走,我只好扯个谎说那张存单丢了,能不能凭户口本领取。她沉吟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叫我等一下,她进去请示领导。片刻后她又出来问我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然后又进了里间,这次时间长了一些,出来后要我把户口本给她,核对名字无误后,就把两笔存款连本带息递给了我。
我之所以敢冒这个险,一是估计铁扫帚战斗队收到我的存单后,按照储蓄规章是无法取出现款的,如今存款果然仍在那里;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死老虎”,到了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之前还没有当作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因此我估计银行打电话到我工作单位去问此人有无问题,是否牛鬼蛇神,那边是不会给肯定答复的。结果证明我的估计果然没有错误。我取出存款后在回家路上心中暗暗窃喜,这是我与革命小将斗,也即是身陷政治罗网后与人斗第一次得到的乐趣。其实这不过是苦中作乐,因为当初我接到铁扫帚战斗队的最后通牒时,的确是很害怕的,怕的是如果我拒绝退回这笔“剥削”,他们会不会到我家来揪斗抄家,这样我暂时的相对平静的逍遥生活就要打破了。惊弓之鸟,只有乖乖服从,把存单寄了出去,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求一时太平骨头之软,后来虽心有未甘,略施小计,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理所当然地要了回来,但实在不足言勇也。
第二次与造反派斗智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揪出来以后。我与走资派副院长彭平和一位姓李的日文教员(理所当然的“汉奸”)关在同一栋辟作“牛棚”的外国专家宿舍楼里,这楼虽叫专家楼,其实也是一栋筒子楼,只是粉刷得干净一些而已。其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专家都已回国,一个不剩,半截空楼遂权充“牛棚”,便宜了我们这些为人所不齿的狗屎堆了。某日深夜,我们三人都已入睡,忽然外面走廊中有多人的脚步声,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专案组的几个学生走了进来,为首的一个叫道:“董乐山,快起来,跟我们走!”我当即起身穿衣服,彭平虽是当官的走资派,平时却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关心地问了一句:“去哪儿?是提审?”这时一个学生斥责他:“你睡你的觉,不关你的事!”
我在几个学生前后簇拥之下,到了楼下一间屋子,只见一盏至少有二百度以上的灯泡发出强烈的光,黑布围上的灯罩把光线集中在屋子中央的一张三屉桌上,桌子一边坐着一个军代表。他们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押我下去的学生就坐在我的后面,由于灯光正对着,十分刺眼,我看不清屋子里有多少人,只见黑黝黝的人影憧憧,沿着四周墙边,坐满了几排,显然是来造声势的。
当初清理阶级队伍把我揪出来时,我以为只是算算我这只极右分子“死老虎”的老账。谁知这些老账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开头几次提审,问的都是一些我根本想不到、甚至根本不知所云的问题。这一次,在强烈的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的半夜两点钟,他们若有其事地要我交代接受司徒雷登委派充任美帝潜伏特务的经过。天晓得,我根本不认识司徒雷登,更不用说为他充当潜伏特务了。但是在他们有板有眼的提示下,我的昏沉沉的脑子里仿佛确实发生了一件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司徒雷登在离中国的时候,途经上海,在杜美路杜月笙的公馆(当时租给美国总领事馆)接见领馆所有中国雇员,接见后把我留下来,在密室布置我潜伏的任务。我当然是矢口否认:第一,我是美国新闻处一个小职员,连总领事面都没有见过,说不定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何况是美国大使;第二,司徒雷登离沪时确实接见过一些华籍员工,但都是各部门的助理主管,根本轮不上我,我也只是在事后听说有此事的。但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在军代表的吹胡子瞪眼的大声怒斥下,在提示者的循循诱导下,在屋子四周黑暗的墙边坐着的革命群众高声朗读伟大领袖的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启发下,我的混乱头脑实在无法正常思维了。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回去好好地睡一觉。既然群众说我见了司徒雷登,既然党说我见了司徒雷登,那么为了遵循最高指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只好不相信自己了,我一定见了司徒雷登。此话一出,全场喘了一口气。原先是凶神恶煞的军代表顿时换了副和颜悦色的面貌:“那么今晚的会就开到这里,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仔细回忆一下,把材料写好。”
我回到牛棚房间以后,倒头就睡。睡在对面的彭平大概放心不下,一直在等我,没有睡着,他小声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我只叹了一口气,翻过身去,脸冲着墙一边。他又关切地叮咛了一句:“要顶住,千万不要想不开。”彭平是个小老头儿,“一二·九”时代清华大学学生,上了年纪以后,有些倚老卖老,嘴巴很碎,平时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从不跟他谈正经话。这时我却心头感到了一股暖意。
这一夜我当然是辗转反侧,没有合眼,不知这场逼供闹剧如何收场:屈打成招,心有不甘,这莫须有的罪名一辈子也洗不清;但是要坚持不屈,他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长期折磨下去,后果也不堪设想。
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我一宵未睡。天亮之后,我决定要“翻案”,事不宜迟,宁可因此挨斗挨批,否则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因此在起床以后来不及盥洗就到门口把看守的学生叫了过来,告诉他,我要找工宣队谈话,我之所以要找工宣队,因为昨晚提审是军代表,似乎没有工宣队在场,这样转个弯,也许不至于招致难堪——不论是对军代表,还是对我自己。我还没有洗完脸,那学生就来了,把我带到工宣队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工宣队和一个革委会学生代表,桌上放着纸和笔。他们都一脸兴奋的神情,大概以为我要招供了。为首的工宣队女队长平时脸色铁青,这时却满脸和颜悦色地欠一欠身,请我坐下。
我没有等她说开场白,就抢先说:“昨天半夜,在强烈的灯光下,在军代表和革命小将的追问下(我没有敢用‘逼问’一词),我头脑混乱了,最后说的话不是实情,心中不安,一夜未睡,所以一早就来找你们郑重声明,希望你们谅解。”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工宣队女队长的脸色就变了,但我看出失望多于生气。她沉吟了片刻,把手一挥说,“你回去吧。”
她居然没有当场发火,骂我一顿,使我意想不到。我回到自己屋子里去时,心里一块大石落地,感到十分轻松。连彭老头也看出来了,期望地望着我。我不忍对他保密,就说:“我找工宣队声明昨夜他们逼我说的不是事实。”他似乎也放了心:“是嘛,应该实事求是嘛。”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不知军宣队听了工宣队的汇报以后,一怒之下,想出什么法儿来整我。
但是奇怪的是,我提心吊胆地等了几天,风暴却没有来临,一点动静也没有。但是那个军宣队员却不再露面了,换了另外一个。我私下打听一下,听说是调走了。彭老头儿认为他搞逼供信,违反了政策,所以给调走了,但我认为事情不这么简单,要说违反政策,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对共产党过去的政策的大违反,怎么没有人出来说话或制止。彭老头儿这一心态正如不少老干部在被折磨致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希望他老人家前来解救他的冤屈似的。
不管怎么样,我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是,必要的时候,略施诡计斗一斗智也是一种乐趣,尽管这是为了避免束手待毙而不得已为之的。
(《沉默的竖琴》,董乐山/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