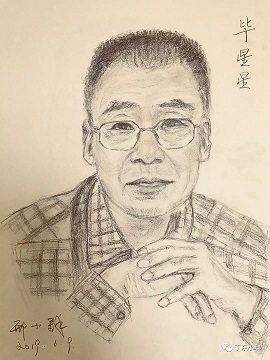再没有树,更能见证乡村的变迁了。
土地归家户的时候,大田里没有树。地里长树,庄稼就歇住了,不好。路上也不种树,大路村里叫官路,官路上的树当然是官有,没人愿意在大路上植树。巷子里的树,栽在房前屋后。田野里的树,栽在井台边。牲口拉水车,蹄子踩出一个圆圈,树就围着井道,栽成一个圆圈。地是自家的,井台是自家的,树永远是自家的,树就长得高大。买了卖了,树可以随地走,就一直留着。井台一周的树,得水近,长得好。地主也不急着砍树,它就一直长。井台的大树,柳树,榆树,都一抱粗细。也栽点杏树,孩子淘气了,吃个新鲜。
树围着井台,田野上看,就是一点一点的绿。一点一丛树,没有直行,也没有连片。平原上没有河滩,没有滩地的林子。树就这样一点一点撒在原野,漫不经心的。
槐树榆树长得慢,柳树长得快,柳树就比槐树榆树高大。在一丛树里,柳树经常是最高的。不是城里公园里的垂柳,那太柔曼。就是一般的馒头柳,枝叶短,纷披着,倒像今天的披头士。
巷子里大树老树更多。老院子,几十年几百年传下来,树伴随着人,一辈一辈过来了。大巷里,一揽粗的大树多的是。民国时期教书的师傅门口,上马圪台边上一棵老槐树,树身早已空了,狗钻进钻出的,猫钻进空洞爬上去,枝杈上露出小猫头来。枝干都枯干了,每年零星抽几条细细的嫩枝新芽,一副老树着花样子,这树总有几百年了。
合作化土地财产归公,村里有人宰杀牲口,各地都严打过,当成刑事犯罪。其实同时,砍树也成风,好像没有处罚。在心里,人们还是惜命,驴马都是一条命么。没有人怜惜树。树难道不是命吗?
入社在树是一劫,从此村子难见大树。
农业社也栽树。土地大路都是社里的,社里就在大路两旁栽树。规划整齐,一行一行的。这个时候最大的变化,树成了行。沿着马路,延伸到远方,那是社会主义的林荫道。
栽什么树呢?最流行的是钻天杨。发木快,直溜溜往上长,三五年就成材。还有泡桐,七八年就能解板材。毕竟刚共了产,大家都在担心归公。谁能想那么长久,几年后还不知道是谁的,你还敢思谋几十年的大树?
从此田野成了钻天杨的一统天下。以前村头的楸树呢,池塘边的大杨树呢,烂园子里的构桃树呢,统统让位给新兴的统治者。白杨独霸天下,好像土地的新主人,榆树柳树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家常伙伴冷落了。更不用说桃杏树,那是经济林,有资本主义嫌疑,孩子们想偷嘴都没个地方了。
可树这个家伙和人一样,天生是杂居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杨柳榆槐,各呈奇妙。大家一起,各长各的,才叫日子。天下要只留一种东西好过,这东西肯定活不成。没过几年,一场大规模的树种瘟疫,很快席卷了各地白杨树。杨树树身上头长出一个肿包,黑黢黢的虚松起来,仿佛脖子长出一个瘿,枝叶干死。过一段往下再串出一个瘿,树身就一节一节朝下死。没治,像癌变。杨树成片病死,村民连忙砍伐。不分青壮年少,田野躺满了杨树白森森的尸体,大多属于未成年。其实预防的办法简单得很,有几棵榆树槐树隔开,就像打了隔离带,传不过去了。一大二公规划的时候,只想到整齐划一,没想到一律好了也容易一律坏。
留下的泡桐,也不容它们长粗了。生产队穷得干打干,没钱分红了,队长就说:掘几棵树去!粮食低产, 口就不错了,分红就靠卖几棵树。谁上台当队长,都盯着,那树根本长不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分地,皆大欢喜。树,却是又迎来了一轮劫难。分地分牲口,树也要分。共产风心有余悸,凡到手的树,大多砍了改成板材,堆放在家里。大地白茫茫一片,好似坚壁清野,大家于是放心。
十多年后,迎来了又一轮大植树。粮食越来越不值钱,种地无利可取,乡民开始把目光投向果树。邻村栽种了,卖了好价钱。不用发文件号召,坡地带头栽了果树。不几年,平川也跟着学。一展平的好地,都不种粮食了,一律换了梨树苹果树。百里沃野,连片果林。阡陌在树行里穿越。田野一片绿,五月花,十月果,好景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造林运动。绿了坡地,绿了平川。树的家族,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树大约很骄傲。自以为招摇天下,十年百年永享厚祚,指望榛莽参天。树太天真。这是一轮经济林运动,人们栽树为了卖钱,怎样挣钱怎样来。果树不能长大,长大不好授粉,不好采摘。人们欢迎果树低矮化,大地上列队站满了树家族的侏儒。为了结果子,多结果子,果树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也得接收驯化。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果农全身披挂,七天喷一次农药,消灭了钻心虫,也顺带消灭了所有的蝴蝶蚂蚱蛐蛐儿。土壤施肥根本等不及,各种化工原料齐上阵,树上挂满了吊针瓶子。你要上颜色吗,挂这个液体。你要甜吗,你要脆吗?分别有液瓶等着。果皮很艳,果肉不过是各种化学试剂通过枝叶合成。从树林子经过,各种输液瓶叮叮当当挂满枝头,微风吹来如鸣佩环。一棵棵树,像蛋鸡,像肉牛,像填鸭,不过是换票子的机器。人瞪着血红的眼睛,胳膊粗细的小树就开始思谋牟利,那是觊觎乳猪上笼,残害未成年的童工。如此大规模的奴役压迫动植物,亘古未有。
果树冲着商品果子,更新换代在所难免。秦冠过时了,要换红星。红星过时了,嫁接了红富士。你刚换成最新的嘎啦,有人的冬枣暴利,呼啦啦掘了满地树根,一园子苹果换成枣树。今年山楂火得很,隔明年推广大个儿番石榴。农家的果树,十几年间轮回了一个遍。树根摆满大路,好似根雕艺术大展。挖树栽树,好像还没有休止的意思。
本来,田野里再折腾,村巷里是安宁的。官路上的大树没了,门前的树还在。谁也料不到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高潮来了。平地,扩巷子,迁移,铺上炉渣,抹上水泥。铺路整街,前任村长要取直,继任村长要拓宽,再换一任索性动迁。蓝图几番描绘,终于彻底消灭了最后的几棵老树大树。到乡村去,太阳底下白花花的,整个一个光芒万丈。这大概就是那个孤零零的崭新的新世界吧。
我的村子的老树,现在就留下我家院子里的那棵。六十来年树龄,因为长在院子里,没人管,也就没人命令砍倒,它得以幸存。这棵树,村里人叫“出”树,就是臭椿。查一查字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樗”,老乡亲至今保留着这个古老的发音。树以无用而保全,3000年前如此,至今如此。
公有化以来,是树逃不脱早殇的命运。人手握生杀大权,敛之常不待其熟。
大树是静物。大树在,好似老树精微笑着慈祥地告诉你,60年来,虽然不免风雪,毕竟没有刀斧,它的日子可说安然。
一个地方能长成大树,证明了此地起码享有几十年的请勿打扰。
那么一个折腾的时代呢?人折腾完人,当然还要折腾树。
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树不得安宁,是人不得安宁。人不折腾了,树也就安宁了。
乡野连自己的树都保不住,那肯定是受了欺负,他该有多委屈。
60年来,乡村风景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大树。
《随笔》总第207期 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