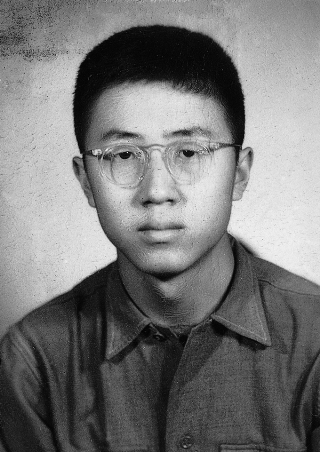5.新中国
那时共产党在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开过之后,报纸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还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因为我很注意,所以从中识得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许多要人,至今不用查资料,那时谁当什么我大部分都记得。毫无疑问,那时认为这些都是很纯正很了不起的人。尤其是看到报纸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理长得特别英俊,气度不凡。他还兼任外交部长,有知道点情况的(好像就是爸爸)说共产党的外交部长非周恩来来当不行。
听说不久就要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报纸上还说有人曾经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是毛主席认为“民主”两个字多余了,未采纳)。开国那天,学校里要开庆祝大会,要演节目。记不清是谁组织的,找来一个剧本要排演话剧。剧本说的是一位解放军“指导员”老王挂了彩,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养伤。国民党军队来搜查,女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子平时如何精心看护老王,搜查时又机智地掩护了他。他们选中了我来扮演男主角老王,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住在西南大后方,“国语”比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人说得好些。其实我直到那时还是性格内向的,但那时有一股热情,我并不胆怯。女主角就是女房东,由清心女中的一个同学扮演。自从解放后,陆家浜路两边面对面的男校女校不禁止往来了。已经有些高中生和她们往来频繁,联系一起搞活动。除了清心女中还有民立女中,也在南市。那位女主角皮肤白嫩,长得很清秀,看上去有些腼腆羞涩,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女中去看她们的一次文娱演出,见她又活跃在舞台上,那次她扮的不是“大娘”,而是活泼的女学生。我虽然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但是在那个年龄,第一次和女生接触,一起活动,感觉到兴头更足。
6.开国那天我入团,接着当了团总支委员
这时上海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先锋队”本来就是上海建团前的一个预备组织,我们这些“先锋队员”除了一两个在那段时间“表现不大好”的,几乎全部都入了团。入团申请书上“介绍人”一栏填的是“潘鸿芳”,他是高中生,大概是解放前就参与地下学生活动的。其实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大家都是新团员,所以只好由组织来指定一个稍有“资格”的作为介绍人了。
就在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在清心中学礼堂里开了全校庆祝会。在这次会上全体被批准入团的新团员进行了入团宣誓。会后文娱表演,包括我们的那个小话剧。
接下来,就成立了清心中学青年团总支部。朱永嘉任总支书记,林本仁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记不得了,其它还有好几个委员,包括我。初中部只有我一个委员,我已记不得当时为什么把我选上去的。其实沈锦辉、顾伯衡、董志鸿、章北威他们几个都比我“资格老”,我还是被他们“团结吸收”进来的。也许就是像顾伯衡说的,他们认为我“很好”。我只记得我当时心里有点怕,因为我性格内向,当了总支委员,初中部的两个团小组就由我来管,相当于整个初中部的分支部书记。我要召集和主持会议,要讲话,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我怕临场会很紧张。我找沈锦辉说了,他一个劲的鼓励我不要怕,说大家会支持我的,锻炼锻炼就老练了。我只好当了。沈锦辉的确一直很支持我,我想,把我选到团总支去也是他主动“让贤”推举我的。初中部的两个团小组长分别是顾伯衡和董志鸿,当时觉得,顾伯衡一直很朴质也很踏实,董志宏则有些“冷热病”。不料,顾伯衡后来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1950年夏天考入上海中学以后就和他们没有再见过面。是我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以后,偶然从上海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专门讲“反革命分子顾伯衡”的事。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只是从中知道他初中毕业后没有再读书(原来就知道他家里不富裕),大概参加了一个短训后在公安部门工作。说他在那里多次发表“反革命言论”,还有“反革命活动”。虽然最初见到这则消息时心里颇为震动,但后来我想这是很可能的,那时他就和我一样,是个热血青年。这种人参加工作后见到些什么看不惯、想不通的情况时,最容易用理想主义的标尺来度量现实,按捺不住去“发表反革命言论”的。如果再有点什么行为,就成为“反革命活动”了。在别的地方也许马虎些,在堂堂公安机关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呜呼!后来有不少“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是我们这种解放初在学校里最热情进步的人。
7.上海市开国大游行
1949年10月8日,全上海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成立大游行。我们发动了大多数同学参加,南市各校的队伍都从各自学校出发集合排队。除了横幅、标语、旗帜外,上面还发下大量的中国人民领袖和世界各国人民领袖肖像,世界各国人民领袖就是各国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有波兰的贝鲁特、民主德国(东德)的威廉.皮克、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乔巴山、朝鲜的金日成(金日成那张像年轻漂亮,爸爸评论他:“还像个中学生”,但是几年之后就被朝鲜人民尊为“慈父领袖”)。至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时已经被叫做“叛徒”,所以不在其列。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有美国的福斯特、英国的波立特、法国的多列士、意大利的陶里亚蒂、西班牙的伊巴露丽、西德的马克斯.雷曼、日本的德田球一、印尼的艾地、越南(当时尚未“解放”)的胡志明、巴西的普列斯特斯等。这一套领袖群像被群众高高举着,就像一片森林。足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声势浩荡,社会主义阵营无比强大。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当时的这每一位领袖,在我心目中都是十分崇敬的伟大人物,各路神圣。
游行的中心是设在跑马厅的总会场,在那里接受首长的检阅。因为参加游行的人太多了,队伍行进得极慢,常常在街上停留很长时间。站累了,只好坐下来等,有时索性打打闹闹。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不小,大家浑身都淋透了。直到半夜,我们才经过检阅台。从跑马厅一出来,队伍就散了。那时我已经在走读,但是回家已经太晚,于是许多人一起回到清心中学,就在石麟堂图书馆楼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衣服倒在地板上睡了。那时太年轻,一点也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第二天回到家里就感冒了,这次感冒很厉害,长时间咳嗽不止。妈妈打听到两种土方子,一种是把煎荷包蛋蘸着蜂蜜吃,另一种是qin糖(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就是那时挑担子的小贩卖的一种粘糖,黄色的,像大羌饼那样一大块,用一条有刀口的弯铁片和榔头敲下一小块一小块卖给小孩吃的)熬南瓜吃。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并不见效。从此我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每年秋冬都要持续咳嗽。中年时曾经痊愈,90年代有一段时间喜欢在数学推导或写论文的时候抽烟,气管炎又复发,这段时间不长,但却发展成了肺气肿,可见还是早先那时种下的根。
8.支持进步,团结中间,教育落后,打击反动
这是政权更替的变动时期,共产党接手上海以后在经济方面继承下来许许多多的困难;战争还没有结束,国民党在大陆上还占着相当大的地盘,更何况还有台湾、海南和东海上的许多岛屿,对方电台经常在宣传着反攻的条件、决心和计划。这个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共产党政权在中国一定能够长久,清心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中也不那么平静,就是在青年团员中思想也有波动的,有些人一时热、一时冷,甚至有提出要退团的。不像后来那样总要上面来发动什么运动,那时的矛盾和斗争是明摆在眼前的,不需要去找、去“深挖”。团总支委员会上还常常研究“敌情动态”。原来的“教官”支蔚钧是最值得注意的人,据说他常常聚众聊天,在教员中散布敌视共产党的言论,当时还没有说他就是特务什么的。其它还有几个教员也有一些“落后言论”。很聪明、有能力而一向有些傲气的“小开”陈拱龢就是一个。从我初中一年级进清心他一直是我所在班上的级任先生,解放后不久升初三,班级学生作了调整,我这个班的级任先生还是他,他在课堂上下都有些牢骚。有一位原先在校的年轻教员,姓屠,名字忘了,他也和陈拱龢、王笃信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庭,但他缺乏陈拱龢那样的洒脱风度,也缺乏王笃信那样的温雅气质。以前没有教过我们课。解放以后他表现进步,努力学习新思想。所以除了有两位年轻共产党员被派到清心来当政治教员以外也让这位姓屠的教政治课,但是从陈拱龢在课堂上说的话可以听得出他很瞧不起这位姓屠的。大概是姓屠的在教员会议上发言积极,思想“前进”,陈认为他是赶浪潮、求表现,对他不齿。曾当班上学生的面挖苦他:“呜噜呜噜闲话阿讲勿清爽,还要夸夸其谈,像煞有介事!”,可见陈拱龢当时对共产党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但是他对担任的工作还是很认真。当时研究了教员中这些情况后,决定按照上面的指示,采取支持进步、团结中间、教育落后、打击反动的方针(原话不一定完全如此,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于教员在课堂上的言论,有明显不良影响的,青年团员可以当场提出批评、辩论甚至揭露。我记得沈锦辉就曾经在课堂上对陈拱龢的话举手提出过不同意见。那时陈先生兼初三历史课,讲到世界古代史时把奴隶起义称为“暴动”,这是习惯的称谓,其实这个词是中性的,但在当时和我一样刚懂一点革命道理的青年团员沈锦辉听到就很敏感,认为用“暴动”这个词是贬义的,是污蔑奴隶起义。
学生当中说起话来基本上是“百无禁忌”,有些同学把社会上传播的种种言语都带到学校来了。对他们一般是采取谈话教育,要求团员都要做这个工作。但是有少数团员自己思想也不稳,例如小矮子周维勋有一段时间经常唱反调,我们认为其中有政治思想的原因,也有“个人英雄主义”,对团干部不服气,故意闹别扭。还有一个叫顾澄的,我已记不准他当时入了团没有,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积极热情,后来变得牢骚满腹,记得他把毛泽东叫:“毛竹筒”(上海话基本谐音)。班上团小组很对这些人感到头疼。
那时来了两个新教员,都是有关方面派来做政治工作的。一个叫叶锦镛,解放以前在大学里参加过地下学运,到清心来当政治教员,个子不高,但体格壮实,他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他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给我们讲到牢狱审问中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涉及下身的摧残时有个别同学听了发出笑声,这使他非常生气。另一位新派来的教员叫潘乃熙,白面清秀,但比叶的岁数还大些。他除了教更高年级的政治课以外,好像还担任了教导处的副主任,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两位也常参加团总支委员会议,帮助青年团的工作。
同学中也有极少数人情况不一样。例如有一个叫方铓的,当时和我同班。他的年龄大概有二十以上了,据说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他能写会说,平时公开场合表现很进步,我们“庆祝开国”那天演话剧,好像有他也参加了“导演”。我发现他很会恭维人,记不清是在墙报上还是在班级会议上,他曾经大大赞扬陈拱龢,说他学识渊博,有能力而且风度潇洒等等。但是有好几个人反映他在下面传播反动言论,还渲染他自己在“反动军队”里的生活,包括和别人的太太睡觉的感觉。终于有一次由团总支书记朱永嘉主持,在礼堂里开了一次对方铓的揭发斗争会。许多人出来揭发,并叫他老实交待。他在会上的表现就像演话剧一样,哭、叫冤,声音动作都像话剧里那样夸张。一般说,我如果看见许多人围攻一个人,很容易对被围攻者产生同情心。但对于第一次见到的这场政治斗争,我在感情上没有“立场不稳”,因为方铓自己做戏般的夸张表演令人反胃。记不得后来对他怎么样了。
9.看解放区电影和苏联电影的感动
那时电影院里有一些旧的影片甚至美国电影还在上映,现在记得的有我在卡尔登看过一部反映爵士音乐与古典音乐竞争立足的爱情片子。还有一部上海的电影公司赶政治时髦,说是批判“美国生活方式”实际上以“美国生活方式”招揽观众的片子。说一对醉心“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青年与现世隔绝,在远郊造了一座铝合金板“帐篷”式的活动别墅过起奢侈浪漫的美国式生活,演出一连串尴尬闹剧。结局是在一场偶然事件中,那叫做“金屋”的房子毁了,怎么毁的我忘了,片名我也忘了。我记得男演员是乔其,女演员是个著名的京戏、电影两栖明星。是言慧珠还是童芷苓我也记不清了。原先的电影明星解放后也要找饭吃,说到乔其,有一次我们去静安寺路“大陆游泳池”(1950年代初静安寺路那一带划为“新成区”这个游泳池也改称“新成游泳池”)游泳,炳方哥哥(即后来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指着下水扶梯边上坐着的一个标准运动员体形的人告诉我:“那是乔其,他现在这里当救生员”。
但是已经有了几部老解放区拍的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每一部电影的片头都是手举镰刀、铁锤和步枪的工、农、兵雕像,配以一首叫“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曲子。在国光大戏院看了一张木偶短片“皇帝梦”,影片里做“皇帝梦”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蒋介石。后来据我的印象,解放以后国产的木偶片比卡通(动画)片多。从“皇帝梦”看起来,在老解放区就开始有了木偶片了。我看的第一部解放区故事片叫“光辉灿烂”,描写解放了的东北某城市共产党如何团结工程师,克服种种困难修复被破坏了的发电厂,使城市“光辉灿烂”起来。还有一部片子叫“桥”,主题和“光辉灿烂”大同小异。此外还有一部很感动人的片子叫“中华女儿”,也叫“八女投江”,说的是东北的一次战役中打得很惨烈,一支部队最后剩下八个女战士,为了不被敌人俘虏,手挽手成一排,毅然向江心走去,全部牺牲。后来又陆续看了革命战争片子《钢铁战士》和《翠岗红旗》,后者是小叔叔带我到华东交通部(他解放后离开了私人银行,被录用在那个部里当了会计)礼堂去看的。那天全部职工开个什么大会,会上有中共华东局高级首长之一的曾山作报告。在这些影片中看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一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抱着满腔义愤勇敢顽强战斗,最后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军民一起欢呼,首长登高做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心里感到非常畅快。
后来苏联影片出现了,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记得那时在靠近北四川路的一个五条马路交汇的口子上有两家可能是新建或新命名的电影院,一家叫胜利大戏院;一家叫国际大戏院。它们比我家附近的国光和华德两家电影院都大些,中等档次,比较简朴。我之所以认为是新的,一来是听名字很“进步”,二来是解放前我还从来不知道有它们。也许(记不大清楚了) 那时候集体来过或者和谁一同来过,并且得知这里常上映解放区新片或苏联片。那些日子我去过多次,要从唐山路朝西到新建路转周家嘴路,过小苏州河的一座桥到鸭绿江路一直往北四川路方向走,不比从我家走到大光明近。
虽然那时大光明等头轮电影院还有美国片子,但我的热情已经转向苏联电影了。实际上解放后最早看到的苏联影片好像还是苏联人帮助中国共产党拍摄的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前者记录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历程;后者描写了大部分中国大陆解放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一片欢腾,红日东升的新中国到处已然欣欣向荣,预示了无比伟大壮丽的前程。导演叫做格拉西莫夫。
苏联的彩色片子和美国彩色片很不一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颜色单调,红、蓝两色突出而其它色谱不显。而美国好莱坞的彩色片以前叫做“五彩片”还有叫“七彩片”,几乎是色谱俱全,看上去要真实和漂亮得多。这也是一些“落后分子”鄙夷苏联的一个根据,有人解释说因为苏联长期遭到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得不到国外的彩色影片技术,他们用的是他们自己独立发明的一种技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彩色技术不是同一条路子。后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中国拍摄的一些彩色影片很明显的都属于苏联那种。
最初看的两部苏联片子,一部是《桃李满天下》,也叫《乡村女教师》。另一部是《幸福的生活》,也叫《库班的哥萨克》。不管怎么样,苏联影片比当时的国产影片(包括解放前的和老解放区拍的)拍摄的质量和艺术感染力都要强些。比起美国片子来有一个大的改进就是作了国语配音,虽然那时的配音音质不好,语调生硬,而且还带点山东或东北口音,但是大体还能够听懂,比打字幕好。解放前放映进口电影一般也有中文字幕,但绝大部分不是刻在影片上,而是用幻灯机把竖排的汉字打在银幕左侧的墙上,忙坏了观众的眼睛,看了字幕还影响看画面。
不管怎么样,《幸福的生活》是一部很迷人的片子,看到集体农庄庄员们用巨大的康拜因收割金黄的麦子,唱着那首充满快乐激情的“库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库班草原在呼啸……”银幕上顷刻间麦粒堆积如山。庄员们送粮食到市镇,绚丽的市镇展现一片欢乐节庆气象。国家功勋演员们为农庄庄员演出芭蕾舞“天鹅湖”,经典歌剧“伊戈尔王”、“欧根.奥涅金”、“伊凡.苏萨宁”(电影中都打出了它们的精彩片断)。片中的几首歌立即脍炙人口。其中的《红莓花儿开》到现在还在卡拉OK厅里流行。其实我觉得另外还有两首因战争离别又重逢的一对中年恋人在矛盾中抒发旧情的歌,那感情更加浓郁而动听。一首是:“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草原的鹰,勇敢的哥萨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重逢?为什么扰乱我的宁静?……”;一首是:“不在那遥远海洋的彼岸,不在那汹涌波涛那边。我们的命运和我们在一起,就在这苏维埃祖国。……”后来还有一些类似的苏联影片如描写矿工幸福生活的《顿巴斯矿工》(那里面用一种也叫“康拜因”的采煤机采煤);描写一位女工人劳模成长的《光明之路》(那里面也有一首令人陶醉的主题歌)等等同样都以绚丽的画面和动听的歌曲展示了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灿烂幸福;人们纯洁高尚的情操;人际之间沁人心肺的挚爱。
《桃李满天下》更是感人至深。那时上海出了一种影响很大的电影画报叫《大众电影》,我几乎每一期都买。有一期着重介绍了《桃李满天下》,而且还刊登了主角演员的大幅照片。她是苏联功勋演员玛列茨卡娅,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演艺却炉火纯青。从一个革命前十六七岁,辫子上打蝴蝶结的中学生一直演到卫国战争后六十几岁的老太太,每一个年龄段都演得很自然、逼真、出色。从这里我第一次较深的接触到一种终生奉献于高尚事业的人生观。片子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完全不像我国后来宣传“雷锋精神”,“当个螺丝钉”等等那样枯燥、苍白。在我心里留下了长期深刻的印象,我想那时许多人都是一样的。直到今天我对俄罗斯的艺术十分崇敬,她的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美术都有深厚的根底和独特的魅力。特别是歌曲,也许正因为在我自己的青春时期接触得最多的是苏联歌曲,我觉得俄罗斯歌曲里饱含着幽深、浑厚的激情,胜过西欧和美国的许多民歌。
我的妹妹,比我小六岁,她叫胡田田。后来立定志愿终身奉献给小学教育事业,后来虽然由于我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使她不能不背些包袱,但她还是通过自己十分坚苦的努力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和贡献,当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直到她四十六岁英年早逝的时候,于弥留之际,还执著地叫妹夫陈志明把她正在教的那班小学生在课堂里的声音录下来,在病床前放给她听。我想华尔华娜.华西里也夫娜(影片的主角)的形象,肯定是一生铭刻在她心里的。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后来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一个弹“冬不拉”的青年人被害临死前的一句话:“我们太年轻了!”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太年轻了。在赫鲁晓夫带来的苏联第一次“解冻”以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前期,我见到报纸(可能是《参考消息》)上一篇文章报道了苏联当时批判以《幸福的生活》为代表的一批粉饰现实的电影作品的消息。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完全知道,苏联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一直萎靡不振。何况是在电影所说的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当时人们感受的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的灿烂幸福,而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和贫困。
所幸的是,我一直还没有看到对《桃李满天下》的任何微词。总算上帝怜悯,我希望这个美好的印象不要再破灭了。而我的妹妹胡田田,正是受了那个叫玛列茨卡娅的苏联女功勋演员所塑造的形象的感召,才付出她的生命来仿效那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教师的。
我还热衷于跑书店去寻找解放后的新书。在福州路(原先叫四马路)的一个路口新开了一家门面比较大的“三联书店”。“三联”是由解放前早已有的《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进步书店联合组成的。那里多为“进步书籍”。我手头钱很少,在那里翻看得多,买的极少。记得第一次买的是一本很通俗的文艺书,叫《红旗歌》,里面包含两个小剧本,都是写解放初人们的思想转变的。第一个就叫《红旗歌》,写纱厂里一个落后女工的转变;后一个剧名忘了,是写一个类似“革大”那样的政治思想学校里各种知识分子学员的思想转变过程。里面有党的领导的谆谆教诲,进步帮助落后,还有混在里面的特务坏人的蓄意造谣破坏,被揭发,最后群众擦亮了眼睛等等。这种剧本特别适合刚解放时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当时在上海还有一台根据真人真事编排的话剧,影响很大,剧名叫《郑依柳的转变》。据知郑依柳是上海中西女中的学生,而中西女中是上海最典型的贵族化的教会女中。学生中剥削阶级出身的小姐居多。娇气、对“欧美生活方式”的崇拜、对解放后新事物的疑虑甚至抵触,在这里也许表现得比较突出。郑依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后来终于在周围帮助教育下转变得非常好,还入了团。这个剧本被拿到很多学校去排演,可惜我虽熟知这个事,但没有直接看过这出戏。
我还很感兴趣地看了胡绳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廖盖隆写的《解放战争史》,还买了冯定写的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平凡的真理》,记得这些都还是在清心中学初中时候的事。
10.爸爸当了里弄“冬防大队长”
解放后第一个冬天,人民政府指导在各里弄组织“冬防大队”,任务是防火、防盗、防特(国民党特务)保证治安。实际上好像还准备从这里开始为建立后来常设的“里弄居民委员会”做准备。不知怎的,爸爸被选为“冬防大队长”。现在我想大概有几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当时闲在家里;他有文化;他做事严谨、讲原则(虽然谈不上是马列主义的原则),在一些知道他的人中间口碑较好,难免有人举荐。但是他在家里私下说他心里很有顾虑,他说:“怕在政治上又留下污点。”这个“又”字的意思是说他过去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公务员已经是一个污点了。我觉得他思想够落后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
后来大家一“抬桩”,他这个人就是吃不住别人的捧,同意了,干起来却又是像煞有介事,作古正经忙得团团转。他们还有一个“班子”,好像叫“队委会”,包括了“各阶层”的人。记得其中有一个住在隔壁一条巷子、做过甚么校长的,名叫程凤庭,是个斯文人。他的太太原来是我在唐山路小学的老师叫吴有文。委员中女的好像不比男的少,有一个大概是女工人,长得还比较俏,叫施培英,说话叽叽喳喳的。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中年妇女,因为我在四川住过,听得出她是湖北人。许多年后婶婶还常常提起她的名字(因为后来婶婶和她一起张罗过幼儿园)。于是,这些人常常出入我家,商量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看到爸爸想通了,而且如此投入,如此认真,心里很高兴。
里弄居民代表多次开大会,会场就在79号到85号前面的大天井里。爸爸主持开会,报告工作,读文件,传达上面的精神,这种会开的热闹得很。这是解放后的新事物,不少人都蛮起劲的。几个月以后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居民会上讨论一个什么重要活动,我正好在家,也去参加了。我在学校里早已是“团干部”了,开会讲话是家常便饭,可是家里人没有见过,还把我当个小孩。在那个会上我站起来就一个什么问题发表了一大通意见。那时爸爸正好在家里和别人个别商量着什么事,会由程凤庭在主持。不知道家里是谁赶紧回去告诉爸爸说:“快点去看伯威在发言!”,爸爸急急忙忙从大门跑出来看,听到我在大庭广众面前侃侃而谈,很感意外。从这以后,他把我看作可以和他平等地谈谈事情的人了。后来里弄里是搞了一次募捐活动,正值暑假,我也参加了,挨门挨户宣传、要钱。那次募捐很有成绩,爸爸就叫我给《新闻报》(后来改称《新闻日报》)写了一篇报道。那篇豆腐干文章居然登出来了,成了我的第一篇“大作”,报馆寄来了稿费单,我取出来去三联书店买了几本书。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