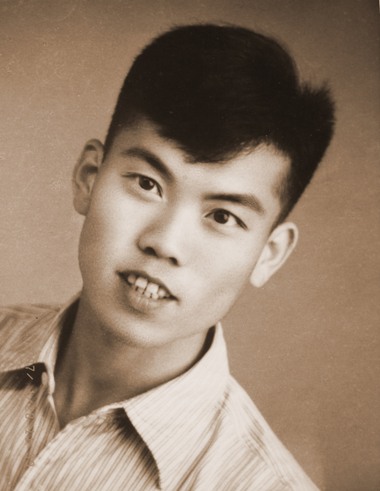第二节 “右派”加“特嫌”双加料的反动分子
我怎么被“加冕”为“苏修特嫌”啦?
话要从头说起。1966年8月,我的妻子安娜的舅父自苏联来到我家,当时安娜的母亲在我家住,是特意来兄妹相见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从国外来客人,又是从“修正主义”国家来的,更引人注目。舅舅从哈尔滨乘火车来吉林,安娜恐怕在吉林站接不到于是就由江北站上车,想在车厢里找。刚一上车,列车员就看出来是接外国人的,直接领到软席车厢,立刻找到。到家不到半小时,派出所的警察就来到家里,查看护照,盘问情况,并将护照拿走,告诉走时去取。不知是否原来上边早已通气,已被监控,防备外国人干坏事?
自此以后,安娜和我就被倍加注意和防范。“清理阶级队伍”时,安娜被怀疑是“苏修特务”,我也加码为“苏修特嫌”,成了双加料的反动分子。后来安娜还被立案称“511案件”专案调查。怀疑是舅舅来联络,交待特务任务,等等。纯属望风扑影。不,无风也扑影!
正是由于这层渊源,我长时间被抓住不放,反来复去地检查交代问题,就是过不了关。因为我不知道我被认为是“特嫌”,所以检查不到这方面的事。总是被认为避重就轻,不交待实际问题。一直到1969年冬天,我仍然被“挂”在那里,总是被监控着,整整一年。
1969年4月,有一次在同一个班里的一名叫邹明起的工人问我:“老马,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没交待,怎么还不被解放?” 我回答说:“我是右派谁都知道的事,还有啥须要交待的。” 这时,邹明起说:“那为什么咱们连长支春禄说你是‘苏修特嫌’?” 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抓住我不放,不然我还真的被蒙在鼓里。
后来,到了5月份,我被检查出体内含汞量超高,汞中毒,不能再在有汞的环境中工作,于是我离开乙醛工段,被调到同一个营的丙烯氰车间合成工段泵房岗位继续倒班。——顺便说说,生产丙烯氰的原料氰化氢是剧毒物,在此工作的工人每人吃一等保健,每月给2斤白糖解毒,并发给注射用硫代硫酸钠以备急救;但是没有我的份,似乎我不会中毒。这就是当年对我的政策。——在此期间,我在班组的一次检查批斗会上,有意阐明关于舅舅来吉林的事,但并无作用。
不久,取消营连的建制,恢复原来各个车间的单位,醋酸车间与乙炔车间合为一体,我分到乙炔工段当加料工。在这里同班的一位暂时下放劳动的大学生王庆良对我说:“我问过咱们车间书记王延禄,为啥马吉卫还不解除专政?他回答说,你是‘苏修特嫌’。我又说,也看不出像特务呀。他说,那家伙很狡猾的,能让你看出来?”
实在没办法,这个重负我一直背负着。我难以理解,为什么普通群众看问题明明白白,谁是不是特务一目了然,而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却咬着木棒当骨头,真是中了“阶级斗争论”的毒太深了!对他们来讲,真可谓“四面楚歌”呀!
毛泽东有三个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他的斗争哲学之精髓,其中“与人斗”作为他的人生主要目标和动力,总是给自己给共产党甚至给国家树立“假想敌”,于是就将一些民众。 友人,甚至同志,向敌人那边推;把斗争的心态带到现实生活中,结果反而给人民、给党、 给国家造成危害。
直到1970年1月10日,这一天我们班是上副班(不在岗位生产,而是干其它的零活),上班以后开会,班长(姓杨,忘记名字了)拿来一张具有车间书记王延禄签字的公文纸,宣读:“解除对马吉卫的专政”。
我是全单位最后一个被解除专政的。那时,被揪斗的人,几乎全已被解放。“解放”一词在我身上还都不适用哪。
如此结束了一年零五个月的被专政的生活。这要比戴着“右派”帽子改造的四年更漫长,更受折磨,对心灵的伤害更深。戴着帽子那时还期望着摘掉帽子会有未来,而此刻真的茫然了。
第三节 被谴送去农村
(一)下乡政策缘何而来?
1970年上半年,不知道是根据党中央的什么文件或是什么规定,吉林省出笼了一项“下放”政策,把城市里的“牛鬼蛇神”下放到农村去。当时电石厂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下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姓许,开始了下放、遣送行动。农村成了这些人的疏散地。依据当时吉林省的规定,这些人下放的地点之选择有三条原则:第一,远离城市;第二,远离边境;第三,远离铁路线。电石厂的指定“飞地”(下放地点)之一是蛟河县白石山公社,是属于山林区。被下放者本人和家属一起下去安家落户,每口人发给80元建房费,划拨给所在的生产队,由生产队负责给建房。
令人难以捉摸的是,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没有个准。在下放到农村之后得知,指定被下放到农村的有三种人:一是刑满释放人员,二是保外就医人员,三是监外执刑人员。而像我们这些人,即不是“五七战士”;也够不上“下放干部”资格,带着工资下农村,吃供应粮,干活所得的工分给生产队;连社队干部都不知道这帮人算个啥人。有些社员说,反正“屁股没粑巴”不下放。倒是也有政治水平高的明白人,说这是战备的需要,像这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一旦战争爆发,在城市里他们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云云。是啊,按毛泽东的说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人;当时全国有七亿人口,余下的这百分之五可是一个庞大的“第五纵队”呀!
难道这就是下放政策之依据乎?
(二)落户农村
1970年6月9这天我是上四点班,上班以后,在开班前会时,车间主任支春禄来到班里,对时任班长李炳兰说:“马吉卫下放去农村,别让他上这个班了,让他回去吧”。他同时还与我个别谈了此事。于是,我便离开了车间。
本来,下放之说早已听到,染料厂开始的最早,电石厂有的人在3月初也有的人已下去。据知,在4月份时,电石厂就已与染料厂沟通,让通知我的妻子安娜与我一起下,但染料厂说,我妻子的“苏修特务”问题尚无结果,暂时不放。故而推迟到此时。
我的下放场所是蛟河县白石山公社宏胜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时电石厂的被遣送到吉林省蛟河县白石山公社的人员名单中,共有“牛鬼蛇神”15名,其中“摘帽右派”5名:洪钱林、张家驹、马吉卫、齐正文(以后改去别处,他是在摘帽后调来电石厂的)、吴仲簿(后因患重病没去)。这是我在白石山公社办理手续时看到的名单。洪钱林和张家驹下到富强大队。与我同到宏盛大队下放的是有其它“问题” 的两个人:一个姓王,在第五生产队;一个姓孝,在第三生产队。
早在1970年4月24日(记得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那天),我母亲患心脏病住进吉化职工医院,为了照顾母亲,我的二姐姐于五一节时来吉林在医院护理。老人患心脏病是个慢性病,以后又得了尿毒症,长时间出不了院。通知我下乡时,我就已将下放搬家的事准备了,打算只要妈妈稍好,我们马上就走。
有一件很不人道的事,使我难以不永记在心。电石厂下放办公室姓许的主任,命醋酸车间的专政组的人去医院找医院的负责人说:“内科住院的老马太太是下乡遣送对象,不管病好不好,撵她出院”。 内科病房大夫姓未,办出院手续时,他对我说:“老太太的病挺重,出院有危险,上边让你们走,没办法,回去多加护理吧”。1970年7月19日妈妈出院,21日一大早就把我们全家送走,年已78岁的病老太太经不住如此折腾,到了白石山妈妈就立刻住进了白石山公社医院,幸亏有我二姐姐陪同住院照料。我们家人被送往山沟里宏盛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时押送我们去的群众专政组的人一个叫王东,另一个叫王凤国。因为山沟里汽车进不去,他们把东西卸到沟口的一位“五七战士”家的门前,就回去了。待了两天,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找牛车往沟里运。幸好我家穷,没有值钱的东西,放心。
妈妈在白石山公社医院一直住到深秋。在山区道路崎岖,连牛车都难行走,颠簸不停,为了让妈妈不受更多的折难,一位姓曹的社员,用独轮手推车把妈妈由医院接回来。独轮车的两侧各放一个圆筐用绳子绑牢,妈妈坐在一侧的筐里,另一侧放物品保持平衡。推车的人要有力气又要有技巧,否则倾倒了就要伤着人。从医院到我们住的沟里相距15华里,整整走了一个下午,难为推车人社员曹大哥的坚持,也难为坐车人的煎熬。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年人跟着走,都心惊胆颤。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万分感谢这位社员曹大哥。
这位社员曹大哥的友善,与让撵妈妈出院的那个许主任,两下相比,什么是人道主义?让我感激谁?
(三)农业劳动
到了宏胜第一生产队,我家被安排暂借住在一位叫马福厚的社员的房子,是他家的一个小偏厦,一间房,大约有14平方米,一半作卧室,一半作厨房,中间间壁起来。卧室有一铺炕,长2.5米左右。大家挤着住。妈妈自白石山医院出院后,住不下,没几天二姐就带着我的第二个孩子去黑龙江克山县她家了。二姐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侍候妈妈的病,又为我带大了孩子,直到上学才回来。到下一年,即1971年的秋天,生产队给我家盖的新房子盖好了,我们搬入新居。新房子共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很感谢我们的生产队。
我住的这个屯子,有两个生产队:宏胜一队和五队,总计有百来户人家,多半是外来户,没有户口或是临时户口的,那时被称之为“盲流”,多来自山东。我们一队的生产队长姓象,忘记了名字,是关里来的“盲流”;生产队的副队长,人们称作“打头的”,姓王,叫王普乐,是从江苏赣榆来的也是“盲流”;都没有户口。这些人,在一个地方看好了就干,不好了干到年底,算完帐拍屁股就走。生产队会计叫李凤池,是当地人,也是关里来的,只是时间长了,有户口的。大队部也设在这个村里,在村的入口处;当时的两名大队干部是:书记姓孙(后来换个姓王的),会计姓孟。
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我就上工干活。 在农村,社员有句话:“一天三顿饭,围着太阳转”。只要日头出来,就上工;太阳不落山,不能从地里回来。我刚到乡下时,正是大暑季节,白天开始逐渐地短,但仍然是昼长夜短,一天15个多小时的劳动,还真有点不习惯。看来农民比城里人辛苦多啦。难怪“被改造者”动不动就往农村放。但这里的劳动时间虽长,效率并不高,在焅时间。时常听到社员提到以前分田到户的事如何如何。
我们生产队有两家“五七战士”,一位是吉林市龙潭区原副区长娄振声同志——后来回城后任龙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我当政协常委时与他常有接触);另一位是龙潭区卫生大队队长姓沈,不知名字,其妻子原是龙潭区某小学教师,到这儿也在小学校当老师,人称隋老师。“五七战士”也参加队里的劳动,工分归生产队。但不经常干,有时还在公社干事,他们不参与队里的任何官方事务。
生产队有一个集体户,有下乡知识青年十人,五名男生,五名女生。都是吉林市第十六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到这“广阔的天地”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刚到宏胜大队时全队还没有电灯,直到这一年的入冬时,才给拉上电杆和电线到各个村的村口,村里的线杆和电线由村屯自己负责。这年冬季有了电灯。
农活我能干,我是在农村长大的。1947年11月,刚解放的家乡开始土地改革,那时我家分得土地八亩八分三厘。我在考入沈阳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前,曾在家兼种地二年(1948年和1949年),那时,我边读书(在海城第一中学,现为海城同泽中学),边帮家里做庄稼活。因此我对农业劳动不陌生也不惧怕。
七月正是铲二遍地的时候,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钻到里面,又闷又热。铲二遍地比较容易,不用分苗,只锄草和搂地。在挂锄之后,就开始间秋菜,铲秋菜地。到了9月开始割烟叶、编烟叶辫子、晒烟。蛟河的晒烟很有名。实际是指漂河烟,后来全蛟河县的烟都出名了。接着是种冬麦、白露种小葱。中秋节一过,先要收秋葱,因为有一种说法:“八月葱九月空(指农历)”,意思是大葱到了农历9月如果不起出来在地里就空心啦。紧接着就开镰啦:先割稻子,再割高粱和玉米,最后是割豆子;轻劳力掰玉米棒子,掐高粱穗。上冻前要把秋菜收集完。秋天的活一个紧挨一个,所说的“三春不如一秋忙”,正是这个道理。
到了打场的时候,就比较缓气了。一般的是,先打稻子,因为稻子在秸上容易“捂”,怕出芽子。至于高粱、大豆等,可以到上冻后打“冻场”,缓空。农活忙完,整个冬天搞副业:打草帘子,上山拉木头,割条子,打柴,等等。
我在生产队干活,比不上壮劳力,但也能顶上“个儿”,每天下工后评工分,得不到满分。我去的第一年,得了不到一千五百分,五个月的时间,相当于每天平均得9分。一天满分是10分,那年(1970)的工分值是7分5厘,相当于每个壮劳力一天赚7角5分钱,这是中下等水平;好的生产队一个工2元多;有孬的生产队一个工只得三两毛钱,听说有的队一个工才2分5厘;更有甚者要倒找钱的,上工干活不如在家闲着——这只是听说,不知在那儿。
年底算账分粮 .农村就这手好,生活上有保障,饿不死,也撑不着。有句话说,“够不够三百六”,意思是说,农村人口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年360市斤粮食。生产队给送到家。队里打的粮不够分时,就吃返销粮,个人拿钱,按收购量价。——正是因为这样,农村人对于生孩子放心,多一口人多一份粮,补贴一下大人的肚子。
从元旦到春节,农村该搞运动啦,这年冬天搞的叫什么“社教”。都是离不开“阶级斗争”那一套。农村搞运动更有其特点,都是家族式的,这一伙对那一伙;坐地户对外来户。根本没有谁错或谁对,最后哪伙人多,那伙就赢。“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勾心斗角。
咱们生产队里还真有个“坏人”,是从吉林市监狱放到这的监外执行人员,人们称他叫“小劳改”。谁也不叫他真名实姓,我也没打听,说不出。他原来是个唱什么戏的,因为强暴女人进的监狱,来到这里,他应当是正牌的“三种人”下来的。但在他的身上并不能反映出什么“阶级斗争”的迹象。
“算盘响,换队长”,这是农村的一句常嗑,前任姓象的生产队长人走家搬蹽竿子了。这种无长远机制的生产单元是不会有发展的。“社教”后产生了新队长,姓孙,啥名忘了。
第二年,1971年春,开始新的一年农业生产。犁地、坺地用牛拉黎,这些要使用牲畜的劳动有专人干,一般人不会使牲畜;其它的活,那时全是人工干,生产队里没有农业机械,全大队连一台拖拉机都没有。解放二十多年,农村变化未见明显。
那些须要农业技术的活咱干不了,只能干耙地、播种等非技术性的活。踏窝子、撒种子、上粪,这些活较为容易,只要用心认真做,一会儿就学会。不过撒种要找准了,多啦浪费少啦保不住苗,一窝玉米三四粒,一窝大豆六七粒。有句农嗑说:“豆豆四五六,一撒手七八九”。掌握不好就浪费了。
各种农活项目与前一年差不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好。
这年,也给我家一块自留地,种蔬菜用。讲起这块自留地还有点说道。事情是这样的:队里一位叫孔繁福的社员要迁移到蛟河县天北公社,这年的年初他妻子对我妻子说,“我们要搬走啦,我家这块自留地给你家种吧,反正队里也得分给你家地,我们这块地离家近还挺肥沃的”。就这样,双方默契。在开春时,我向生产队孙队长说这件事时,这位新上任的队长发火说:“他有什么权力把地给你?土地归生产队所有,他走了应当把地交还给生产队。至于你家的菜地,生产队会给你的,给你啥算啥。”此话确实有道理。我回答说:“我听从队里安排,反正现在也没开始春耕,来得及。” 但是到后来,这块地还是分给我家种了。
后来,从社员中了解到,并非这位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而是姓孔的与姓孙的之间的事。
据了解,这位姓孔的原籍河南,是抗日战争期间便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以后并入了党,而且是负过伤的轻微的残疾军人,在1970年那个时候,每个月政府发给他残疾补助金12元,由公社按时发放。他在解放初期,因为与家乡的一位姑娘的爱情关系,未通过组织两个人便私奔了,结果党籍也丢了,这真是一位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人。后来辗转来到东北,落脚到了此地,算是外来户,也曾当过生产队的干部。(他的儿子叫孔祥义,是那时村里唯一的一个中学生,老孔还让我给他做过学习辅导,每天晚上到我家学习,直至“社教”开始后就不好意思来了,是个很上进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位姓杨的(夫妻二人无子女)党员,原籍山东,也算是外来户吧,也曾当过生产队干部。孔杨二人较为接近。在“文革”期间,算是同一个观点的,属于一个“派”。另外还有一位姓于的老汉也是党员,山东人,外来户,三个人是一伙的,代表着一派人,但这位姓于的后来“杀了回马枪”,算是“反戈一击”有功,与那一派和好了(也有人说这位老于头并非“观点”改变了,而是因为与另一派的人有姻缘关系;他的养女,即后老伴的女儿嫁给了另一派的人)。
另一派人就是新任队长这一伙,这位队长的亲哥哥就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他们的同母异父哥哥姓高叫高宝德,是前任大队书记,老者为人忠厚,当时在队里做木匠活(那时给我家盖房子的一切木工活都是他做的)。在“文革”期间他们是代表着另一派,但此时高老头已不参与这些派系争斗了,直接出面与对方交锋的是那位现任书记,因为他领导搞“社教”呀。
对这年冬天队里的“社教”活动我没有参加,咱是外来人,不便于参予,人家也不想让咱知道内情。侧面了解到,得势的那一派还把老孔关起来圈在大队部里,由下乡的知青看管,还挨打——时至1971年1月农村还这样搞,在城里,这是1968年正时兴的,看来农村滞后两年。偶尔一次我去听了一回会,听到孙书记在说老孔:“老孔,不要以为你是参加抗日的,我告诉你,老的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不改变态度是不行的。”——不知这是林彪的观点还是“四人帮”的语言,我想不会是他老人家的教导吧。对此我不加述说。
或许是因为“社教”后的形势致使老孔离开了这里,搬到天北公社去啦,不得而知。那位姓杨的老党员也离开了,但不知去向。
到1971年的夏季,大队书记也换了,从外地调来一个姓王的。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