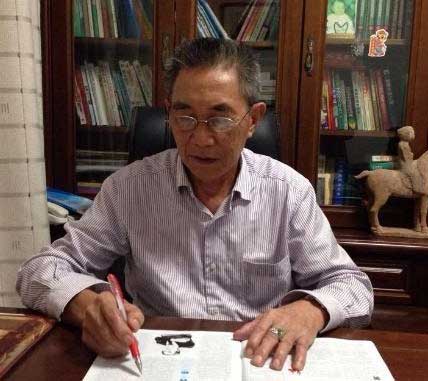206、龙五
自1969年九大召开后,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无限上纲。随着阶级敌人的增加,五类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每年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势必成立一个规范化的伙食团来承担后勤工作。自原来开集训会的文秀祠堂拆除建了新开完小之后,新开完小就成了固定的五类分子集训场所。该校由四合院组成,可容纳三十几个班上课。不仅场地很宽,且周边与民屋远离,独立清净,很适合搞阶级敌人集训。
原来文秀宗祠的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我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不如改成“所斗在此,集训于斯。”文秀祠堂消失了,对联留在记忆中。新开完小没有对联,可“龙五”却留在记忆中。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永远坚持,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集训会就要一直开下去。于是伙食团专门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作了永久打算,并有专人管理,在所有的炊具用具上,用大红瓷漆写上“龙五”字样。
所谓“龙五”,就是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的简称。
看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心里有了底。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着:看来“龙五”已经成了一个单位名称,老“龙五”死了,难道有新“龙五”接替补充吗?阶级斗争扩大化,陌生面孔不断出现在这个队伍里,“龙五”会变成“龙六”“龙七”了,还有“龙二十一”。
有个姓游的分子对我说:“当时一看到”龙五“字样,心里就冷了半截,好像帽子要戴进棺材。如果那样,管制是永远的,怎么改造也没了希望!”
在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中,浏阳全县共划右派分子561人,其中小学教师划右452人,占总数的80.57%,占教师总数的18.2%.浏阳三中24名教师划右16人,占该校教师总数的66.67%.后来陆续摘除右派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后来右派得到改正纠错,四类分子摘帽,浏阳全县共10380人。
在大队申报摘除我的右派帽子时,不仅要整理上报改造表现的材料,还要开社员会讨论签名。有人告诉我,会上大家都认为你劳动改造和写写画画都是认真的,是老实改造的表现。只有一个大队领导举起右手说:“大家同意摘就摘吧,不过帽子在我手里,只要他一不老实,就是这样一下罩死他!”说到这里,这个干部右手下划,做了一个狠狠扣帽子的手势。
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四类分子全部摘除帽子时,少数贫下中农也是想不通难以转这弯子的。队上有个姓潘的说,如果都摘除帽子成为社员,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这种坚持极左路线的人已习惯于搞斗争了。似乎得了神经过敏症,时刻看到敌人,时刻想到斗争!
如惊弓之鸟的“龙五”们,在摘除帽子以后,都心情开朗,都积极出工,都积极搞家庭副业。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状态也大大改变,一般生活水平都在中等以上。并且教育后代遵规守法,认真读书。我所在的江美大队共有十几名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学生进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还有子弟当上村长、木工厂长等,政界、商界、企业界、新闻教育界的都有。这是一种发愤图强,扬眉吐气的精神动力促使着龙五的后代们向上进取的结果。
自然死亡和摘帽平反,使“龙五”这个名称在社会的复兴时代消失了。这样带来的是社会更和谐,人心更凝聚,人民更安定,国家更强盛。并没有“不知多少人头落地”的惨剧发生。
现在的新开完小,已经改建成了“长沙市直属机关希望工程”学校。原来“龙五”的集训场地不复存在。标上“龙五”的炊具什物老早处理了。原划过“龙五”的人快离人世,最年轻的我也接近耋年,下一代将不知“龙五”是什么?龙五,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历史中消失了。
207、打不死的程咬金
程知节,济州东阿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军,归唐后从太宗,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常先登,功封卢国公。其实他本名叫程咬金,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故事脍炙人口。而“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话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至于程咬金为什么要挨那么多打?为什么打他不死的原因就不去查史考证了。要说的是文革时期本地也有个“打不死的程咬金”!对龙伏公社太白生产大队的人来说,这是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他是太白董头湾人,姓刘名武成。无后,入继兄子为嗣。历年的“龙五”集训会,我都看见他在队伍里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知他戴的什么名分的帽子,总之是受监管的五类分子。五短身材、性格好强、善谈好辩、眼神犀利、下唇微突。从外表看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人。冬天,鸭舌帽檐低压,乌黑的脸容很难完全暴露。
落实政策摘帽后,他以学生家长名分请龙伏中学几位老师去吃过饭。他出示的证件本我也没看,一直不知他的详细经历和个人身份。但对“刘武成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倒听到很多人是这样说。也未曾打听过为什么要挨打,为什么打不死等。
后来听他的族弟福桂说:文革爆发后,他跑到北盛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湘江风雷”,扬言要报复曾经多次打过他的大队干部。可他作错了用神,以为红卫兵会帮他的忙。殊不知红卫兵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蒋司令和郭叫鸡(浑名)把他带到社港镇,派供销社某干部趁夜到太白报了信,太白干部马上派民兵突击把他抓回来,关在大队部。
第二天就在大队部捆绑吊打。跪在板凳加压棍,有的用四个竹尾巴捆个把子抽,背上鲜血淋漓像剐了皮一样。有的用扁担打,有的把草灰塞在眼睛和嘴巴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只有奄奄气息了才收场。由他胞兄用土车子推回去的。这么多人打,打得这样恶,也没有打死。真是经得打,“打不死的程咬金”外号就这么出来了。
富贵说,没想到这个“程咬金”不但没被打死,最后居然活到九十多岁,刘武成一次对他说:打过他的人有几十个,都没活过他的寿年。其中陈刘沈等几个干部打他最多最狠最恶,可是他们都早死了,都去吃了他们的烂肉(哀筵),只差一个人还冇吃他烂肉……
可是就是这个仇家,他也还以他特别的方式惦记着。
一次同乡沈汉喜对我说:“上次路上碰到刘武成,八十多岁了,他说准备去买个猪脔心,搭车到中医院看望个人。××在那里住院,是最恶最冇良心的人,当年只想用扁担打死他。刘准备去送个猪脔心换下此人的心肺,因为当年恶打他的仇人都死光了,就差这个家伙的烂肉还冒吃到啊!”
我们都感叹,八十多岁,还这么英耀(强壮),挨了那么打,反而添了寿,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一次我到龙兴寺,扯起“程咬金”,几个堂弟就说:“解放前武成在云南卢汉部下当文书,解放时,卢汉在云南起了义,他就属于起义军人。1958-1959年还在干坑源小学教书,后来说他是兵痞划了坏分子,就成了五类分子受管制。他也有靠山,县监委宋某的妻子就是他作的媒人。据说他打报告告翻了××人,又为坳上塘争鱼的事出了主意,占了上风。所以,这些人耿耿于怀一直要搞垮他,认为划成分时把起义军人划成兵痞,就给他戴上了紧箍咒。没想到他命大打不死,活到九十多岁。后来还落实政策,晚年能拿到津贴。”
我五二年在浏阳读书时于北斗街碰到过这个程咬金。他说他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和平解放浏阳时迎接过解放军。
后来很久未见到过他,2005年冬我在黄桥遇见他,他仍是把鸭舌帽低压着,只是穿件旧式棉大衣,走路很精神。他很兴奋地说:“今年八十七了,程咬金是打不死的。增了寿年,政府有钱发下来,生活倒安逸。”
去年因修浏醴高速路老家拆迁的事,我回乡住了几十天,才听说他于2008年正月夜间外出时,失足倒在池塘淹死了,享年九十岁。
兵痞也好!程咬金也好!幸而大难不死!这个老人家最后还是安然度过了晚年!只留下了“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长名古记。
208、怀中的官印
1966年10月26日,浏阳县委组织1600多名学生代表和100名教师代表,去天安门接受检阅。从此红卫兵开始全国性大串连,浏阳县设立接待站安排食宿。在大串连鼓动下,浏阳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树旗帜,以观点划线,分别成立“革筹会”、“革联站”,派性泛滥。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波及长沙,浏阳党政机关被夺权,工作瘫痪。同月,中央派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出台后,约束了混乱局面,抑制了局势的“恶化”(以上据地方史)。
在文革形势的背景下,红卫兵在公社和大队的夺权闹得火热。我所看到的是马源的陈赞黄为“红色造反者”头头,和瑞的沈喜生是“农联”的小头目,上源的刘全兵是“工联”头领。但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湘江风雷”,龙伏的头头是李掌珠、黄觅仙、刘定一、寻扬名等。听说红卫兵夺了权,在任干部就交出公章。红卫兵坐了办公室,原干部就叫“靠边站”。不管夺权还是被夺权,也不管运动搞得如何轰烈,我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不出工就缝衣,为着生计在劳动在奔波。
一日,我的堂伯父突然来到,一番闲谈之后,他严肃和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从纸包里亮出一枚“浏阳县龙伏公社”的公章,说“我是‘湘江风雷’的,大家推举我坐办公室,我们夺了权,干部已靠边站了。”我顿时想起此前我们几个五类分子在洞庭水库堤坝上议论文革的一番话:文革是一场政治演习,发动文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伯父以前是喜欢摇唇鼓舌、谈论历史故事的,而且是声调高亢,有时口气咄咄逼人,有时哈哈大笑。这次来的目的按说应该是亮一下当前的身份,说明已踏上仕途,走上官运。
但他神情异常,似乎并不显得如何得意,没坐多久就走了。他出门时只说了一句:不管什么组织的红卫兵,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
没多久就听到锣鼓响,队上的男男女女都跑到大路边去看游行。这次队伍里被示众的人是“湘江风雷”的大小司令、五类分子以及从边地清洗回乡的地主子弟邓。大家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嘴里喊着“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的烂洋瓶等自我打倒的口号。从龙伏出发,经石江、黄桥、南岭、坪上、焦桥、新开、春田等地,绕道做了一个大圈子,约有二十多华里路。看游行的人很多,大家都是等着看热闹,看高帽子。
我堂伯父自然也在其中,他没有走上官运,倒是赚了一顶高帽子戴了,也赚到续娶老婆的几句教训和羞骂。骂他老不自爱,还去文什么革,造什么反。风雷风雷风了一个高帽子,是上了“觅仙司令”的死当。
不过伯父虽然没有“风雷”出什么名堂,也算是上了一个当。但不能怪“觅仙先生”,觅仙先生也应是无数上当者的一个而已。但伯父和觅仙先生、刘定一先生却因“湘江风雷”结成了朋友。
伯父于1985年3月4日去世,享年68岁。治丧期间,我为他扩绘了一个遗像作为纪念,撰写了一副灵联作了评说。而他的“湘江风雷”造反派朋友们,更重义气。黄觅仙先生前来悼唁撰奠挽联,刘定一先生送工扎了一栋灵屋。这也算是特殊时期结下的历史友谊吧。
有关伯父,可回眸前文“保长们”一节,以深其印象。
209、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009年春节后,为了找到浏阳法院对“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原判判决书,我特地来到石江村村主任沈思之家。沈思之即读书会一案我的同案犯沈皆遂之子,他说好像看见过,便到一间潮湿发霉的杂房里,翻箱倒柜,对所有书报文字进行了详细清查,没找到我需要的原判书,却找到了他父亲的履历表,还夹杂了他要求平反的上诉报告、个人自传毛稿及未完成的正稿。
我这个早已在11年前去世的难友,在这份自传草稿里的第七页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七零年三月十一日,我正在和社员们在田埂上干活,突然有人喊我去大队部‘有事’,说什么我又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坚定地表示,我如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反革命嫌疑没有向党交代,可以与他们同罪,甚至可以立即枪毙。”
“可是无情的绳子套上了胳膊,我被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武忠国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对我和我五岁的孩子进行了非人的迫害。甚至让孩子站在大雨中淋湿,逼得可怜的孩子从阴沟中的泥水里爬进关押我的房间里来找爸爸。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务员竟有如此的残酷!结果呢?随随便便抓来,三十一天后又随随便便放了。并威吓我不准上诉,上诉了就与陈朋飞一样,送茶场,受大会批判。”
“回到家里,我打开上了锈的房门,看着生了绿苔的房子,我又伤心地哭了。好心的邻居老人劝说我好好抚养孩子,慢慢过。我抹掉眼泪又出工去了。”
在另一页正稿第一页,也记述了上面的事:
“七零年春,我和五岁多的孩子,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我对莫名其妙的被抓,又不了了之的释放,痛不欲生。因可怜五岁多的孩子举目无亲,才未自尽。”
沈皆遂于1999年3月27日因病突然去世,去世时我借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还开卷摊在他床头的书案上。他留下的上述文字所幸未化为纸浆灰烬,为我写本文提供了可靠证据。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离皆遂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而离他“无故关押三十一天”的1970年3月11日就已隔四十年了。往事未如烟,我清楚地记住了我被传讯却未抓捕的那一天,也就是这同一天(1970年3月11日)。本是阳春三月柳暗花明的好时光,然而老天对人间有所感应,却很阴沉,似有不祥之兆即将降临。
早饭不久,队上还未敲钟出工。治保主任板着脸闯进门来,严肃地宣布:“到石江陂云公祠去开会,有重要事,可能要蛮久时间,把中饭一起带去!”
我提着妻子装好的饭袋,瓷盆里的米饭上放着煎鸡蛋饼,竹筷子横在瓷盆上。我走出大地坪老屋,沿着去云公祠的老路,走在前面。我没有问及去开什么会,心里已感到“来着不善”。但我没有想到此去是“传讯”,是面临一场无风起浪的“政治”迫害。
治保主任把我带到云公祠东边的仓房那边,有人已在等着我的到来。
“最近外出了吗?到过些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一连串的讯问我要老实交代。
“出工和做衣是外出了!出工在队上,做衣在市主家。出工是和社员在一起,做衣和妻子在一起!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证明!”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讯问。
然后他们指着关在仓房里的人说:“与这几个人有往来吗?和他们一起去做过什么事吗?”
“我与他们几个人从来没有交往。只皆遂是邻居,每日都见面,但没同他外出过!关于我的行踪,请查队上的记工簿,并可到市主上去调查。”
传讯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我回去,说有事再传我。他们先去调查一下。
我提着饭袋回到家里还未坐定,祖母和妻子就围过来惊恐万状地问:“看来今天的情况不同,治保主任的神色很可怕,到底开什么会?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看见传来的几个人都是地主子弟,陈朋飞、陈不凡、沈长美,还有皆遂等。他们都关押在云公祠,只放我回来了,说再去调查,有事再传我去。要我不出远门,只准出工做衣。
云公祠的仓房又派上了用场,恢复了土改时的班房,私立法堂。吊打捆绑闹了几天之后,皆遂父子另外关押在石江学校,陈朋飞等送到三里坪茶场强制监管。
但几十天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人都放了。既未送到火官庙去判刑劳改,也未公开解释被抓原因,更没有补记工分赔偿道歉。反正“不准上诉!”,就这样“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四十年后,陈朋飞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尚健在;皆遂也是退休老师,已去世;沈长美是能源办的沼气池技师,停工在家养老;陈不凡孤身一人,进了养老院。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但回忆这起莫名其妙的关押和不了了之的释放,以及所受到的迫害和摧残,仍记忆犹深。
2008年秋,为了写“沈载得轶事”一文,我去陈朋飞那里查阅陈氏族谱,顺便问起他们在四十年前关押在云公祠的始末情况。
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周洛买楠竹,顺便去石柱峰看看风景,却被人密告是搞反革命组织。在云公祠和石江学校关了个多月,又不敢判刑,最后就放了我们。我要求补记工分,就把我送龙伏茶场劳改,茶场回来又挨斗争。长美被吊起来挨打,鼻子都打出了血。受几十天迫害也冇办法,下面是无法无天的,胡搞乱搞的。他们私立法堂就是违法的。”
“不过他们这些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讲你也晓得。政府还是明,后来落实政策救了好多受难的人。我现在每月能领二千块钱退休金,算是个好结局。皆遂更好,儿子入了党,当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了大学。我陈朋飞还是原朋飞,沈皆遂还是原皆遂。硬要把好人打成坏人,真是地方无鬼不遭瘟呀!”
五十几年前反右,我和皆遂等几个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送到火官庙判刑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证据之一,就是去石柱峰的东山之游,被密报成反革命测量据点活动。而皆遂和陈朋飞他们几个人这一次文革中的无妄之灾,又是因为去石柱峰看风景,被人密报成反革命活动。
石柱峰是我故乡的祖山,本书开头的序言里,我曾经多次写到站在大地坪老屋里远眺石柱峰的景象。倘若祖山有灵,看到这种接二连三上演的悲剧和闹剧,不知会作何感想。
210、偷三只鸡走了
我获得社会上的一些秘密消息,是靠做耳朵生意的,当然算是马路消息了。因为多在做缝纫和出工的时候,也可称市主消息和田园消息。这种做耳朵生意的小道消息,当然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芝麻蒜皮。
住在大地坪老屋东横厅的成生是中共党员(社教时入党)贫农成分,历任生产队长。因与他是童年时代的玩伴,又因都喜爱木工。朝夕相见,往来密切,算是合得来的人。明摆着我是五类分子,他却不怎么介意。有时把按照政治路线不该对我说的消息也透露出来。一天,他在开完公社党员大会回来后,便轻声对我说:林彪死了,坐飞机摔死的。这个消息只下达到党内,还没有向社员宣布。
我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感到特别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十大元帅中排名“探花”(第三)的元帅,不远前还是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号称为副统帅,定为大宝的接班人。不管是亲密的战友还是亲密的朋友,他步入了接近登峰造极的地位,为什么要坐着三叉戟飞离祖国摔死在国外的地盘上呢?到底是“君不仁臣逃国外”还是“臣不忠叛逃国外”呢?我觉得这是难以说清的国家级事件。
这个消息当夜我只跟妻子说了,她也不敢相信最最最亲密的战友会这样突然外逃。直到后来这消息从秘密到公开,从党内到党外广为传开了。这是十一月初才向群众传达林彪事件的时候,距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已是五十多天了。到12月才下达三批林氏集团的材料,批判清查,肃清影响。1972年4月,浏阳联系文革再次批林,8月开展批林整风。1973年7月12日全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用大寨精神学大寨,把浏阳建成大寨县。
一般社员听了大会传达,都知道林彪坐飞机逃走摔死了。但弄清是坐第256号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草原的就不多。很多老百姓去开会只是为了赚工分,不考虑听清楚和听懂大会传达的中心问题。有的说林彪坐三只飞机走了,有的说林彪坐三叉机走了。越传越走样,邻人有个口齿不很清楚的中年男子,就把林彪事件说成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还炆汤芋喝了。这样就把三叉戟说成三只鸡,把温都尔汗说成“炆汤芋喝”了。因为他土改时当过民兵班长,他把民兵发音为“门崩”。每次他来了,就有人喊:门崩(民兵)班长来了,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这又把民兵班长和林彪搅合在一起了,硬要取笑别人,惹得大家拍手打个“呵嗬”才收场的。
几十年过去了,门崩班长也早已辞世。可是“林彪逃走的时候还偷了三只鸡”的笑话,还是偶尔能够听到。
据说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各个战役中,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无论历史最终如何定论,林元帅若泉下有知,听到他死后被人当做“偷三只鸡炆汤芋喝了”的小毛贼,想必一定会啼笑皆非。
211、半夜焚书
自《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抓黑帮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经处理了的事情再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的运动已由高层到基层,由城市到农村,纷纷烈烈深入到了每个角落。
一个阴沉的晚上,宝乔祠的上厅里召开大会。主题是批判三家村,着重是批判邓拓和抓小邓拓。会议由龙伏公社副书记宋继龙主持,他说混进党内、政府机关、军队里及文化界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叫黑帮,就要清洗,就要批判。三家村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黑帮,这三个人串联在一起就叫三家村。大黑帮已抓出来了,可是各地还有小邓拓,要把三家村散播的余毒肃清。就要发动群众检举暗藏的小邓拓。
他说邓拓写了一本书叫《燕山夜话》,就是邓拓把夜里在燕山讲的话写出一本书。书里都是通过故事来达到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如果私藏这本书不坦白上交政府的,如果有宣传《燕山夜话》内容的,都是邓拓的徒子徒孙,都是与邓拓一鼻孔出气的小邓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
这个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的运动,好像只是一个走过场运动。因为在这偏僻的农村,知道邓拓其人的很少,读过《燕山夜话》的就寥若星辰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本书。
与会者都感到这三个人物的名字很陌生,说从来冇听见过这样古怪的名字。有的说邓拓夜里在燕山讲话的那本书也从未听过和见过,好像三家村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以夜话为书名的古今有之,如《围炉夜话》之类。前文满盈阿公和六老倌常在大地坪老屋纳凉时讲故事扯谈等就可说“乘凉夜话”。
只有坐在角落里的我和皆遂就有点触电。因为我俩对这三个人物略有了解,特别是皆遂已不知从哪里买了本《燕山夜话》回来,我们都翻看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俩虽坐在那里听会,但心里都在打着战鼓,回家后就商讨如何处置这本惹祸的“夜话”。皆遂认为这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书,都是一些有启发性的带知识性的内容,例如那篇写由一个蛋孵出的鸡长大后生下蛋,再孵鸡再生蛋,最后可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养鸡场,也是勤劳致富的生财之道呀!那一篇“姜够本”就是告诉你做不亏本只盈利的种植业呀!“
“你太天真了”我驳斥他:“硬要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戴上新资产阶级帽子也是容易的。因为你剥削母鸡下了蛋,又剥削它孵鸡。接着你可随意吃母鸡下的蛋和它孵的小鸡。当新母鸡接替下蛋孵鸡时,你又把老母鸡宰了。到后来你当上养鸡场的场长时,你又剥削请来的饲养员。如果当初把那个鸡蛋吃下了,就不会惹出后面的祸来。再说种姜不亏本,子姜不比老姜辣,也是有文章可做的。只有把”夜话“烧成灰,就发不出祸根芽了!”
他也觉得坦白上交,说不定反倒会惹出一个“小邓拓”来。于是同意烧掉。于是我们就半夜焚书,把这本《燕山夜话》变成了灰蝴蝶。
是夜,两人才睡了个惊魂稍定的放心觉。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