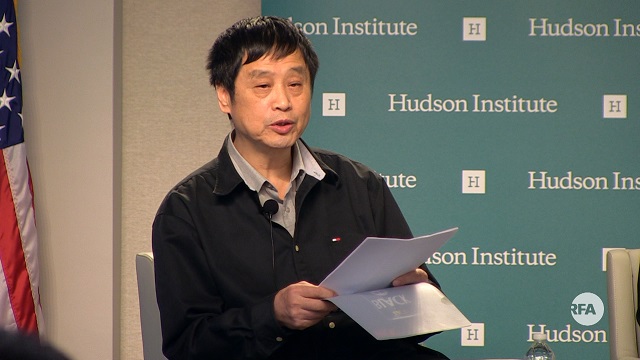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自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依次对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作学术访问。台湾的大地震并未使我惊恐,但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脆弱,人在无助的境况下的绝望,仍使我感慨万千。当大陆因为异乎异常的事件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度和激动时,我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埋首苦读,我未分享同仇敌忾,但决非冷眼旁观。我认真思考,知识分子在重大事变发生时,如何尽自己的职责。
对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纪之交,我并不特别看重。但也许是出于碰巧,我这一年的著述多与历史有关。《蓦然回首》是我对于1966年至1976年10年经历的一部回忆录,《形形色色的造反》则是对同一历史时段的学术研究和理性分析。收入“第三代学人自选集”的一书叫做《告别20世纪》,而另一部文稿则以《直面历史》为书名。历史感应该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素质,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并不特别重要——尤其在中国。
学者面对有形的外部力量,往往是不堪一击,但有一种内在精神,却无比强韧,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孕育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自学术生涯开始,古希腊晚期的一个事件、一种形象,一直是激励我的源泉。
当罗马军队在公元前212年攻破叙拉古城时,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才的发明家阿基米德正面对沙地上的一幅数学图形凝神沉思。当罗马士兵将剑高举时,他只是安详地说:“别踩坏了我的图形!”学者并不意味着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万一不幸处于苦难的时代、悲惨的国度,万一偶发事件突然降临,他会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那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传统学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除少数自不量力、一厢情愿者想“为帝王师”外,多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书中自有颜如玉。”时至今日放眼望去,情况仍基本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志士仁人,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如果“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并不高(当然一点也不低)的标准不能成为共识,那么学术的发达是没有希望的。
学者似乎天然具有理性的禀赋与冷静的气质,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情况其实不然。罗素在回顾自己一战的经历时,曾经痛心地指出,学人们是多么地短视、盲信、跟风和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剑桥大学,学术精英云集,面临日益逼近的危机,人们立场超脱、见识高远、思想睿智。罗素发起签名运动,许多教授和同事起而响应,坚决主张英国应保持中立,不卷入不正义之战。但战争刚一爆发,随着政府掀起的战争歇斯底里和民众的狂热,大多数签名者马上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被抛到九霄云外,批评政府的人变成政府的战争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罗素对此惊讶不已,但对于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豫,他说:“当战争来临之际,我觉得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责任是抗议,不管抗议是否有效。我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进去。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罗素不是基督教,他所说的上帝的声音,其实发自他的良心。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现在不是想指斥那些弃学经商,在下海的浪潮中捞一把的人,也不是想揭露那些在化公为私、权钱交易中分一杯羹的人。9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心理的急剧动荡,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难于定位,守望良知变成一个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坚持道义立场远为困难的事。良知需要智慧支撑。
高度指令性、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已到穷途末路,超越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乌托邦早已失败,中国在十分不情愿和反复中开始向市场化转型。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贪婪和无耻急剧膨胀,血汗与泪水的控诉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经济交换方式、人际关系和思维习惯也缓慢地形成。现实中的丑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但问题出在哪里?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还是斯大林模式改头换面,权力仍然是社会生活的腐蚀剂?知识分子既要谴责批判,又要清理历史,如果责任或罪过能分主次的话,我们是盯住专制权力,还是经济资本?
当知识界意识到社会公正已成为今日中国之重要问题时,问题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许多人的态度是:在二者中只能择一。
我拒绝这样的立场,我决不认为不公正的根源仅仅是市场经济。我的经验告诉我,在60和70年代,当一切自发的经济活动萌芽都被扼杀时,根本谈不上公正,虽然在表面上,大家都是同样地一贫如洗。我当然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正问题,而且很严重,但我决不认为当今发达社会中的公正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学者,我们应当追问和研究: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公正和正义?
我不满足于业余水平的回答,于是在两三年前转入政治哲学领域。我发现,公正问题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许多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如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最学说令人瞩目,其观点引起广泛研究和争论,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正问题(或者说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有独创性贡献。这些大师的著述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鼓励,罗尔斯的恢宏气度和建构能力,诺齐克的雄辩与尖锐,德沃金的精思巧辩和平衡术,常常使我掩卷叹服,同时也产生投入思想竞技场的跃跃欲试的心理。我和他们一样,把个人自由放在思想辞典的首页,同时力求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寻求平衡,和所有的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不能对不幸者,社会上弱势人群的呼号充耳不闻。当然,我也充分认识到,自由与平等的悖论,是人类历史上许多世纪积累下来的难题,任何推动其解决的努力和步骤,都有莫大的意义。
国际学术前沿话题和对自身社会中尖锐、迫切的问题碰巧有极大的相关性,这自然使我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顾。但是,我仍有这样的一份清醒,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可能这么便宜地和国际学术接轨。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粗鄙性”,沉缅于当代学术话语可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我们决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头脑搅昏,自欺欺人。打个比喻说,西方的问题有点像工人和雇主订合同时,争论劳动力和资本的份额回报,以何种比例为公正,而中国的问题是,当小偷和强盗以非法手段窃据财产时,有没有警察。形势甚至可能严峻到这个地步,当警察也开始偷和抢时,该怎么办?当然,比喻总有局限性,不免不恰当。社会公正问题,中西社会毕竟有共通之外,尤其从学理上考虑,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的思考和研究将导致什么结论,我只知道,从2000年起,我必须更加努力。
爱思想2004-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