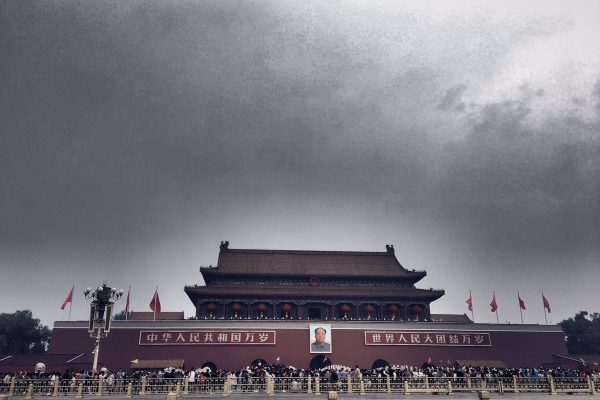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黎国智,在最近一期“中国改革报”发表文章,大胆批评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党大于法”现象,呼吁改变长期形成的执政党领导权和国家统治权混合、党高于一切的情况,立刻解决“以法治国”和“以党治国”的矛盾。这把自文革结束、提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口号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重新又摆到了我们面前,促使我们再次反省: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中共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法律制度,究竟有何发展、变化?建设中国民主与法制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一、中国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黎国智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党大于法”的体制里,许多高干的犯法并非由法律来审判,而只是采用党纪处分。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象。黎教授以极大的勇气道出了——人人都心里明白但都嘴上不说的——中国社会目前的现状。最近,海内外读者所关注的陈希同案久拖不判和周北方案重罪轻判,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通过揭示这种社会现象的矛盾本质,黎教授代表了中国未泯的良知。
民主与法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中国,这个口号曾经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认为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的手段,说它本质上虚伪的,从而受到批判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在屏弃这一口号的过程中,渐渐蜕变为一个拥有无限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眼里,法律只是用来镇压反对者和统治老百姓的,而自己是绝不能被法律束缚手脚的,所以在一个号称拥有儒家“民本”传统的国度里,盛行的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主义”和“官本位”的人治,以致于中共领导人自己都已经意识到并曾公开地告诉人民,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级,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提出了要建设民主与法制,也重新挂起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而且修改后的宪法也在第五条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记得当时负责政法工作的中共元老彭真在作立法解释时,特别从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执政。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受到既得利益的束缚,一直未能顺应民意和潮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即无法完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现代执政党的本质转变。在回答到底“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时,彭真就玩弄起文字游戏来了,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宪法之类的托词,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结果现实就成了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滥用、曲解、践踏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实际上的“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以权谋私、开后门的风气,曼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结党营私也越来越公开化,腐败成了无法医治的癌症,中共一边叫反腐败,一边却在利用特权搞腐败,整个社会变的腐败越反越严重!
无论是邓小平、彭真在八三年发动的“严打”,还是前不久江泽民所搞的“严打”,这种用政治运动形式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共对普通刑事犯罪和异议人士,采用“从重从快”的非常手段打击之,甚至像王丹、魏京生等没有罪的也要判处重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犯罪,却采取从轻发落甚至网开一面的特殊做法,实际上就是“从轻从慢”,像周北方案在被捕一年八个月之后才审判,首先就破坏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而在实体部分,中共不但掩盖了许多重要的犯罪事实——因为政治需要而重组了他的起诉罪行,而且从已公布的罪行来看,判决结果成了对中国法律的无情朝弄,中国刑罚中的“死缓”,也被老百姓讽刺为“死免”。
通常,处理一个即使罪证确凿的领导干部,也首先要交由中共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而后再由上级党委和政法委员会的审批,在最后处理时,党员干部的级别、过去对革命所作的贡献,都可以被用来折抵刑期……,所以中共党员干部,不但在诉讼程序上而且在法律实体上都享有事实上的特权。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老百姓犯罪抓来就判,在风头上还要“从重从快”,党员干部犯罪,他们的特殊身分就至少可以挡三把,第一把是撤销党内外职务,第二把是开除党籍,第三把是将功抵罪——被象征性的判刑。
正是中共党员干部的这种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制。黎国智教授分析,在建国之初,中共引进的斯大林专政模式,把共产党的独占领导,理解为党政不分,党权高于一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客观上为一些人崇尚人治、破坏法制制造和提供了“依据”。
邓小平、江泽民口头上虽然讲要“依法治国”,而实际上他们却陷在毛泽东“以党治国”的政治机制中难以自拔。从黎教授的观点来看,依法治国,具体的说,要求宪法具有极大的权威,也就是“法律至上”、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应做深刻反思、反映民心、党心的理性选择:一、要从理论上对党的领导权作出科学界定,严格区分党的领导权与国家统治权;二、从制度上创造适合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的、实现“依法治国”的领导体制;三、在实践中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条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
不过,据报道,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解释,“以党领政”传统是经过多次重大事件考验形成的,眼下又面临十五大人事换班的敏感阶段,在一切要求“稳定”的背景下,绝不允许有人挑战“以党治国”的原则,因此不可能考虑接受黎国智的建议进行这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黎教授的建言和毛泽东的机制当中,江泽民显然选择了后者。
二、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耻辱
中国共产党虽然大权独揽,它在大陆建立了当今世界上最严密的集权专制,但是它的确也搞出了自己的“特色”——“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标签。虽然首届政协时,定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但在毛泽东大独裁专制的淫威之下,尤其是在反右运动当中,当年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其他几个党派社团,像民盟、民革、致公党、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台盟、民主建国会等领袖,陷入毛的“阳谋”,被当成“大右派”打倒在地,“民主党派”也就名存实亡。
经过几番改造,脱胎换骨,这些贴着“民主党派”标签的政治团体,对毛泽东和中共俯首称臣,成为中南海欺世盗名的花瓶。表面上看这八个党是互相独立的,但实际上全部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而在中共的行政编制当中,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都享受正部级待遇,其负责人也兼任人大或政协的副职,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具备双重身分的党员,即他们同时还是秘密或公开的中共党员。
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在政治纲领上要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且它的组织经费开支来源于共产党控制的国库、领导人的选拔和机构的设置,也完全由中共一手操纵。即便是花瓶摆设,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严密的控制,比如参加“民革”的对象,往往必须是国民党的后代;参加“民盟”则要求是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而且发展人数也必须遵照中共统战部门下达的指标,目前,这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十万左右,跟拥有五千多万党员的中共,在人数上不能同日而语;……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耻辱。
据来自北京的消息报道,自何鲁丽代替被武警凶杀的李沛瑶,出任民革中央主席;最近由原北大校长丁石孙,接替费晓通担任民盟主席以来,事实上拉开了中国大陆的八个所谓民主党派更换领导人的序幕,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之前,各民主党派的现任主席或主任委员,都将离任。中共中央要求,民主党派也要适当体现年轻化,并建议下一届民主党派的中央主席,年龄一般不要超过八十岁,副主席不要超过七十五岁,从现任这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年龄来看,除“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以及前不久才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外,其余都已过了年龄界限。据悉,目前超过这个年龄界限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已经向各自党派提出了辞呈。消息人士透露,即将卸任的还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雷洁琼、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卢嘉锡、中国致公党的董寅初、九三学社的吴阶平。有报道说,八十六岁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也将提出辞呈,由现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冯梯云接替。民主促进会将由楚庄接替雷洁琼、致公党由杨纪珂接替董寅初、九三学社则由安振东接替吴阶平。
根据中共统战部门的安排,尽管“民主党派”已经或即将在最近更替领导人,但是新产生的领导人不会在明年“两会”上接替其前任在人大和政协的职务,既“民主党派”领袖所担任的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职务,则要继续到一九九八年任期届满为止才作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把“民主党派”领导人安排在政府机构担任象征性职务,重新成为中共的一项统战政策,就像人大政协那样,政府一些部门的副职也选拔一个非共产党(往往是“民主党派”的)人士来担任。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空间极其有限,一些投机者便找上了这条捷径,采取了“曲线当官”的策略,既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再以“民主党派”的身分作为统战对象而进入中共体制内当官,这样他们往往要比同等资历的中共党员晋升得更快一些。由此,这些民主党派中的阿谀逢迎之士,便有点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地把自己说成是“参政党”。其实,中共宪法虽然写了“多党合作”的统战原则,但是只有领导,根本不存在合作,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拥有多党成分的“联合政府”了。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目前大陆“民主党派”,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既得利益的共同体,而中共通过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渗透、赎买等方法,垄断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资源,驾驭着中国的政治机器,强化了“以党治国”的机制,同时也严重腐蚀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最不幸的悲哀!
三、“以党治国”无法照搬到九七后的香港
无独有偶,最近香港在推选行政长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舆论焦点是:九七以后共产党在香港是否要登记,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公开地进行活动。
对一个在法制社会生活的人来讲,答案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尽管作为一个没有登记过的非法政党,中共在香港事实上已经活动到现在了,问题的关键是,香港这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法制社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交还到不讲法制的中共手里,中共到底是实行政治改革以遵守法制、真像自己所承诺的维护香港稳定;还是僵化的坚守原有的政治机制、我行我素以破坏法制来突显自己的权威、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
九七后中共在香港是否登记,不仅将检验中共推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诚意,而且对中共自身和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如果它登记了,当然说明他还愿意遵守香港法律,他在香港的活动受到香港法律的管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现在香港已经有许多登记了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党派社团,规范他们的行为的法律是否与规范中共的是一致的?或有一样的效力?也就是在香港的法律面前,中共与其他的政党社团是否应该平等?与此同理,台湾的国民党也在香港活动多年,它是否可以依照香港法律登记以后公开活动呢?
“以党治国”,这一共产党在大陆“行之有效”的政治机制,明年七月一日以后,将在香港受到空前的挑战,很显然,照搬大陆的做法,在香港搞“以党治港”肯定是行不通的了,香港现行法制的存废,关系到整个香港社会的稳定繁荣。从中共现行的做法分析,它已经明白照搬大陆“以党治国”的办法寸步难行,但是又深知“遵纪守法”将会成为一个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故不甘心就此老老实实地遵守香港法律,授港人以“柄”,而原有的旧政治机制的惯性还在发生作用,所以它的宣言和行为之间一直自相矛盾。
香港舆论无疑是“将”了中南海一“军”。当然,挑战同时也是转机,中共如果面对这一挑战,真正的洗心革面,坚定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不但香港前途有希望,中国大陆的人民当然也将受益无穷。
香港与大陆的联系,随着九七的到来也越来越密切了,同样香港人的观念、香港舆论的焦点,也对中国大陆的人民越来越富有启发性。像香港人公开质疑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尽管大陆人私下也有这些讨论,但公开的拿到媒体上讨论似乎还没有见到。一个大陆的人,是否也可以公开提出类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是否也需要依法向中国大陆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呢?如果没有依法登记注册,是否就意味着中共不但从本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缺少了合法性?不过,中国大陆没有人公开提这样的问题,也许中共根本就不让你提这样的问题、即还不具备谈论这些问题的环境条件,或者是大多数人们根本就没有想也不敢提这样的问题,这本身不是就很说明问题吗!
中南海的智囊目前正加紧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研究,而这一课题也将成为明年中共十五大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包括分配领域的贫富不均、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题制上的差异、东西部、农村和城市在发展上的失衡、这些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正在全面的激化当中,严重的威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和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江泽民就此发出指示,与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不同,现在要维持这个基本矛盾,使其内部两方面取得平衡,基本矛盾是社会的支撑物,像腐败问题,也是阶级斗争的一极,是基本矛盾对社会发难,但是我们不能发动人民来打倒官僚,维持矛盾平衡的手段,是加强政治控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参与研究的人员建议,今后五年内,中国将出现大规模新无产阶级与旧无产阶级的斗争,新无产阶级是指不能仅靠土地为生、而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民,政府要在今年年底开始,取消企业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界限,协助进城农民迅速成为新兴的工人阶级。以专政手段控制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阶级利益冲突。
实际上,江泽民和他的智囊们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本质上乃是日益专制腐败的中国共产党,与在一个日益开放社会中不断觉醒并积极追求民主法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或者讲是政治上的集权专制与经济上的开放与发展的矛盾。
“党大”还是“法大”,即“以法治国”,还是“以党治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也许还要伴随整个中共执政及其存亡的过程,和整个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讲,主要由造反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要从一个革命党,完成到现代执政党的转变,其根本的标志就是:看它能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能否在这个社会建立起反映公平正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