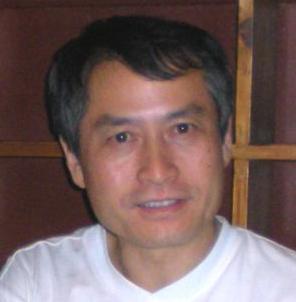2003年5月20日下午3点,三个穿便服的国安人员通过我的单位党委,将我骗出办公室。亮明身份后,他们告诫我不可声张,将我押上一辆挂普通牌照的桑塔纳轿车,送进了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一进审讯室,他们叫我在拘传令上签字,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然后他们搜光了我身上的物品。当天连续审讯我到深夜12点过。临过12小时前,他们拿出一张拘留证,我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拘留。具体的犯罪行为,一是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马克思理论的终结》,并将它邮寄到海外和在贵阳街头售卖、散发。这本书近十万字。二是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名为《逐马檄文》,另一篇名为《第三封建》。两篇文章各有一万余字,也因邮寄散发被他们截获而成了我的“罪行”。
5月21日,他们抄了我的家,收走了我的全部文稿、信件,以及7本日记和笔记,52张磁盘,492本书和电脑、打字机、收音机,我的全部存款和现金也被收走。在被收走的文稿中,一篇还未打印完的《共产党应该共产》一文和一篇英国BBC电台采纳播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一文,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它们加重了我的”罪”。
下午(不知道几点),他们将我押上车,交给我几件我的家人送来的衣服和被子。两部挂贵A牌照的车将我押送到了二戈寨贵阳铁路局第二看守所。在这里,他们对我施加了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
他们先是连续一整天不给我饭吃;进到这里就被一个断了一只手的警卫将我的外衣裤全部脱光扔在地上。这断手用两只脏脚踩在我的衣裤上(此时外面下着雨,他脚上粘满了泥污),用一把大号夹钳把衣服、裤子上的大小纽扣和饰物全部砸碎,衣、裤也被砸、扯得尽是破洞和口子。又将裤腰和裤裆撕破,皮带抽走,皮鞋扯破,荷包中的药物(因我正感冒,审讯时恩准我留在身上的)扔掉。然后将堆在地上的衣服踢过来叫我穿上。接着又把我的被子甩在地上,也用脚踩在上面,象是在找什么东西。完后喝令我捡起。我穿着被撕、踩、敲、砸得又脏又破又皱的衣裤,由另一名警卫押着往外走。一路上,我一手抱着肮脏的被子和衣物,一手提着破裤子,狼狈不堪。幸得搜查室离监房不远,要不我一身和带来的衣、被会全被雨水淋透。
我被关进9 号监房,这里连我共关押了12名人犯,他们中有偷、扒、贩毒、诈骗的惯犯,和因为打群架致人伤残的人犯。在我被关押期间,这个看守所内,年龄最大的有65岁,最小的仅14岁。在与我同监的人中,有4人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都因生活穷困被迫走上偷、扒之道。
在这儿关押时间最长的有7、8个月之久,关5、6个月的比比皆是。铁二看善于在犯人身上榨油,我在这里被关了20天,就被强迫交纳300元的关押费。关的犯人越多,时间越长,收取的关押费也越多。这可是纳粹集中营都未能想到的榨取犯人的方法。而且犯人一进来身上的钱、物要全部被搜光,他们也提供方便让犯人通知家属送钱进来。看守所有香烟、日用品、小炒、早餐售卖,但价格比外面至少贵5倍以上。尽管监规上明文规定“监内不准吸烟”,但这一条例外,因为香烟的利润高,销量大。人犯交给他们保管的钱也是个良心帐,出狱结账时还你多少就是多少,到底是怎样花掉的只有他们清楚,本人是不得而知的。我因为进来时交了435元钱给看守所,许诺要请同监房的人犯好好吃一吨,颇得大家另眼相看,不但免了杀威棍(铁二看这里叫:表演节目),还能得睡在木踏板上,要不,新来的要叫睡在地上。
监房里没有床也没有被子,房间包括一个大便坑共约14个平方,离地大约20cm高的一块木踏板占去了约8个平方,经牢头指定的人才能睡在上面,其余的睡在地上。睡在木踏板上的也只能侧着身子躺下。铁二看有14间这样的监房,每个监房长年关押犯人10名以上。饭食每吨都是切成两半的土豆,不去皮,几乎无油。也许只粗略淘洗就下的锅,土豆坑凹处还有泥沙,吃到碗底的沙土和黑乳色的汤也证明了这一点。饭中经常吃到沙子,而且时常有酸霉味。饮水更不卫生,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五颜六色的油污,齿唇未沾,一股怪味先已让人恶心。
这里没有洗澡和放风活动时间,只是在牢房后有一个大约5m2的天井,上面用水泥板和钢网盖住,能见到一线线天光,他们仅以此当放风。尽管牢房墙上写有看报学习时间,但这里是不允许有这些东西的,一旦发现就糟责打。牢房的秩序全权交给牢头,他浑然是一个次奴隶主。其他人犯的吃、喝、拉、撒都要向他请示批准,他的吃、喝、拉、撒和起、卧、洗、漱都由别的犯人侍侯。
在关押期间,国安厅提审时,我提出过政治犯问题,和我国是联合国成员国,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和遵守我国在国际上签订的有关保护人权的条约,要求他们改善全体人犯的待遇,改善饮食卫生条件,至少两周让犯人洗一次澡。他们对此明确回答我:关于政治犯问题,我国不承认什么政治犯,我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只是与杀人放火的行为不同,但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刑事犯罪行为。至于我国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和什么国际条约,在这里提出来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明白他们说的”在这里”是指在监狱这里还是指在中国这里。
即有如此的政策心态,可想而知他们会如何凶残地对待人犯。我被提审时,他们想饿我一顿就饿我一顿,耐不住饥饿要求他们给点吃的,反遭到他们的讥讽。一次在审讯后送我回牢房时,一名国安和一名狱警押着我往牢房走。我当时一点没有在意这反常的现象(以往每次送我回牢房时都是仅由一名狱警押送,这次却多了一名国安)。进牢房要先经过关狼狗的铁笼,像出牢房也必须先经过这一关一样。
像往常一样,临近牢房时,狼狗开始吼叫。我每次经过它时都紧贴着墙边走,生怕这恶狗扑了出来,它每次在我经过时都狂叫着扑得铁笼哐啷作响。这一次我的灾难来临了,狱警走近铁笼打开了它的门,这畜生冲出它的牢笼就吼叫着直朝我扑了过来。安特和狱警见状立即都转身走开,一下没了踪影。我看着扑过来的恶狗,知道叫喊求救无济于事。
我小时候有过被恶狗追咬的经历,知道逃跑只会被撕咬得更惨。而且也无处可逃。我只得恐惧地站定。瞬间,恶狗就扑到了我身边。它张开大口在离我几步远处一跃扑了过来,我本能地抬起双手护住脸部,可这条最凶,至少同监室的犯人个个都知道最爱咬人的狼狗扑到我身上时只用它的爪子划过了我的衣裤,狗嘴却没有咬下来。但它似乎不甘心,凶恶之状不减,狂叫着反复扑跳。我即有第一次攻击没被咬的幸运,就不会再动摇,虽然恐惧依旧,心怦怦直跳,但却镇定了许多。
恶狗狂叫扑跳了一阵,只碰了几下我的裤脚,转身跑开了。狱警此时走过来,假惺惺地问:“被咬了没有?”我冷冷地回答:“没有。”狱警上下看了我一下,疑惑地说:“……那你运气还好。”
尽管在铁二看的每个监房墙上张贴有在押人员的各项权利,其中就有在押人员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到了这里,在押的所谓犯罪嫌疑人们是不被当人看待的。狱警因正常事务询问在押人员都是喝令其蹲下,抱起头。此时人犯只能两手抱着后脑蹲在地上,看着狱警的皮鞋回答问题。
这里不许看书、报,不许唱歌、下棋,任何形式的娱乐均不允许,一经发现这类事,就要被罚跪挨打。
我被关进来的第二天,正遇给犯人检查身体,每个监房都被提出几名犯人,我也在其中。所谓检查身体,不过是一名穿白大挂的人,戴着一双永不更换的一次性塑料手套在每个犯人的身上摸几下。我担心,如果这些犯人中有谁得了性病或皮肤病,那大家都会被传染。
提出来的犯人被喝令蹲在地上等待检查,周围有十来名狱警。他们服饰笔挺,一个个满脸凶相,一脸杀气。有敢出声动弹者,一声呵斥,惊鬼动神。在押者们一个个蹲在地上,不敢抬头,不敢支声。这情景,使我想起书上描述的南京大屠杀中,日本鬼子对抓来的中国军民如何处置的情景,也想起纳粹集中营给犹太人检查身体时的情景。我此时想,大概人都一样,一旦得势,他人的性命、健康都不算回事,何况什么尊严、人格。这也是人畏死的缘故,一旦成了他人囚徒,就只得低声下气,忍辱乞命。国家没有民主,社会没有公理,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就是奴役、屠杀的机器。
我在狱中20来天,感冒、腹泻一直困扰着我,多次呼请要药,大都无果。6月10日下午,经家人多方努力,我被取保候审一年放出看守所。回家后,我因身体极度虚弱住进了医院。
申有连——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3年因自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结》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拘捕,家被搜查,所有书籍和手稿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