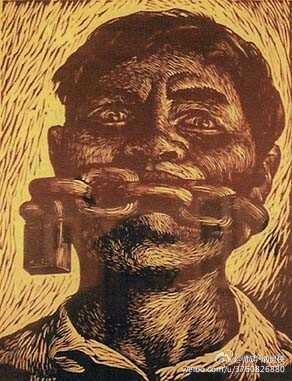 2015年开年受到的第一桩刺激在上海。前不久参加叶开博士创立的“老虎文学奖”颁奖活动,和一群教授作家吃饭的时候,说到我们学生时代的种种叛逆,我忽然发出感慨说,北京大学的孩子们怎么回事?像孔庆东这样一个公然为文革张目叫好的所谓教授,换做我,早就不知道给他扔了多少只臭拖鞋了!立即就受到大家的嘲笑说,师涛你错了,你太落伍了!孔庆东在北大可受欢迎呢!一间两百个人的教室,孔庆东去开讲座,起码能挤进四百人,你要是敢对孔教授不敬,学生们说不定就把你哥撕的吃了。你以为呢!
2015年开年受到的第一桩刺激在上海。前不久参加叶开博士创立的“老虎文学奖”颁奖活动,和一群教授作家吃饭的时候,说到我们学生时代的种种叛逆,我忽然发出感慨说,北京大学的孩子们怎么回事?像孔庆东这样一个公然为文革张目叫好的所谓教授,换做我,早就不知道给他扔了多少只臭拖鞋了!立即就受到大家的嘲笑说,师涛你错了,你太落伍了!孔庆东在北大可受欢迎呢!一间两百个人的教室,孔庆东去开讲座,起码能挤进四百人,你要是敢对孔教授不敬,学生们说不定就把你哥撕的吃了。你以为呢!
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喜欢用粗鄙的语言关照问候孔庆东胡锡进周小平之流,原因是多年以前读余杰的作品以及和他本人交流,他最大的焦虑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宣传体制下,中国会不会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通过这几年的人生实践,越来越多的人深切地感受到,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的危险相当大,就看达摩克利斯之剑究竟会落在谁的头上。
人生短暂几十个春秋,回首我的大半生,几乎就是在大大小小各种刺激中度过来的。举一些表象的例子:有一天忽然发现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事迹竟然是假的;有一天忽然读到笑蜀先生编辑的《历史的先声》,发现几十年前差点就实现了现在无数人在苦苦奋斗的理想;响应国家有关教育产业化的号召,积极为民办院校鼓与呼,几年后竟然有高官出来公然否定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说法,好像那就是哪个神经病王八蛋在大街上撒了个酒疯。在监狱里的经历就不能叫做刺激,只能说是恐怖。我永远不会忘记,几个警察把囚犯拷在铁笼子上,几根电警棍在他身上刺啦刺啦作响,整个人就像是一棵圣诞树发出耀眼的电火花。那些年的惨叫声使我深受刺激,至今都不愿意靠近杀猪宰羊的屠宰场。
有许多好心人都劝我忘记仇恨,好好生活。我回答说,我没有仇恨,我也恨不起来。不论高官还是囚犯,不论警察还是小偷,当我们平等地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能意识到,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为生活而奔波的平凡之人,何必要残忍地手足相残呢?尤其是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观点不同,方法不同,言论不同,难道非要使用专政的高压、刑事的手段甚至旧社会的伎俩来达到刺激一个人以便让他改变的目的吗?将近九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后,原本以为一切会好一点的,乐观一点的,但2014年多名律师和文化界人士被抓捕的事件确实让我感到极度震惊、极度恐慌、极度刺激。
2014年反腐败取得丰硕的成绩,我也是真心拥护的,也知道习总和王总非常不易。但是一想到媒体沦落到只配鞭尸的角色,人大机构安静的像清闲的看客,各级干部畏缩的只顾自保,就感到世事的艰难和个人的无奈。尤其想到,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官们,在位时极力否定普世价值观,极力打压敢说话的媒体人和死磕派律师,到头来轮到他们自己倒霉,却没有机会为自己发声,只能在劳改队和我的那些牢友们发发牢骚。我在监狱里和几十位落马官员相处,众人好奇的目光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刺激。
十几年前,老师课堂上讲资本主义的虚伪与残忍,举例说法国有条高速公路,一位老太太被车撞死之后,竟然有十几辆车相继从她尸体上辗过去,导致我积极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去解放全人类。当我们也有了高速公路后,我才明白,在那样的速度下车辆是不能够紧急刹车的,否则会有更大的灾难。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彻底反思我们每天看到的各种官方新闻,质疑各种专家的说辞,梳理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传说。在一次次的刺激中跌跌撞撞地虚度了半生的光阴。上个世纪末,我认识了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时的秘书林牧先生。去他家里拜访时,林老对我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活到七十岁了,才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开始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因此,年龄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活着,还是要接受更多的刺激。最近网络上关于2015年的各种预测讨论得很热烈,我想,该来的,总会要来的。官场上的起起落落,文字狱的出出进进,钱包里的来来往往,殡仪馆的哭哭闹闹,文坛小丑们的吹拉弹唱,很快也会变成圣诞节的烟花,为下一次的狂欢拉开序幕。
(2015-1-18,呼笑山庄)
来源:作者微博

孔庆东在北大受欢迎是很有可能的。几年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乌有之乡的人在高校里就影响很深了。
“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轮回。”——这是很让人害怕的事,因为无力改变,一步一步的倒退。
全球化的今天,转移财产变得很容易。最终受伤的还是吾国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