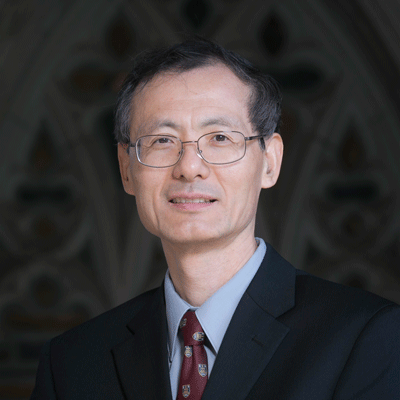鲁迅在 1907 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里哀叹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满清败亡将至,鲁迅期盼精神战士在中国出现,像《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唤醒国人,逃脱灭顶之灾。
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曾为其同胞的道德沦落、为统治者的 “恶行” 而恸哭。上帝差遣他到王宮,痛斥君王用不义不公的手段建造楼房,“流无辜人的血,施行欺压和迫害”。他同时诘责 “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预言 “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利米书 8:8 ;22:5、13、17)。
鲁迅自己也发出 “铁屋子” 里的呐喊——尽管先知的呐喊只能为 “绝无窗户万难破毀” 之铁屋里即将 “从昏睡而入死灭” 者徒增 “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苦”。
从毛泽东开始的专制极权,不是将铁屋子改建为敞开门窗的现代民主社会,而是加固铁屋子,并将呐喊者消声。
于是在中共治下,先知的命运都有并不惊人的相似之处。反右时期毛泽东坦言,鲁迅若还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上世纪六十年代,林昭就是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里带着反铐,刺破手指,以鲜血明志:“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林昭囚室血书的呐喊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至今还在神州回荡。当代中国,牢狱也是刘晓波和无数捍卫自由与人权者的归宿。正如王剑虹《编者的话》所言,张展穿越自由之路 “毫无悬念地通向了监狱”。
先知异于哲人和革命者。沙发椅上的哲人,对着窗外的萧索沉思 ;革命者以暴易暴,用仇恨和血腥编造解放人类、铲除不公的太平世界美梦。
先知面对朝堂和市井,呼唤未泯的良知与理性,告诫不论是君王还是草民回归真理与信仰、道义与公正。先知是无畏的践行者,被爱而非恨所驱使。
先知是孤独的。上帝告诉耶利米:“君王、官长、祭司和人民都要攻击你。”(耶利米书 1:18)祭司赞颂君王的功德、智慧 ;先知直言他的罪恶、愚蠢。当代中国的统治者将党国祭司的袍服赐给了御用文人,也赐给了官办教会,所以教会只能放逐先知。民间基督教无缘进入公共领域,社会良心退化,却将对世间不公的冷漠圣化为属灵与虔诚。于是先知成为了众矢之的。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武汉被封。是先知般的敏锐和悲悯,让张展 “觉得这座城市受伤了”。她逆行至封城武汉,担负公民记者的责任去披露真相,援助惊恐受困的人们。“同胞的创伤使我心碎 ;我悲痛万分,惊忧不已……为什么我的同胞没得到医治呢?”(耶利米书 8:21-22)那是耶利米的哀歌。驱使耶利米的哀怜之心,同样驱使着张展 ;等候耶利米的枷锁和牢房,同样等候着张展。
张展的道德勇气有目共睹,而她的文字却并不掩饰恐怖统治投在她内心的阴影 : “这种恐怖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我唯一的念想就是进监狱,好结束自己的恐怖感。” 但她同时要 “和恐惧反复地较量,直到跨越恐惧为止”。面对政府的非法暴力,张展沉稳坚毅的语气和行动是这种较量的结果。她知道这个国家 “需要牺牲……换来和平和自由”。
要了解张展的勇气,就必须了解她的基督教信仰。对上帝的敬虔使她蔑视地上的 “神界”,对他们 “身上沾染的权力的傲慢和流氓的习气感到厌恶” ——尽管他们看似 “全能”,可以让天 “准时蔚蓝”、“指标总平稳增长”。
她平视皇帝,不屑他的新装。她的目光穿透政府滥用的暴力,看到统治者的恐惧。她告诉审判长 :“这是审判你的法庭,不是审判我的法庭。” 她不觉孤独,因为 “上帝与我同在”。她鞭策自己 “当然应该寻求真理,不计成本地寻求”。
王剑虹受信仰和道德激情所驱使,细心收集这些散落在新闻报道和社媒的文字,整理编辑成《自由张展》,让读者走进张展的心灵世界、认识这位二十一世纪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也保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当代见证史料,值得我们称谢。
我们声援张展的同时,也应提醒自己 :我们没有权利让张展去为民主和宪政中国殉道,用她的牺牲来遮掩我们的怯懦与麻木。鲁迅当年被捧为战斗者和革命者,听到 “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 后,曾 “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拍手毕竟容易,尤其是让他人去牺牲。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营救北京各校被捕学生出狱后即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引东汉《风俗通义》留下一封公开启事 :“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们不能不献上对张展的敬意,更不能当道旁儿催促乘者驰驱不已。
但若担心张展倾听的是我们在路旁劈劈拍拍的拍手而非真理、信仰与良知的声音,那就是高估了自己,同时也低估了张展。
2024年4月14日
【作者简介】连曦,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研究讲座教授,著有《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印书馆,2021)和《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 。
来源:《自由张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