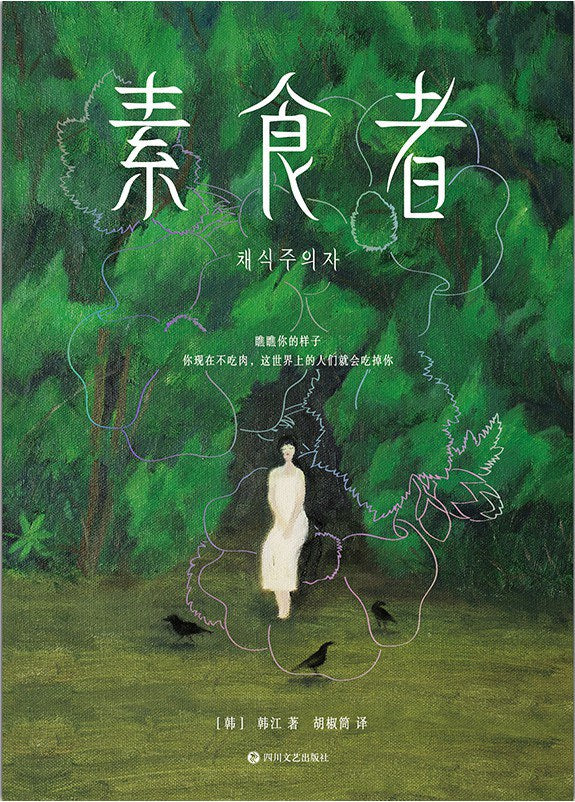必须采取些措施了。
那晚发生的事令我狼狈不堪。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妻子却无动于衷,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搞砸了什么事。她歪斜着身体,将脸靠在车窗上,看起来疲惫不堪。如果按我以往的性格,早就暴跳如雷了。你是想我被公司解雇吗?看看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
但直觉告诉我,此时不管我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任何愤怒和劝解都不可能动摇她,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令我束手无策的地步。
妻子洗漱后换上睡衣,但她没有进卧室,而是走到自己的房间。我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然后拿起了电话,打给住在远方小城镇的岳母。虽然时间尚早,还不到上床睡觉的时间,岳母的声音却昏昏沉沉的。
“你们都好吧?最近都没有你们的消息。”
“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岳父身体怎么样?”
“我们还不是老样子。你工作都还顺利吧?”
我迟疑片刻,回答道:“我很好,只是英惠……”
“英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岳母的声音里带有几分担心。虽然她平时看起来并不怎么关心二女儿,但毕竟妻子也是她的亲骨肉。
“英惠不肯吃肉。”
“什么?”
“她一口肉也不吃,只吃素,这都好几个月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该不是在减肥吧?”
“不知道。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听。因为英惠,我已经好久没在家里吃过肉了。”
岳母张口结舌,我趁机强调说:“您不知道英惠的身体变得多虚弱了。”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让她来听电话。”
“她已经睡下了,明天一早我让她打给您。”
“不用。明天早上我再打过来好了。这孩子可真不叫人省心……我真是没脸见你啊。”
挂断电话后,我翻了翻笔记本,然后拨通了大姨子的电话。四岁的小外甥接起电话大叫了一声:“喂?”
“让你妈妈来听电话。”
大姨子跟妻子长得很像,但她的眼睛更大、更漂亮,重点是,她比妻子更有女人味。大姨子很快接过话筒。
“喂?”
大姨子讲电话时掺杂的鼻音,总是能刺激到我的性欲。我用刚才跟岳母说话的方式告知了她妻子吃素的事,得到相同的惊讶、道歉和许诺后,结束了通话。我迟疑了一下要不要再打给小舅子,但我觉得这样做未免过了头,于是放下了电话。
* * *
我又做了一个梦。
有人杀了人,然后有人不留痕迹地毁尸灭迹。醒来的瞬间,我却什么都记不得了。人是我杀的?不然,我是那个死掉的人?如果我杀了人,死在我手里的人又是谁呢?难道是你?应该是我很熟悉的人。再不然,是你杀了我……那毁尸灭迹的人又是谁呢?那个第三者肯定不是我或你……我记得凶器是一把铁锹,死者被一把硕大的铁锹击中头部而死。钝重的回声,瞬间金属撞击头部的弹性……倒在黑暗中的影子是如此清晰。
我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梦了。这个梦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就像喝醉酒时,总能想起之前醉酒时的样子一样,我在梦里想起了之前做过的梦。不知道是谁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了某个人。恍恍惚惚的、无法掌握的……却能清楚地记得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感。
没有人可以理解吧?从前我就很害怕看到有人在菜板上挥刀,不管持刀的人是姐姐,还是妈妈。我无法解释那种难以忍受的厌恶之情,但这反倒促使我更亲切地对待她们。即使是这样,昨天梦里出现的凶手和死者也不是妈妈或姐姐。只是说她们和梦里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肮脏的、恐怖的、残忍的感觉很像。亲手杀人和被杀的感觉,若不曾经历便无法感受的那种……坚定的、幻灭的,像是留有余温的血一样的感觉。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有的一切让人感到陌生,我仿佛置身在某种物体的背面,像是被关在了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后。不,或许从一开始我就置身于此了,只是现在才醒悟到这一点罢了。一望无际的黑暗,所有的一切黑压压地揉成了一团。
* * *
跟我期待的相反,岳母和大姨子的劝说并没有对妻子的饮食习惯带来任何影响。每逢周末,岳母便会打来电话问我:
“英惠还是不肯吃肉吗?”
就连向来不给我们打电话的岳父也动了怒。坐在一旁的我听到岳父在电话另一头的怒吼声。
“你这是闹什么,就算你不吃肉,可你那年轻气盛的老公怎么办?”
妻子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默默地听着话筒。
“怎么不讲话,你有没有在听啊?”
厨房的汤锅煮沸了,妻子一声不响地把电话放在桌子上,转身走进了厨房,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不知情的岳父可怜地嘶吼着。我只好拿起电话说:
“爸,对不起。”
“不关你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我大吃一惊。因为结婚五年来,我从未听过大男子主义的岳父用充满歉意的口吻跟我讲话。岳父讲话从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他人生里最大的骄傲就是参加过越战,并且获得过荣誉勋章。岳父平时讲话的嗓门非常大,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坚持己见、顽固不化的人。“想当年,我一个人独挡七个越南兵……”这样开头的故事,就连我这个做女婿的也听过两三次了。据说,妻子被这样的父亲打小腿肚一直打到了十八岁。
“……下个月我们会去首尔,到时候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谈吧。”
岳母的生日在六月份。由于二老住得远,所以每年住在首尔的子女都是寄些礼物,然后再打电话为他们贺寿。但这次刚好大姨子家在五月初换了大房子,岳父、岳母为了参观新房也顺便给岳母过生日,所以决定来一趟首尔。即将到来的六月第二个星期日,算是妻子娘家历年来少有的大型聚会。虽然谁也没开口说什么,但我知道全家人已经做好了在当天斥责妻子的准备。
不知妻子对此事是否知情,她还是安然自得地过着每一天。除了有意回避与我同床这件事——她干脆穿着牛仔裤睡觉了。在外人眼里,我们还算是一对正常的夫妻。有别于从前,她的身体日渐消瘦。每天清晨,我关掉闹钟起床时,都会看到她睁着双眼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除此以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自从上次参加过公司的聚餐后,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对我心存质疑。但当我负责的项目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以后,一切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我偶尔会想,像这样跟奇怪的女人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权当她是个外人,不,看成为我洗衣煮饭、打扫房间的姐姐,或是保姆也不错。但问题是,对于一个年轻气盛,虽然觉得日子过得沉闷,但还是想维持婚姻的男人而言,长期禁欲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因为公司聚餐很晚回到家,借着酒劲扑倒了妻子。当我按住她拼命反抗的胳膊,扒下她的裤子时,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低声谩骂拼死挣扎的妻子,试了三次才成功。此时的妻子面无表情地躺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一切结束后,她立刻转过身,用被子蒙住了脸。我去洗澡的时候,她收拾了残局。等我回到床上时,她就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闭眼平躺着。
每当这时,我都会有一种诡异且不祥的预感。虽然我是一个从未有过什么预感,而且对周围环境也不敏感的人,卧室的黑暗和寂静却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第二天一早,妻子坐在餐桌前紧闭着双唇,看到她那张丝毫听不进任何劝解的脸时,我也难掩自己的厌恶之情了。她那副像是历经过千难万险、饱经风霜的表情,简直令我厌恶不已。
距离家庭聚会还剩三天。当天傍晚,首尔提早迎来了酷暑,各大办公楼和商场都开了空调。我在公司吹了一天冷气回到家,打开玄关门看到妻子的瞬间,我立刻关上了门。因为我们住在走廊式的公寓里,所以我怕经过的人看到她这副模样。妻子穿着浅灰色的纯棉裤子,赤裸着上半身,正背靠电视柜坐在地上削着土豆皮。只见她那清晰可见的锁骨下方,点缀着两个由于脂肪过度流失而只有轻微隆起的乳房。
“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我强颜欢笑地问道。妻子头也不抬,一边削着土豆皮一边回答说:
“热。”
我咬紧牙关,在心里呐喊:抬头看我!抬头对我笑笑,告诉我这不过是个玩笑。但妻子没有笑。当时是晚上八点,阳台的门敞着,家里一点也不热,而且她的肩膀上起了鸡皮疙瘩。报纸上堆满了土豆皮,三十多颗土豆也堆成了一座小山。
“削这么多土豆做什么?”
我故作淡定地问她。
“蒸来吃。”
“全部吗?”
“嗯。”
我扑哧笑了出来,内心期待着她能学我笑一下。但是她并没有,她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一眼。
“我只是有点饿而已。”
* * *
我在梦里用刀砍断某人的脖子,由于没有一刀砍断,所以不得不抓着他的头发切下连在一起的部分。每当我把滑溜溜的眼球放在手上时,就会从梦中醒来。清醒的时候,我会想杀死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鸽子,也会想勒死邻居家养了多年的猫。当我腿脚颤抖、冷汗直流的时候,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乎有人附在了我的体内,吞噬了我的灵魂,每当这时……
我的口腔里溢满了口水。走过肉店的时候,我会捂住嘴巴。因为从舌根冒出的口水会浸湿我的嘴唇,然后从我的唇缝里溢出来。
* * *
如果能入睡、如果能失去意识,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在无数个夜里醒来,赤脚徘徊的夜晚,整个房间冷得就跟凉掉的饭和汤一样。黑暗的窗户外伸手不见五指。昏暗处的玄关门偶尔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但没有人敲门。回到卧室把手伸进被子里,一切都凉了。
* * *
如今,我连五分钟的睡眠都无法维持。刚入睡就会做梦,不,那根本不能称为梦。简短的画面断断续续地向我扑来,先是禽兽闪着光的眼睛,然后是流淌的血和破裂的头盖骨,最后出现的又是禽兽的眼睛。那双眼睛好似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一样。我颤抖着睁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我想知道指甲是否还柔软,牙齿是否还温顺。
我能相信的,只有我的胸部,我喜欢我的乳房,因为它没有任何杀伤力。手、脚、牙齿和三寸之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会成为杀戮或伤害人的凶器。但乳房不会,只要拥有圆挺的乳房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为什么它变得越来越消瘦了呢?它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圆挺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越来越瘦了?我变得如此锋利,难道是为了刺穿什么吗?
* *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