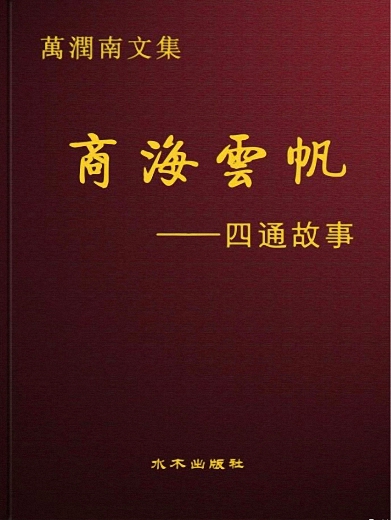第六章 泰山压顶
(37)上阵父子兵
1985年4月8日,调查组正式进驻四通、科海、京海、中科四家公司,一直到同年11月7日 宣布从四通撤出,前后“清理整顿”了我们七个月。
在调查组进驻之前,已经是风声鹤唳。
在1985年3月4日发出的中央红头文件中,四家公司已被定性为“不法组织”,那我就是不法组织的“坏头头”。四通是被告的首犯,我是首犯的首犯。而当局的政策向来是“胁从不问”、“首恶必办”。
为什么汪德昭告状时把我们列为首犯?先生已过世,无从得知其详。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为人海派、“外黑内白”的崔铭山,曾经是汪德昭的司机。
就像四清工作队进村了,我就是那个“四不清”的村干部;就像“文革”时工作组进校了,我就是那个要被打倒的走资派,不,是要被整肃的反动组织的坏头头。
所以当工作组进驻时,我们立即“靠边站”了,准确地说,是被撵到走廊里了。我们的办公室只留下财务一间,其余的都被工作组占领,我们在过道里放了条长沙发,每天在走廊里照常办公。
负责调查四通的组长叫赵陆,北京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一开始,看我的目光都是冷森森的,因为在他眼里,我已经是准专政对象。所谓调查,不过是收集证据。待证据收集齐了,就要将我绳之以法、斩立决了。
在他们看来,像我们这样的民办公司,肯定是一团烂账。你看那个胡石英,居然把大笔现金装在麻袋里塞在床底下。所谓调查,重点就是查财务。
这方面,恰好是我最不担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我父亲是一位非常专业而且敬业的会计师,我在《童年记忆》里曾说过一段往事:国共内战期间,我父亲保管银行的一笔巨款,完璧归赵时,连捆扎现金的绳子都没有解开过。而且,他长期担任财务稽查,专门查别人的账,所以四通的财务管理极其规范。
公司的每一分钱支出,都有根有据,五分钱的公交车票,都要整齐地粘在凭证栏里,以备后查。
有一件公司初创时的轶事:王安时出门谈生意,经常乘坐公交车,回来要凭票报销。有一次,我父亲拿着两张五分钱的公车票,问王总:
“你这次出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王答:“一个人”。其实,他是带着一位女士一起出行的。
“那为什么这两张车票的票号是连着的?” 我父亲又问。
把王安时闹了个大红脸。
老王不以为忤,还赞赏有加。这件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说:“ 老爷子这样管账,不会出事,大家放心。” 我则夸他心胸开阔、善解人意。
四通账目之清楚,让调查组叹为观止。没有查到问题,反而赢得了尊重和一片赞赏。他们说:“就是国家单位,也没有几个能像四通这样账目清楚。” 最直接的证据,是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在调查结束以后,辞掉了公职,要求到四通来上班,我们也愉快地接纳了她。更有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四通来的,我们都照收不误。
当然,这是调查结束以后的事了。但七个月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几千万的往来账,要把每一笔说清楚,拿出每一张凭证,相当耗费精力。不到一个月,我父亲累得眼睛充血,鲜红欲滴,看起来十分怕人。他还是每天捂著一只眼睛,照常上班,因为调查组不会罢休。大家都很心疼,但谁也帮不上。老沈说,他的大舅子,李秀萍的哥哥,在密云的一个单位做会计,要不请他过来帮几天忙?
我立即同意。大舅子来了,只一天,看工作组的堂威森严,吓得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了。
实在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商量:“要不叫小忠来帮一下?”小忠是储忠,我的同胞兄弟,比我小六岁。我在《童年记忆》里说过他的故事。当时他已经从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在上海工商行工作,还是所谓“新长征突击手”,单位里“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

父亲有点犹豫,我说我来给小忠打电话。一个电话,小忠就飞过来了。二话不说,便留下来帮助父兄排忧解难。什么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就是现实版。
我的这个弟弟,和我长得很像,公司里常有人把我们搞错。海淀信用社的老祁,有一次去家里找我父亲,我不在家,储忠初来乍到,没和老祁打招呼。老祁回去后跟崔铭山嘀咕:“那天我去万老家,见到万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理我……”小崔说:“哈,一定搞错了,你把储忠当成万总了。”1989年6月,我离开北京时买机票、住酒店,用的是储忠的工作证,丝毫没有破绽。当然,这是最后的故事了。
汪德昭的告状信里,关于四通,用了六十五个字,除了“总经理系李昌同志的女婿”这十一个字为真,其余的全属子虚乌有。例如说我们“倒卖汽车”,更是捕风捉影。
其“风”或“影”是: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的李丹狄曾找我,说密云有一批汽车,要我们拿200万元人民币,一转手,就是400万元人民币。我有点为难,因为是上级公司。我同父亲商量,他说:这事坚决不能做,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营范围。我就用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婉拒了。不久就看到一个通报,说密云汽车案是个大骗局,有许多单位上当受骗。我在庆幸之余,更体会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前面讲过一个例子是李文元腰斩爆炸喷涂,后来的例子是万老否决汽车案。
老爷子处事方正、待人谦和,在公司里相当有人缘。多年以后,在四通条法部工作过的刘亚军曾经这样评论万老的财务思想——“严谨、准确、为经营管理服务,这在现在看也是很牛的。特别是财务为经营管理服务的思想,至少在国内的企业现在也没普遍建立。而且,他带出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财会专业人员。”其中张延、郭胜荣、刘绿波、汪世平,更被称为四大“财”女。她们离开四通之后,多成为其他大企业的财务主管。
就这样,父子兄弟都聚到一个公司了。后来四通发达以后,偶尔有人诟病我搞“家天下”。我心说:TMD,那时候你们谁肯来啊?!不仅新人不敢来,就是原来的始作俑者,原来打算到四通来入伙的,也不见踪影了。李玉照常给印甫盛、刘菊芬送每个月的顾问费,他们不仅不敢收,还把原来的退回来了。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已经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了。段永基也不见踪影了。我理解,是时机不对。段是聪明人,这时候怎么会往“火坑”里跳呢?李文元也不来了,我更理解,他为了四通的事情,在乡里已经检讨过两次了,还过不了关。
公司里也是人心浮动。“红旗还能打多久?”在许多人内心深处,是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大家关注的目光。出于一种天性,我表现得十分淡定,照常西装笔挺,头发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在古人当中,我喜欢谢安。《世说新语》中有一则他的故事:谢安和朋友乘船出海,遇到了风浪,他“吟啸不言”,“貌闲意悦”,而后“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当时的四通,光是“吟啸不言”、“貌闲意悦”,已不足以镇安朝野。我看到大家脸色的忧郁,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不安。深思熟虑之后,我作了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