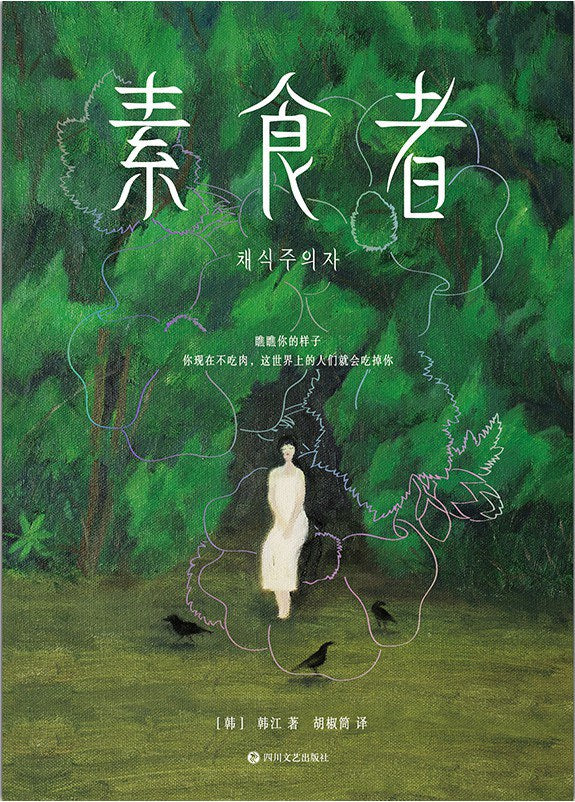她披着他的夹克,穿回了刚才脱下的裤子,双手捧着还在冒着热气的杯子。她没有穿拖鞋,赤脚站在地上。
“你不冷吗?”
面对同样的问题,她摇了摇头。
“……累坏了吧?”
“我只是趴在那里而已,地板也很暖和。”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她没有丝毫的好奇心。正因为这样,她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她不会探索新的空间,也没有相应的感情流露,似乎对她而言,只关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足够了。不,或许她的内心正在发生着非常可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正因为这些事与日常生活并行,所以她才感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根本没有多余的能量可以用在拥有好奇心和探索新事物上。他之所以会冒出这种猜测,是因为有时在她眼神里看到的不是被动和呆滞的麻木感,而是隐含着激情且又在极力克制那股激情的力量。此时此刻的她双手捧着温暖的水杯,像一只怕冷的小鸡蜷缩着身体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但与其说这样的姿势会诱发怜悯,倒不如说她散发着如同阴影般的孤独。这种感觉让人很不舒服。
他想起了那个一开始就不怎么满意的、如今再也不必称为妹夫的她的前夫。那个人长着一张世俗且唯利是图的脸,一想到他用那张只会说客套话的嘴巴亲吻遍她的身体时,一种莫名的羞耻心油然而生。那个愚钝之人会知道她身上长着胎记吗?当脑海中浮现出他们赤裸着身体缠绵在一起时,他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玷污和暴力。
她拿着空杯站起身,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然后接过她手中的空杯放在了桌子上。他重新换了一卷录像带,然后调整了一下三脚架的位置。
“我们重新开工吧。”
她点了点头,然后朝床垫走了过去。由于阳光的光线减弱,他在她的脚下放了一盏钨丝灯。
她脱下衣服,这次面朝上躺在了床垫上。因为是局部照明,所以她的上半身笼罩着暗影,但他还是跟刺眼似的眯起了眼睛。虽然不久前在她家偶然见过她的身体,但此时毫无反抗、与刚才趴着时一样散发着空虚美的身体,足以让他产生难以抗拒的强烈冲动。消瘦的锁骨、因平躺而近似于少年平坦的胸部、凸显的肋骨、微微张开却毫不性感的大腿、仿似睁着眼睛沉睡般的冷酷面容,这是一具每个部位都剔除了赘肉的肉体。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肉体,倾诉着所有心声的肉体。
这次他用黄色和白色从她的锁骨到胸部画了一朵巨大的花。如果说背部画的是在夜晚绽放的花朵,那么胸前则是属于正午灿烂绽放的花朵。橘色的忘忧草在她凹陷的腹部绽放开来,大腿上则纷纷落满了大大小小的金黄色花瓣。
他默默地感受着近四十年来从未体验过的喜悦,那种喜悦从身体的某一个地方静静地流淌出来,汇集到了笔尖上。如果可以,他希望无限延长这种喜悦。照明只打到了她的颈部,所以她布满阴影的脸看上去就跟睡着了一样。但当笔尖画过大腿根时,细微的抖动还是证明了她依然保持着敏感的清醒。静静接受着这一切的她无法看成是某种神圣的象征或是灵长,但又无法称为野兽。他觉得她应该是植物、动物、人类,抑或介于这三者之间的某种陌生的存在。
他放下画笔,完全忘记了是在拍摄。他出神地俯视着她的肉体和上面绽放的花朵。阳光渐渐退去,她的脸也缓缓地随着午后阴影抹去了。他马上回过神,站起身说道:“……侧躺一下。”
她像伴随着某种安静的音乐慢慢地移动着手臂和大腿,弯曲着腰背侧躺了过来。他用镜头捕捉了那如同山脊般柔美的侧腰曲线和背后的黑夜之花,以及胸前的太阳之花。镜头最后停留在了暗光之下的胎记上。犹豫片刻后,他没有遵守事先的约定,利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她那张望着漆黑窗外的脸,模糊的唇线、颧骨凸起的阴影、凌乱的头发之间平坦的额头和空洞的眼神。
她抱着双臂站在玄关处,一直等到他把设备都放进汽车的后备厢。按照M的嘱咐,他把钥匙塞进了楼梯平台的登山鞋里,然后说:
“都搞定了,我们走吧。”
她在毛衣外面披着他的夹克,但还是怕冷似的打着寒战。
“我们去你家附近吃点什么吧?如果太饿的话,就在这附近找点东西吃。”
“我不饿……但这个,洗澡的话会洗掉吧?”
她好像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用手指着自己的胸部问道。
“颜料不太容易洗掉,要洗很多次才能洗干净……”
她打断他的话:
“如果洗不掉该有多好啊。”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被黑暗遮住了半张脸的她。
他们来到市区,找到了一条美食街。因为她不吃肉,所以他特地选了一家招牌上写着素斋的餐厅。他点了两份定食套餐,随后二十余种小菜和加了栗子与人参的石锅饭摆满了餐桌。看着拿起汤匙的她,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刚才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动她一根汗毛。令他感到很意外的是,虽然从一开始也只是计划拍下她的裸体,但自己竟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性欲。
然而此时,面对眼前穿着厚毛衣、正把汤匙放入口中的她,他醒悟到过去一年来折磨着自己的痛苦欲望并没有在当天下午停止。他的眼前立刻闪现过强吻她的嘴唇、粗暴地将她压在身下,以至于餐厅里的所有人都发出尖叫声的画面。他垂下视线,咽了口饭,然后问道:
“你为什么不吃肉了?我一直很好奇,但没找到机会问你。”
她夹着绿豆芽的筷子悬在了空中,抬头看着他。
“如果为难的话,不讲也没关系。”
在脑海里与那些淫乱画面搏斗的他说道。
“没关系,不为难。但我说了,姐夫也未必理解。”
说完,她平静地咀嚼起了绿豆芽。
“……因为梦。”
“梦?”
他反问道。
“因为做了一个梦……所以不吃肉了。”
“那是……做了什么样的梦啊?”
“脸。”
“脸?”
望着一头雾水的他,她浅浅一笑。不知道为什么,那笑容让人觉得充满了阴郁。
“我都说姐夫不会理解的。”
那为什么要在阳光下赤裸上半身呢?这个问题他没有问出口。难道说,突然变成光合成的变异动物也是因为做了梦?
他把车停在公寓门口,然后跟她一起下了车。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她以微笑作答。那表情既安静又亲切,跟妻子有些像,看上去完全跟正常的女人一样。不,她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女人,疯掉的人应该是自己才对。
她用眼神道别后,走进了公寓的玄关。虽然他打算等到她的房间亮灯后再走,但窗户始终漆黑一片。他发动引擎,脑海里想象着她那间漆黑的单人房,以及她没有洗澡,直接赤裸着身体钻进被窝的画面。那是绽放着灿烂花朵的肉体,是几分钟前还跟自己在一起,自己却连指尖都没碰过一下的肉体。
他感到痛苦不已。
晚上九点二十分,他按了709号的门铃。来开门的女人说:“智宇一直嚷嚷着要找妈妈,这才刚睡着。”一个绑着两根辫子,看起来像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小女孩把塑料挖土机玩具车递给了他,他道谢后接过玩具车放进了包里。他打开701号自己家的门,然后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从冰冷的走廊直到孩子房间的这段距离竟是如此遥远。已经五岁的儿子睡觉时还在吃手指,可能是睡得不沉,所以刚把他放到床上就听到寂静的房间里响起了吸吮手指的声音。
他走到客厅,打开灯,锁好玄关的门,然后坐在了沙发上。沉思片刻后,他又站起身打开玄关门走了出去。搭电梯来到一楼后,他坐在停车场的车里,抱着装有两卷六厘米录像带和素描本的包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拿起手机。
“儿子呢?”
妻子的声音很低沉。
“睡着了。”
“他晚上吃了吗?”
“应该吃了吧。我去接他的时候,已经睡着了。”
“哦,我十一点多能到家。”
“儿子睡得很沉……我……”
“嗯?”
“我去一趟工作室,还有些事没做完。”
妻子沉默不语。
“智宇睡得很沉,应该不会醒。最近他不是都一直睡到天亮吗?”
“……”
“你在听吗?”
“……老婆。”
妻子竟然哭了。难道店里没有客人吗?对于很在意他人视线的妻子,哭是非常罕见的事。
“……你想去就去吧。”
片刻过后,他听到了妻子从未有过的、百感交集的声音。
“那我现在关店回去。”
妻子挂断了电话。妻子性格谨慎,平时不管多忙也不会先挂电话。他一时惊慌,突然感到很内疚,手里握着电话犹豫不决起来。不然先回去等妻子,但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随即发动了引擎。现在不是堵车时间,妻子二十分钟之内就能到家,这段时间孩子是不会醒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待在静悄悄的家里,也不想面对妻子那张阴沉的脸。
当他抵达工作室的时候,只看到了J一个人。
“今天这么晚过来,我正准备回去呢。”
他心想,刚才毫不犹豫直接过来简直就是明智之举。因为使用工作室的四个人都是夜猫子,所以晚上独自使用工作室的机会非常难得。
在J整理好东西,穿上风衣的时候,他打开了电脑。J用惊讶的眼神望着他手里拿着的两卷录像带。
“前辈,你拍到东西了。”
“……嗯。”
J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完成了可一定给我看看。”
“知道了。”
J顽皮地朝他行了个礼,然后摇摆手臂做出一副全力奔跑的架势推门走出了工作室。他笑了出来,笑容淡去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笑过了。
他一直工作到天亮,取出母带后,关上了电脑。
拍摄的影片远远超乎了他的期待,光线和氛围,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魅力。他思考了一下应该搭配怎样的背景音乐,但最后还是觉得如同真空状态的沉默最为适合。温柔的肢体语言、绽放在赤裸身体之上的花朵和胎记搭配沉默,会令人联想到某种本质的、永恒的东西。
在漫长的剪辑过程中,他抽完了一包香烟,最终完成的作品播放时间为四分五十五秒。镜头从他提笔作画开始,然后在胎记处淡出,接着特写昏暗中她那张难以辨识出五官的脸,最后镜头彻底淡出。
熬夜后的疲惫感让他觉得身体每个角落都像灌入了沙粒一样干涩,他一边体会着久违的、对一切事物感到陌生的异样感,一边拿起黑色的笔在母带的标签上写下了“胎记1——夜之花与昼之花”。
他眼前又浮现出了朝思暮想的画面,那是尚未尝试的画面,如果可以付之于行动,他希望命名为“胎记2”。事实上,对他而言,那幅画面才是全部。
在如同真空般的沉默中,全身画满花朵的男女缠绵在一起,肉体跟随直觉展现出各种姿势。时而强烈,时而温柔,最后镜头会特写。那是赤裸裸的画面,却因赤裸到了极限而展现出一种宁静与纯真。
他摸着手中的母带思考着,如果要找一个男人和小姨子一起来拍摄的话,那个男人肯定不会是自己。因为他很清楚自己那褶皱的肚皮、长满赘肉的侧腰、松垮的屁股,以及慵懒的大腿线条。
他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汗蒸幕。他换上前台给的白短袖和短裤,站在镜子前以绝望的眼神打量着自己。自己肯定是无法胜任的,那要找谁呢?这不是色情电影,不能装模作样。但要找谁来帮忙呢?谁会同意呢?又该如何说服小姨子接受这件事呢?
他知道自己已经抵达了某种界限,但他无法停止下来。不,他不想停止下来。
他躺在热气缭绕的蒸汽房里等待着睡意来袭,在这个温度与湿度适中的地方,时间仿佛倒退回了夏日的傍晚。全身的能量早已耗尽,他摊开四肢,躺在那里,但那个尚未实现的画面却像温暖的光辉一样笼罩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躯。
在从短暂的睡梦中醒来以前,他看到了她。
她的皮肤呈现出略微阴郁的淡绿色。趴在他面前的身体就跟刚从树枝上脱落下来的、快要枯萎的树叶一样。臀部上的胎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浑身上下遍布的淡绿色。
他把她的身体转了过来。她的上半身发出刺眼的光亮,光源似乎来自她的脸,这使他根本看不清她胸部以上的部位。
电话另一头的她依旧默不作声。
“……英惠。”
“嗯。”
还好她没有沉默太久,但他无法从她的口气里听出是否带有喜悦。
“昨天休息得好吗?”
“很好。”
“我有件事想问你。”
“你说。”
“你身上的画,洗掉了吗?”
“没有。”
他安心地叹了一口气。
“那你能先留着那些画吗?至少到明天为止。作品尚未完成,可能还要再拍一次。”
她是在笑吗?在他看不见的电话另一头,她笑了吗?
“……我想留着这些画,所以没有洗澡。”
她淡淡地回答说。
“身上有了这些画,我不再做梦了。以后如果掉了色,希望你能再帮我画上去。”
虽然无法明确理解她的意思,但他心中的大石总算落地了。他用力握紧手中的电话,心想,小姨子或许会答应这件事,说不定她什么都会答应。
“如果明天有空的话,你能再过来一下吗?那间禅岩地铁站附近的工作室。”
“……好的。”
“不过,还会来一个男人。”
“……”
“他也会脱光衣服,然后在身体上彩绘。这样可以吗?”
他等待着她的回答。按照以往的经验,她的沉默基本上都蕴含着肯定的意味,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不安。
“……好的。”
他放下电话,十指交叉地在客厅里转起了圈。下午三点回到家时,儿子已经去了幼儿园,妻子也去了店里。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要如何打电话跟妻子解释,但拿起电话的下一秒却先打给了小姨子。
在外过夜的事迟早都要解释,于是他拨打了妻子的电话。
“你在哪儿?”
妻子的口气比起冷漠,更像是充满了矛盾。
“我在家。”
“工作都处理好了?”
“还差一点,可能要忙到明天晚上。”
“哦……那你休息吧。”
妻子挂断了电话。如果她能像别人家的妻子一样歇斯底里、勃然大怒、喋喋不休地唠叨几句的话,或许他心里还能舒坦些。但妻子这种轻易放弃,然后将放弃沉淀成犹豫憋在心里的性格,却令他透不过气来。但他知道,这是妻子善良和软弱的一面,是她为理解和关怀对方而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自私和没有责任感。但眼下他只想为自己辩解,正是因为妻子的忍耐和善意令自己透不过气,所以才会让自己变得更糟糕。
当自责、后悔和踌躇这些交织的感情像旋风一样一闪而过后,他按照计划拨打了J的手机。
“前辈?今天晚上过来吗?”
“不去了。”
他回答说。
“昨天熬了一晚上,今天打算在家休息。”
“这样啊。”
J身上散发着二十几岁年轻人特有的自信、朝气和从容。J的身材并不强壮,但十分精瘦结实。他在脑海中想象着J脱光衣服的样子。如果是他,应该没有问题。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明天有空吗?”
“晚上有约了。”
他把M工作室的位置告诉了毫不知情的J。
“只要下午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不会拖到晚上的。”说到这里,他又改变了主意。
“你昨天不是说想看我拍的作品吗?”
J爽快地回了一句:“是啊。”
“那我现在就去工作室。”
说完,他挂了电话。
他期待昨晚剪辑的影片能吸引到J。J的性格温顺,不会轻易拒绝别人,更何况大家一起使用工作室。虽然他不敢肯定,但还是满怀乐观的想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