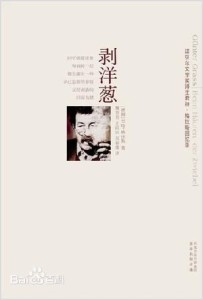火车站里,大家对视野之内的熊熊大火漠不关心。这里熙熙攘攘一切照常:你来我往地拥挤,咒骂,还有突如其来的哄堂大笑声。有人度完假要回前线,有人从前线来要去度假。德意志女青年团的丫头们向大家分发热饮料,被当兵的摸了一把也只是咯咯咯一笑了事。
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
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他,我的父亲,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
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
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
我也从敞开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
火车开了一夜,停了无数次,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它慢吞吞地进站,似乎即使不要求旅客把一切都记录在案,也要求他们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填补未来的记忆空白。
还能记得的是,路堤两边有几幢房子、几片住宅区在燃烧。楼上的窗口里只见火光闪耀。再望下看,是黑咕隆咚的街道和树木茂盛的后院。充其量只有几条剪纸般的人影映入眼帘。看不到成群结队的人。
火车站里,大家对视野之内的熊熊大火漠不关心。这里熙熙攘攘一切照常:你来我往地拥挤,咒骂,还有突如其来的哄堂大笑声。有人度完假要回前线,有人从前线来要去度假。德意志女青年团的丫头们向大家分发热饮料,被当兵的摸了一把也只是咯咯咯一笑了事。
是什么如此刺鼻?是屋顶只是微损而已的车站大厅里蒸汽机车哼哧哼哧喷出的烟雾,还是着火的地方飘来的焦味?
行军给养发下来了,包括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有份。不过,我的香烟转眼就被瓜分一空。作为交换,有个小伙子给了我一点通常过圣诞节时才有的东西:在可可糖浆中滚过的杏仁马铃薯。集合点,报名处,指挥部,无数指示牌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幸好有两个战地宪兵给我指路,他们胸口挂着带链子的金属身份牌,所以人称“铁链警犬”,警告大家小心。在火车站——究竟在柏林的哪个火车站呢?——的售票大厅里,我这个年龄的新兵排着队。等了没多久就有人把一张行军命令塞到我手里:下一站德累斯顿。
现在我看见队伍中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像恩准我们去冒险似的。兴高采烈,轻松愉快。我听见自己在朗声大笑,也不知道此扑面而来,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接着,空袭警报把我们赶到了火车站宽敞的地下大厅,这里被用作防空洞。转眼就有各式人等聚集在此:士兵,平民,包括不少孩子,还有躺在担架上或者撑着拐杖的伤员。人群中有一帮艺人,其中有不少侏儒,都还穿着戏服,他们是演出到一半时听到空袭警报跑到这儿来的。
外面,高射炮砰砰地开火,远方近处都有炸弹呼啸而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这会儿在地下大厅里继续进行:一个矮人上场玩杂耍,圆锥、圆球、彩环在空中上下飞舞,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还有几个侏儒表演杂技,其中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她懂得如何风度优雅地扭曲身子把自己打成个结,同时分发飞吻,赢得无数掌声。这帮艺人是巡回演出的战地剧团,领头的矮老头在场上演小丑。他把从空的到装满水的玻璃杯一字排开,用手指抚摩杯壁,神奇地奏出凄美的音乐来。他上了妆的脸上露出微笑,这画面你一辈子忘不了。
警报一解除,我立刻乘上电车来到另一个火车站。在这儿,又看见住宅区里的窗口火光烛天。又看见整条整条的街道在昨夜的空袭中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远处的一间厂房里烈焰翻腾,好像正在举办灯火辉煌的盛宴。天刚拂晓,开往德累斯顿的火车准备就绪了。
去那儿的路上没啥可说。不谈行军干粮中的夹心面包,也没有什么超前的或后续的思想可供解码。可以断言,因而也就可以怀疑的只有一点:我在这儿,在这座战火尚未波及的城市,确切地说是在新城附近,而且是在位于白鹿区的一户豪门的楼上,才知道自己将去哪支部队。给我的第二道行军命令上写得清清楚楚,叫我这个名字的新入伍者将在党卫军的练兵场受训,成为坦克兵。练兵场在遥远的波西米亚森林中的某个地方……
问题是:我当时是否害怕了?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见这些文字中的两个S还是感到心惊肉跳,当时在征兵办公室里不可能不看见这些,我当时是否同样感到心惊肉跳?
洋葱皮上没有刻下任何可以解读为害怕甚至震惊的痕迹。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我当时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锐部队。要堵截突破我方战线的敌军,要撕开德米扬斯克等地的包围圈,要重新夺回查尔科夫,都得由党卫军上去冲锋陷阵。军装领子上那两个古日耳曼字母S并不让我感到厌恶。对自以为已是堂堂大丈夫的男孩来说,关键的是加入哪个兵种。即便不能去特别报道中已很少提及的潜艇部队,那么也要去“耶尔格·封·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当坦克兵。我在白鹿区指挥部得知,这是一支新建的部队。
我知道弗伦茨贝格是谁:他是农民战争时期施瓦本联盟的首领,人称“雇佣军之父”,以争取自由和解放而闻名。再说,党卫军也不无放眼欧洲的风范:在各个师团里协同作战的志愿兵中有法国人、瓦龙人、佛兰德人和荷兰人,还有不少挪威人、丹麦人,甚至还有中立的瑞典人,他们都在东部前线参加一场据说要在布尔什维克洪流滚滚而来时拯救欧洲的保卫战。
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
我接受坦克兵的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本文节选自《剥洋葱》,君特.格拉斯著,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