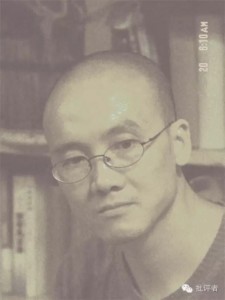 老梦小小的个头,让人无法相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具有了很长的呼吸,虽然诗里含有尚还无从伸展的思辩,但整个的书写基调却是根植于内心的某种浪漫情怀。这一印象,在我们最初的认识与交流中,还不能得到确定。也许写作是散淡的,需要诗人的某种坚定性格来聚拢它的意志。一首多年前写就的诗,要在多年以后才能获得它早就具有的品格,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字就能够做得到。如我们写的那样去生活,去发展我们的面貌,最后让诗立起来。由此,我想起老梦的一副表情,那就是他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在分辨的同时也笑脸相迎。我曾因此怀疑他内心里是否真就有那么一个明亮的世界?后来我明白,这种模糊是缘于他性格上的软弱和退让,并以抱怨的方式轻易获得了发泄。当然,这没有任何力量。你要泥巴立起来,如果他还没有足够的坚硬,他就会摊软。这时候的笑脸,变成了一种顽皮和抵赖。因为他没有无可奈何,就让你觉得,泥巴跟水简直就没有任何区别,它只能停留在自己干枯的地方。再说,老梦的浪漫情怀,也就是他的想象:夜,可以变成白色的大床——你看,床都有了,但他所爱上的女子,还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这女子,也可以说是诗最初化身而来的形象,他们不能合二为一。他写女子再次推门进入他的房间,细节上相当真实,却只能是在丰富着他的幻想。
老梦小小的个头,让人无法相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具有了很长的呼吸,虽然诗里含有尚还无从伸展的思辩,但整个的书写基调却是根植于内心的某种浪漫情怀。这一印象,在我们最初的认识与交流中,还不能得到确定。也许写作是散淡的,需要诗人的某种坚定性格来聚拢它的意志。一首多年前写就的诗,要在多年以后才能获得它早就具有的品格,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字就能够做得到。如我们写的那样去生活,去发展我们的面貌,最后让诗立起来。由此,我想起老梦的一副表情,那就是他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在分辨的同时也笑脸相迎。我曾因此怀疑他内心里是否真就有那么一个明亮的世界?后来我明白,这种模糊是缘于他性格上的软弱和退让,并以抱怨的方式轻易获得了发泄。当然,这没有任何力量。你要泥巴立起来,如果他还没有足够的坚硬,他就会摊软。这时候的笑脸,变成了一种顽皮和抵赖。因为他没有无可奈何,就让你觉得,泥巴跟水简直就没有任何区别,它只能停留在自己干枯的地方。再说,老梦的浪漫情怀,也就是他的想象:夜,可以变成白色的大床——你看,床都有了,但他所爱上的女子,还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这女子,也可以说是诗最初化身而来的形象,他们不能合二为一。他写女子再次推门进入他的房间,细节上相当真实,却只能是在丰富着他的幻想。
对诗歌写作而言,由想象变为虚构,这算是一个进步。虽然不是唯一,也并非必然。事实上,写作所带来的诸多情形都是如此。带着这种类似于里尔克所描述的笼中野兽,老梦的诗思进入到人群,他认为,与人群一起永恒的是地铁。地铁:一个新时代的怪兽。老梦在碰见这只怪兽的时候,显然并不认为它可以是一首诗全部的主题,所以最终只是与它擦肩而过。他所感受到的陌生的脸,和档案中死亡的气息,没能让他在意识上成为一种自觉,以达到像里尔克那样的对于事物最为精准的雕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对于他,甚至对于很多刚刚写诗的人,都并不是不可能做到,而需要的,仅仅是诗人意识上的觉醒。我们不要被太多的思绪所左右,集中一个目标就行。倘是有了这种自觉,然后才是方法上的练习与探究。在这一点上,里尔克对于罗丹的追随,仍然也永久地,还要继续发挥着榜样的效用。
同样,诗人将情绪,或者情感,安置于它本来发生时的场景,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老梦在一首诗里面说过,阳光始终未曾进入中间的客厅,这也许并无必要。并无必要,使阳光变得不再是阳光,而是某种情感的象征。这种日常的场景,带来了友谊,这也是诗人们通常都能把握得住的诗歌主题。它不一定需要命名,甚至也不需要意义和其它,所以,这个主题最为自如自在。一个诗人的心灵,如水在流淌,感应时光。由此我想,诗人对于友谊的把握是不是比对于爱情的把握要相对容易一些呢?友谊不管发生在同性还是异性身上,都可归于同类。爱情确是异类。荡漾在夜色里,随身带着些许花香,这是老梦友谊里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感受着异味。而在异类的世界里,新的变化尚未落下,旧日早已飞走。他在诗里问道:是谁惊醒了我,米沃什,还是布罗茨基?可是笔在哪里?——你看,在他的友谊里,花海涌动层叠的波浪,而恋情,它消失的迅速,始料未及,像是受惊的兔子。人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往往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变得深刻。
在老梦早些时候的诗句里,有一句诗别有深意,那就是:小小的火焰如温存的手指。随着写作经验的结累,和诗人的成长对于生活的切实感受,他注意到:母亲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缺失的牙齿。同时,他的听觉也变得敏感起来,有旗子般的东西在呼啦啦作响。生存的处境也进入到他的诗里——那很远的地方有城市的灯光,每到夜里便灯火辉煌,有时候甚至可以听到,女人的娇笑声。而他,沉默着走进了屋子。我认为,这是老梦习诗多年后最初获得的一个诗人形象。这个形象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由当初那个不确定的浪漫者变为一个沉默者。他的心里感受到了某些纠结——总之,都是你。从我的眼里,心里挖出去的、剩下的,总还是你。经由这些痛苦的纠结,自然地萌生了他对于生命自我的觉悟。可是我睁着眼睛,发现有我才有一切。可是说话时的我去了哪里?带着这样的一个自我,他开始思索——我不知道能否回答关于爱的问题:今天的爱是否是理想之爱,是否是永久,而我们是否永远是爱的主角?对于思考者,是因为思想而感受到了虚无:哦,我扔去谈话——向寂寞中的空虚,没有回响!同时,他从自我中疏离了出来,获得一个他者的身份。于是,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你看,有人美满,有人痛苦,今天我们却也是这中间一人。我——我们。我这时才发觉,老梦不再是我们刚刚初识时的那个老梦。他以自己思辨的方式已经获得了在写作上的某种独立性。我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对这一点还没有全面的认识。其中原因,有我对于那些没有知识背景的写作者很容易就建立起来的怀疑和不信任——尽管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无知无识的人。而当我在集中系统地读过他的诗歌后,才把那些散落各处的光点联系起来,发现它们含有写作中最为内在的一些图像。这些图像,统统都是来自于阅读时的感受。
我刚提到老梦诗中别有深意的一句诗:小小的火焰如温存的手指。其实,我想表达的,主要是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一种声调。这种声调从抽象变为实在,以至成为一个发现,或者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再现:母亲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缺失的牙齿。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声调对文学主题的表达,我认为尚还不够集中。他对于文学主题的发现,还没有自觉的意识。比如:他很像一个失业者,像到了已经是,在他身上另一个可敬的称呼,应和着湿润的大堤。在此,他获得了一个,在湿润的大堤上行走着的失业者的主题。可惜这个主题,被一闪而过。并且,他的诗歌的声调,也形成了非常干练的诗句,体现出反讽的内在力量:蚊子腿上的一丝肉,自然容不下过肥的一只脚。可接下来,非常遗憾,他不去捕捉形象,而是受到了写作时尚的影响,朝着所谓的经典作品去写作:我的口舌是天堂,也是地狱,正如虚空渺渺若玄牝。我如果知道你的一切,但我不知道,黑夜正在朝着他自身倾斜。这与其说是什么经典写作,还不如说是在向心目中的经典学习。学习经典,这当然是一条自我突破的创作道路。我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进展到一定时候,与其在自已崇尚的经典上居高,还不如低下头来虚心求教于历史和哲学,甚至宽泛意义上的宗教。
2008年初,老梦意外地创作《真实的乡村之夜》,他的出发点是反驳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诗作《剃头匠》的取材,为他提供了这样去创作的契机。我以剃头匠为一个进入乡村的角色,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复述了一个公共记忆。《真实的乡村之夜》是对这个公共记忆的一次尝试性进入。他说,在回头描写生活时,出于无法平抑的激荡,产生了相应的暴力,这种暴力表现为对某种习惯力量的强行扭断。接着是短暂的平静。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以农民的生存状态为观察点,来推测所有人的生存:生活既不是苦,也不是乐。它不过是模棱两可的泥巴,可这样糊,那样糊。他觉得自己既不是单纯的农民,也不是现实意味上的城里人,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他复制、审视农村记忆。有的痛苦是由不平导致,演变为讥讽。被讥讽的一切不动声色,无法置疑的强力反过来也观察讥讽者。相互的讥讽获得纠正的力量。讥讽是痛苦的。在他看来,所谓真实的乡村,也许永远不可知。在随后一首诗的创作谈里,老梦意识到时代的局部和时间整体的悖论永远存在于我们身上,要求我们对同时代人产生良心上的负疚,诗歌上的抱负。
对诗歌语言的关注,缘于老梦认为语言上最细微的变化通常属于对诗歌希望有所建树的人。他偶尔发现“风”+“病”=“疯”。一个自然事物的运动加诸肉体上的损伤便会变化为精神上的异常。即自然运动→肉体损伤→精神异常。在这种关系里,语言充当神秘的代言人。他进一步探究,“迷惘—迷网”“方向—芳香”“复活—俘获”也是如此。只是它们的构造稍异于“风”+“病”=“疯”。在一致的拼音字母构成的消去平仄的发音中,他们并没有明显的途径来彼此沟通、组合,进而显示幽秘的通道。迷惘的造成源于迷网,方向引导出芳香,复活起因于俘获。动词造成名词,名词造成形容词,形容词与名词互换,这似乎包含着不可知因果的语言如此奇异,就像他从未认识过它们。言出即为法,声音在寻找他的主人。他发现,除了语音外,形状也是诗歌的秘密。大则为明月,小则为霜雪。这就是秘密。世界处处存在这样的秘密。在对诗歌语言的探索的同时,他对自己的思想状态也产生认识:我这个人对于很多事物的接受都是缓慢而又异常迟钝的,我只有真正去理解了之后才能做出接受甚至吸收。在写作实践中他体会,素手与粗手一般来说在指代意义上可以用来代替男女两个性别,而在某些地方语言的发音中,“su”与“cu”不分。“追逐”和“醉卒”在特定的环境中呈现出相互应和的状态。这体现了词语的丰富性。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信中曾经提及过她的一些发现,“壮美”和“雄壮的美丽”所还原的语言最初的意义也给他带来了启发。他写下《到南京》这个题目,想到“南京”似乎是因为它曾经是“南方的京城”,而这种还原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简单逻辑关系,更是关于历史和时间的永恒话题。当我们试图将古代的某些世像复原时,我们将在这两种可能之间,加上我们自己发明的第三种可能,它根源于历史,或者说时间。事物的最初意义通过代表它们的字构成了我们认识或者判定它的依据,而这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一直贯穿着我们所有的思维,我们用文字记载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如此,只是很多人忽略了它。他试图还原的是语言的本来意义,彰显一个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时候,他获得了一个诗学主张,就是在特定的时候需要拓展空间和想像力时,我们可以用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语音来表达我们所要说出的形状。它具体的方式是:首先,它要求这句话不至于太突兀,要与你的表达能够应和;其次,这句话中所有的节奏、音律都必须要符合我们所要表达事物的形状,它要求我们具有极好的听力。而选择这种表达方式则要求一个诗人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的诗句:满天飞,满天飞,都是些小花。美啊,轻易的就消散,在瞬间。这种声音含糊,意义不是异常明确的句子更多与我们的生活有关,当我们痛苦或者欢欣时,我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就是这样的句子。他推敲欢乐人人都有还是欢乐人人都会,他把会改成有,因为我们可以有,但可能不会。他宣告写完《根源》之后,对于语言的探索状态应该告一段落。自已觉得,语言本身的变形和联系在《根源》里得到体现。黑暗转化为暗黑,然后与夜发生联系,变成我们熟知的黑夜。这种探索也许本身很有意义,但我们不能将之化为目的。这种手段是力图寻找到新的起源和诗意,但不能作为消解文化的目的。诗歌也许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也许会存在。唯一不变的是我们的探索。
《真相》是在以上这样一个探索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一首组诗,是老梦迄今为止的创作高峰。另一方面,它也由于艾略特的《荒原》而产生,更由于创作的焦虑感。里面有他最软弱的情感——我看到了女人——比当初亚当看到夏娃时要激动,因为我传承了悠久的男人的历史。小丽,小云,小娜这代表着我的初恋,刚刚结束的刻骨铭心的恋爱,现在有的单恋依照重要顺序排列下来。他也受到了信仰的触动:容许我暂时抛开友情,想想圣经和其他宗教教导的一切。我不奢望永生,而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精神自由我也不打算就那么轻易的施舍给宗教。他发出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问:与诗歌联系最紧密的是哪个字——像(他的音节即是历史)!通过它,诗歌得以发出许多丰富的声音来。而它的构成是什么?一人一象,你明白了吗——盲人摸象!还须提醒的是,曹冲作为被后世所知并获得巨大声名的工具便是称象。后者所用的计算方式在想像力上趋近于诗歌,在实际操作上则完全是数学!这就是我们不能单独去解释的一切,同时也是本来就存在的两极。除此之外,这组诗还弥漫着很多别的思想观念,比如如何解决与他人相处的问题,为此他写下诗句:他们的冰山将摧毁我的百合。还有对异乡的思考。异乡对所有人都存在着两个意义,一个是实体上的异乡,另一个即为无限中的异乡。最后,他以自己的方式呼应艾略特的写作主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审视自己,都是孤独、脆弱。我所抛弃的终归转回自身——就像过去、现在、未来的循环!而语言是什么?语言即是古今中外的古籍。
接着,我描述一下老梦在诗歌声音意义上的领会,就是他的《声音的饥饿》的诗学文章。我们评判一个诗人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在诗歌乐器上的造诣。乐器就是声音的储藏室。老梦发现,除了深度冥思有可能对声音产生拒绝以外,声音在任何状态中都存在,因为它的产生源于超脱时间与空间的看不见的无法言说的“道”静静的却不可阻挡地穿透一切事物时无形波动引起的诗意反射。哇,这个长长的表述首先就让我们领略到声音的深度呼吸。他认为,我们遇到完全陌生的声音旋律,在精心进入倾听的状态后也会产生下一阶段应该是如此如此的感觉。这种感觉由听力、天赋、阅历、格局等所决定,在最好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旋律和我们的想法合二为一,甚至和更多的人乃至人类大众合二为一。他进而对诗歌的声音作出了类似于定义性的解释:当我们具体谈到诗歌的声音时,必然是指将文字的音节、词语乃至句子的声调、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节奏都包含在内的一种混合的成熟状态。他指出声音中还包含着一种更为晦涩和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诗人的天赋能力。他肯定原创性,衡量一个诗人的天赋能力,依仗的唯有他的原创性,是原创性使一个诗人的声音成熟并区别于他人。在原创性中,包含着一个诗人全部的学识、独特的洞察与特殊的生理构造,如果抛开它们来谈声音,那就只是对简单表层的肤浅触摸。他分析但丁,我们轻轻发声,生恐产生哪怕一点的对挚爱的惊吓。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处注视贝雅特丽齐时,但丁的快速心跳所引起的含在舌尖上将要吐出却只能回荡在胸腔内的全部热情。这种热情并没有通过他的嘴抒发出来,而是通过似乎带有无限光与热的观察转移到那中心本身,这就是在贝雅特丽齐行礼时肢体所充满的严肃的宗教般的神圣效果。他结合中国古诗的戒条起、承、转、合,同样能感受到,由感情的纯粹度所天然选择的声音始终是明亮、温和的,即使在它最高的时候,也没有变得嘶哑和破碎。他分析大师,觉得当大师一说话,哪怕你持反对意见,也会因为其恐怖的发声而事先反省自己,不得不使自己更加慎重。大师潜藏着阴影,即我们过度地依从规矩意味着将面临失去天然感的危险。中国古代杰出诗人有时候通过故意出韵,调整句长的方式来纠正这一点。最终,老梦没有夸大诗歌的声音,因为诗歌的声音是归属于诗歌写作的起点。这样的知识表明,我们对声音的饥饿的忽略自然不仅仅是时代进程的有意而为,也包含着时代对诗人的天然挑选。
我对老梦的诗歌写作及其观念勾勒出来的这个基本面貌,多是依赖于他的写作与言论。我有所选择的表述是基于我们同样作为诗人的那个他。他有自己的一个全面性,当然也包括其中顽固的发展方向,按照自己的风格在走。结合前面的表达,我认为,他早期的写作一个浪漫情怀可以说够。后来诗中出现的诗人形象并不为他在意。他相信一个固执的自我,自比这个形象是在不断变动的液体。他在写作上的主题意识,不像他自己在创作谈和文论中所表述的那般在意。他说一直写生活。他已认识到我所说的主题是指文学母题。写作的创造性(含有雕塑意识),他也淡泊。归集起来说,诗人形象、文学主题、创造性,我认为没有这些自明,谁离诗都还差十万八千里——他必须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自己的写作——沉默地走进屋里,这个非常有诗人的形象;在桥头上的失业者,这个主题不能一笔带过;地铁,这个人造物,也不能只是感叹而已。这样一些跟诗相关的点,怎么来对待?对它们有了处理,创造力就得以表现出来。从其它方面去用力多会误入歧途,只是从气氛上跟诗有关。由于他诗作里面有一些创造性的点他没有抓住,任性而为,因此他的优秀,在别的诗人那儿也能看到,有的甚至更为鲜明,更有创造感。但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都还是处在一个起点似的层面上。接下来,我们必须学会集中一点,全面的表达由这一点深入进去。不然,永远是散的,甚至乱。窗含西岭千秋雪。窗就是点。诗人并不是偶尔写出一两首好的诗歌就能成立。
2010.1.27初稿
2010.1.30修订
作者简介: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
文章来源:批评者201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