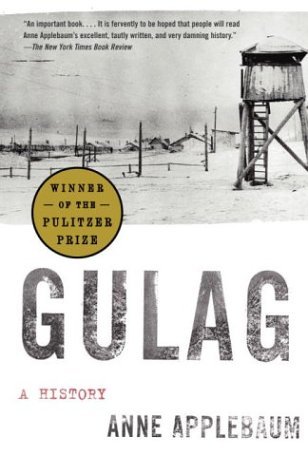1998年初秋,我乘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越过白海到索罗维茨基(Solovetsky)群岛,这个曾经是苏联首个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远方列岛。船上的餐厅充满欢快的气氛。许多人在相互祝福干杯,说笑,为船长热情鼓掌。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旅客是从海军基地来到海岸的两对中年夫妇,他们好像非常开心。起初,我的出现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快乐。在白海上,并不是每天都能碰上乘坐摇摇晃晃的轮渡的真正美国人,这个新奇让他们觉得好玩。当我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做的事情后,他们就不那么开心了。一个美国人乘坐欢快的游船来参观索罗维茨基群岛观赏美丽的景色和古老的寺庙是一回事,到索罗维茨基群岛来看集中营的遗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个人就表现不满了。“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关心我们历史上丑恶的一面?”他问道,“为什么要写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怎么不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他用“我们”是指“我们苏联”。苏联7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但他仍然把自己当作苏联公民,而不是俄国人。
她的夫人也向我发难。“古拉格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她说,“我们有别的麻烦,如失业,犯罪等。你为什么不写我们真正的问题,反而写那些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持续过程中,另一对夫妇一直保持沉默,男的对苏联的过去不置一词。但是,他的夫人表达了支持的观点。“我理解你为什么想知道集中营的事,肯定很有意思,我要是知道多点就好了。”
此后在俄国的考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碰上这四种态度。“关你什么事?”和“有什么意义呢?”是两种常见的反应。沉默或没有意见,像耸耸肩可能是最常见反应。但是也有人知道了解过去的重要性希望更容易找到更多的东西。
纪念碑和公众意识
事实上,稍微用点劲就能在当今的俄国了解很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俄国档案馆都是封闭的,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忙着别的事情。古拉格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苏联卫星国的公众辩论的话题。在有些国家,(一般地讲,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纪念活动和辩论实际上往往很激烈。
散布在俄国各地的还有很多非正式的,半官方的,私人的纪念碑,博物馆,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或组织建立的。让人奇怪和吃惊的是个人纪念碑有时候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一个铁十字架被放在Ukhta市外面的光秃秃的山上来纪念大批囚犯被杀害的地方。为了看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开车穿过几乎走不成的泥巴路,走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翻过铁路道轨。即使这样我还是离得太远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尽管这样,几年前树立十字架的当地积极分子在指给我看的时候掩饰不住自豪的神情。
沿着柏崔左伏斯克(Petrozavodsk)往北几个小时的路程,就来到建立在Sandormokh村外面的另一个特别纪念馆,索罗维茨基群岛的囚犯在1937年被枪决。因为没有记录谁埋在哪里,家属们只好随意地挑选一堆骨头纪念。死者的亲属将死掉多年的亲人的照片贴在木头桩上,有些在旁边刻有墓志铭。丝带,鲜花和其他小装饰撒在曾是杀人现场长成的松树林。在我凭吊的8月的大晴天(屠杀的纪念日,有来自彼得堡的代表团),一个老太太在诉说埋在这里的父母,在她7岁的时候,他们都被枪杀。她在度过了几乎整个生命的时候才能来看望他们。
但是在习惯于规模宏大的战争纪念馆和巨大庄严的国家公墓的俄国,这些个人和地方单位建立的墓地显得粗劣,零散,不完整。大多数俄国人可能都意识不到这些的存在。难怪,苏联解体十年以后,俄国继续表现得好像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历史一样。虽然它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苏联的大使馆,苏联的债务,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俄国没有纪念压迫历史的国家博物馆。俄国也没有一个悼念死者的地方,一个官方确认死难者及其亲属痛苦的纪念碑。
然而,比缺乏纪念碑更明显的是公众意识的丧失。有时候好像戈尔巴乔夫时代大规模讨论引发的强烈冲动和感情随着苏联的解体完全消失了。为死难者讨回公道的激烈辩论一下子突然不见了。虽然在八十年代末期还有很多讨论,俄国政府从来没有检验或审判大屠杀的凶手,即使在认定究竟是具体哪些人的情况下。
当然,审判不一定是解决过去历史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除了审判还有别的方法给以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公正的处理。比如,像南非推行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让受害者正式的、公开的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过去的犯罪行为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还可以进行官方的调查,像2002年英国议会对北爱尔兰30年前发生的“血腥星期天”屠杀事件的调查。有政府的调查,政府的委员会,公开的道歉等。但是俄国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选择。除了这个草草了事、没有结果的对共产党的“审判”,在俄国事实上并没有公开的诉说真相的行动,没有议会听证会,对苏联的枪决,屠杀,和集中营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调查。
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后,德国人仍然在进行定期的公开辩论关于受害者赔偿,关于纪念馆问题,关于纳粹历史的解释问题,甚至新一代德国人是不是继续背负纳粹罪行的愧疚负担等。但是在斯大林去世的一个世纪后,俄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争论,因为过去的记忆不再是公众文本的活生生的一部分。
俄国人的平反昭雪过程从1990年以来确实在继续,静悄悄的在进行。到了2001年底,俄国有大约四百五十万政治犯被恢复名誉。国家平反委员会估计仍有五十万案件需要审查。但是虽然委员会本身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委员会由集中营幸存者和官员组成,参与者没有真正感觉到创造这个委员会的政治人物是出于追查用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米兰黛勒(Catherine Merridale)的话说“真相和和解”为真正驱动力的动机,相反,这么做的目标是停止对过去的讨论,给那些受害者几个卢布和免费乘车券安慰一下,避免任何对斯大林主义的原因及其遗产进行更深刻的考察。
改变的东西越多,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越多
对这种公众沉默有些好的或至少可以接受的解释。多数俄国人确实真的花全部的时间配合他们经济和社会的彻底转型。斯大林主义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终结之后又发生了太多的事。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不是战后的德国,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许多人心里仍然清晰可见。在21世纪初期,20世纪中期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来说好像古代历史一样遥远。
也许更确切地说,许多俄国人感觉过去的事情已经讨论过了,再追究下去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当你问上了年纪的俄国人为什么古拉格的话题如今不再提起了时,他们往往这样回避“在九十年代那是我们唯一能够谈论的东西,现在我们不需要再继续谈下去了。”
但是这种沉默还有其他一些让人难以原谅的原因。许多俄国人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并认为这是对他们自尊心的重大打击。他们现在觉得,也许旧的制度确实糟糕,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们是强大的。现在我们不强大了,我们不愿意再听到别人对它说三道四。就像谈论死去的人的缺点,太痛苦了。
还有些人仍然担心如果继续深入挖掘过去,谁知道还会发现别的什么东西来。俄国改造委员会的主席亚可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非常坦率的指出“社会对过去的罪行漠不关心,因为有太多的人直接参与了这些罪行。”苏维埃制度让数百万的民众成为犯罪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者和帮凶。虽然有许多是主动参加的,还有许多体面的人是被迫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子孙并不总要记住让他们丢脸的往事。
但是对于缺乏公众辩论的最重要的解释并不是涉及年轻一代的恐惧或自卑情结或父辈罪行的残余。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今当政者的权力和地位,不仅是俄国,还有许多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卫星国。在苏联解体10周年的2001年12月,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3个是被前共产党员所掌握,许多卫星国也一样。甚至在那些不是由共产党意识形态影响实际控制的国家,前共产党员及他们的子女或跟随者仍然是主导社会的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商界精英。普京总统(Vladimir Putin)本人是从前的克格勃成员,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个Chekist,这个词曾经是来描述列宁在革命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在后共产主义世界,前共产党员占主导地位和缺乏对过去的讨论之间并不是巧合。说得明白一点,前共产党员在掩盖过去的罪行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过去的事情让他们蒙受耻辱,让他们受到损害,伤害他们声称要进行的改革,即使他们自己与过去的罪行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以给出太多太多的理由解释俄国为什么不建立国家纪念碑来纪念数百万的受害者,但是亚可夫列夫再次给出了最简洁一针见血的解释:“当我们—老一代人都死掉后,纪念碑就建起来了。”
这个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能正视,悔改和讨论共产党的历史就像一块石头压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头上。关于老的“秘密档案”内容的风言风语继续让当今的政治局势陷入动荡,至少破坏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总理的政治地位。过去和共产主义老大哥达成的一些交易到现在仍然持续发酵产生影响。在很多地方,秘密警察机制—干部,设施,办公室—基本维持不变。偶尔发现的新的尸骨能一下子激起冲突和愤怒的火焰。
这个过去的包袱在俄国表现的尤其严重。俄国继承了苏维埃权力的全套装饰,和苏联的大国情结,苏联的军事设施,苏联的帝国目标。因而,俄国对政治后果的缺乏记忆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危害更大。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斯大林将车臣人(Chechen)驱逐流放到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荒原,其中一半人死在那里,本来是打算让剩下的人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消失。50年后的今天,俄罗斯联邦军队故伎重演,开进车臣首都格罗兹尼(Grozny),在两次战争中屠杀了上万车臣平民。如果俄国人和俄国精英发自肺腑的,真心地记得斯大林对车臣人做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在1990年入侵车臣,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这样的行为简直就像战后的德国又一次入侵波兰西部一样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是很少俄国人这样看问题。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有多么无知。这对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再说的重一些,如果让旧政权的恶棍逍遥法外,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这听起来有点像启示录,但是在政治上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为了让大多数民众遵守公共秩序,警察不需要抓住所有时代的所有犯罪分子,但是他们需要抓住相当一部分。没有什么让犯罪分子看到可以逍遥法外,逃脱惩罚,嘲弄众人更容易鼓励无法无天的情况了。秘密警察继续拥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别墅,丰厚的养老金。而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穷,被人遗忘。对许多俄国人来说,好像是说你越和过去合作,你就越聪明。同样的,你如今欺骗的越多,撒谎越多,你就越聪明。
从更深层次上说,古拉格的一些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新的俄罗斯精英的态度和世界观中。老斯大林主义者把人分成两类一是享受所有权力的精英一是不值一提的“敌人”,现在的新俄罗斯精英则对自己同胞表现出傲慢与蔑视。除非那些精英不久认识到所有俄国公民的价值和重要性,尊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俄国将最终逃脱不了成为当今的北方扎伊尔的命运,一个居住着贫穷不堪的农民和亿万富翁的政治精英的国度,这些权贵将资产存放在瑞士银行的金库中,跑道上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工程师在跑前跑后。
可悲的是,俄国对过去的缺乏兴趣剥夺了俄国人自己的英雄和恶棍。那些秘密反对斯大林的人物的名字,不管他们反抗的结果如何都应该让俄国人了解,就像在德国刺杀希特勒政变的参加者的名字一样。俄国幸存者文学的难以相信的宝库,那些讲述人性战胜苏维埃集中营可怕情景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阅读,更多的人引用。如果学生对这些英雄和故事了解的更多,他们就发现除了帝国的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有更多让他们引以自豪的俄罗斯的过去。
但是不能记住过去还有更多世俗的、实际的后果。比如,人们或许争论俄国不能正确看待过去也解释了他们对现在仍然在推行的某些形式的审查的无动于衷。秘密警察仍然猖獗,不过现在起了个新的名字叫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 或者FSB。大多数俄国人不怎么在乎FSB的能力打开邮件,监听电话,没有法院命令进入私宅等。
对过去缺乏敏感也能解释俄国为什么没有进行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改革。1998年,我曾经参观过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市的中央监狱,曾经是古拉格的主要城市监狱之一。这个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的城市监狱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当我走在石头建筑的大厅时,旁边是一声不吭的监狱看守,就好像我们回到了我曾经阅读过的古拉格回忆录录中。牢房狭小,里面空气污浊,墙壁潮湿,卫生条件极差。监狱长耸耸肩,说这都是因为没钱。走廊黑暗是因为电费太贵,囚犯等几个星期才能审判是因为法官待遇太差。我不同意这个解释。缺钱是个问题,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俄国的监狱仍然和斯大林时代的监狱一样,如果俄国的法庭和犯罪调查只是摆设,那部分是因为苏维埃的遗产不像忏悔意识悬在控制俄国刑事审判制度头上。过去的罪恶并不来打扰俄国的秘密警察,俄国的法官,俄国的政客,俄国的商界精英。
但是,当今俄国很少有人觉得过去是个负担,或是个责任。过去是个应该忘记的噩梦,或者是个不能当真的闲话。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静静地躺在一边等着下一代人打开。
西方记忆缺失
我们西方不明白发生在苏联和中欧的事情的重大价值当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那样深刻的影响。我们大学里对奇怪的“古拉格否认者”的宽容不会摧毁我们社会的道德构成。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西方的共产党已经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支持。
但是,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记住过去的历史,对我们自己也能产生后果。其中之一是,我们对现在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的理解将继续遭到我们对历史误解造成的歪曲。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斯大林对车臣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是对车臣人犯下的严重罪行,那么不仅普京现在不能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袖手旁观。苏联的垮台也不会像二战结束一样激励西方势力同等程度的动员。当纳粹德国最终倒台的时候,西方其他地方成立了北约和欧洲联盟—部分目的是防止德国再次脱离文明的“常态”。相反,直到2001年9月11日,西方国家才开始认真重新考虑他们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然后有更强烈的动机和需要让俄国回到西方的文明中来。
但是最后,对外政策的后果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古拉格,迟早会发现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冷战?是因为疯狂的右翼政客吗?是与政客勾结的军事工业集团和中央情报局编造的整个事件强迫西欧和美国的两代人参与其中么?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困惑已经出现了。2002年,保守的英国《观察家》Spectator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是有史以来最没有必要的冲突之一。”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也把冷战描述成为“四十年没有思想的战争,只是造成了五万亿美元债务。”
因而我们忘记了让我们动员起来的事情,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激情,长久以来让西方文明连结在一起的理想。我们忘记了我们坚决反对与之作战的罪恶。如果我们不能竭力记住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另一个20世纪极权统治政权的历史,最终西方会发现无法理解自己的过去,我们将不理解我们的世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不仅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忘记另一半欧洲的历史,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将会被歪曲。每一个20世纪的群众灾难都是独一无二的: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纳粹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柬埔寨革命,波黑战争等等。这些事件都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渊源,每一个事件都是在某个特定环境中产生,同样的环境将不再可能重复出现。只有我们贬损、摧毁、非人化自己同胞的能力在不断重复并将一再重复:我们要将邻居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看成虱子或臭虫或毒草,把我们的受害者重新塑造成低等的,少量的,恶棍只配关禁闭,驱逐或枪毙。
我们越是能够理解别的社会是如何将他们的邻居或同胞从人变成物品,我们对导致大迫害和大屠杀的具体情况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明白我们人类本身的丑恶的一面。极权哲学曾经而且将继续对众多人有强烈的吸引力。正如德国犹太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说的,摧毁“典型的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者最根本的目标。我们需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回忆,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一个迷,一个解释。没有了这些,总有一天醒来会发现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译自:“The Gulag: Lest We Forget” by Anne Applebaum
http://www.hooverdigest.org/051/applebaum.html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