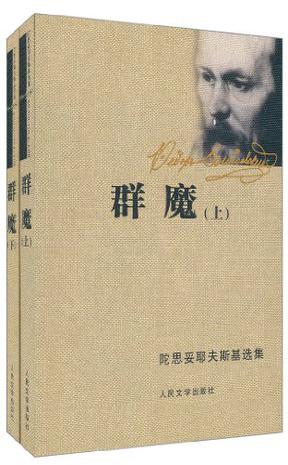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真正的思想盛宴
涅恰耶夫,是这一盛宴里最让人无法忘却的思想飓风
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主人公的原型
是巴枯宁、别林斯基的朋友和背叛者
是一位融合革命激情和虚伪骗局的职业革命家
是俄国19世纪民粹派运动的精神领袖
是“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和恐怖主义的倡导者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不陌生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就是广大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两部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名著。《怎么办?》中的主人公——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这位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做是“盐中之盐”、“茶中之碱”、“原动力之原动力”、“花香之精粹”、“大地之精华”的所谓“新人中的新人”,曾激励过无数的中国读者。他是一个坚定的俄国职业革命家,立志毕生献给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解放运动。为此,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刻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拉赫美托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坚韧的意志,的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生活中所奉行的那一套绝对的禁欲主义原则,以及“睡钉子床”这一非常态的举动,也着实让一般读者在敬佩、惊讶乃至难以置信之余,在读者心目中无形地勾画出想象中的革命者(确切地说,是暴力革命者)的理想肖像。人们以为,革命,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必须有绝对坚强的意志,就意味着必须绝对地抛弃个人的私欲。一个革命者必须绝对地把自己视为革命事业这个伟大工程中的一架机器,必须绝对地消磨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这一切都被读者视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理应具有的美好品质。而这一切观念,应该说,与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的。
然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摆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时,小说中的革命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却又在无形中颠覆着读者心里那业已铸成的革命者形象。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残忍、冷酷、绝情的特性,将读者心中长期形成的对革命者的美好印象一扫而光,以至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颇有微词——毕竟,我们难以接受陀氏笔下这个“恶魔”般的革命者,这不啻为对革命者的一种诽谤。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曾是革命阵营里的一员。一个人是绝不会无端地轻易否定自己充满激情的年轻时代的精神追求的。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曾真诚地信奉过暴力革命,是一名狂热的社会主义革命斗士。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改变信仰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和革命者,他对革命者的“诽谤”才会如此地难以反驳,才会不得不让人们去深思:在俄国的革命者身上,究竟有什么悲剧性的精神特质?
尽管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很不习惯于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与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甚至屠格涅夫晚年的两部作品《烟》和《处女地》联系在一起观照,毕竟在许多中国读者的眼里,这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的作品。但从客观事实而言,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却真地将它们联系到了一起。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就是谢尔盖·盖纳基耶维奇·涅恰耶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1862年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涅恰耶夫时年15岁。这部小说给涅恰耶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小说中那位“特殊的新人”——拉赫美托夫的形象,更是让年少的涅恰耶夫激动不已。他立志要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一个信奉严酷的宗派主义革命原则的革命志士。他坚信,强有力的个人完全可以有权力超越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因为那些法律与社会道德究竟是为旧世界而定的。而当涅恰耶夫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一步步地实践了自己年少时的设想,成为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位叱咤风云的领导者时,冷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以他为人物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群魔》,将“现实版”的拉赫美托夫艺术化为他笔下的恶魔般的虚无主义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以说,正是涅恰耶夫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形象“拉赫美托夫”的“妖魔化”。
然而,客观而言,涅恰耶夫在俄国的出现绝非偶然。“拉赫美托夫”的“妖魔化”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也绝不是凭空地杜撰出这一“超现实性”人物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俄罗斯人性格中那易偏激和爱走极端的特性,以及俄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启蒙理性思想观念在俄国社会传播的不彻底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性等,均是俄国产生涅恰耶夫式人物的社会原因。这种类型的革命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性、偏激性和矛盾性,也恰好成为整个俄国暴力革命史的真实的写照。涅恰耶夫是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思想对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一代影响甚大。他在国外的广泛而积极的行动,与巴枯宁、奥加辽夫等人的广泛接触,以及从国外俄侨那里获得的巨大资助,使他一度蒙蔽了眼光一贯非常透彻的赫尔岑。众所周知,涅恰耶夫的历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长篇小说《群魔》的材料。在这部作品中,天才的作家发出了警告,指出在俄国存在着出现这类人物的危险。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幸证实了作家的预感。这些革命者的悲剧恰恰是俄国19~20世纪历史进程悲剧性的体现。对于熟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了解涅恰耶夫这个历史人物,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诸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烟》、《处女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等文学名著的内涵,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能够洞察出俄国社会悲剧性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原因。
从涅恰耶夫事件中可以发现,来自政府一方的镇压与迫害愈是严厉,就愈有可能出现与之产生对抗的犯罪组织。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讽刺性作品《现代田园诗》中曾出色地描绘了一群被监视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他们竟然企图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可靠性。在象俄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往往对待刑事犯是宽容的,而对待政治犯则是过分严厉的。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在沙皇统治者看来,刑事犯不是异己力量,只有政治犯才是有可能颠覆自己的统治的异己力量。涅恰耶夫式的革命者之所以会在俄国出现,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涅恰耶夫身上体现出革命者的复杂性。善与恶、理智与情感、谦和性与自主性、独立性与奴性等等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矛盾性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特性的一种体现。20世纪以来,不少俄罗斯思想家都注意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这一特点。高尔基、罗赞诺夫、别尔嘉耶夫等来自不同阵营的思想家都试图深入地剖析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罗赞诺夫在他的学术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里指出,“如果我们不再把思想和愿望指向某种遥远的东西,那么,我们将重新感觉到从徒劳的漂泊中向我们返回来的力量的完满”。对那遥远的目标的狂热追求和对身边现实的生活的漠视和冷酷,这的确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特点(或曰弱点)。高尔基在他的评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里就深刻地批判了这一民族劣根性。这种民族性格特质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而对于那些俄国革命者而言,构成那些具有造反性格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极端的嫉妒、冒险主义、企图不择手段地致富或表现自己、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等等。不过,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这些人在道德信念上都是极不可靠的。他们的狂热激情愈强烈,他们就愈有可能跨越道德的界限。而所有这些精神特质极有可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革命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出这些特质。而一旦这些特质全都集中地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时,这样的人就是最危险的。涅恰耶夫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者。
在俄国十二月党人中,大约只有两、三个人属于这种突破道德约束的狂热分子,譬如德米特里和伊波利特·扎瓦利欣和罗曼·梅多克斯,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里也只有两、三人是这样的狂热分子,譬如В·П·卡捷涅夫,在所谓“60年代人”当中,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烈夫的同时代人当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三个人属于这一类型。然而,稍后出现的涅恰耶夫则全面超越了所有这些人。作为文学作品之原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主人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被指责对革命者实施了诽谤。可以说,涅恰耶夫的经历展示了众多值得探究的深渊,正如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Ф·卢里约所言,“甚至可以反过来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对该人物有所粉饰”。
俄罗斯民族为人类贡献出了不朽的文化,但它也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某些悲剧。巴枯宁、涅恰耶夫等极端性人物的出现,既给俄罗斯社会的历史进程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同时也为其他民族和国度的人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一面历史之镜。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学者就开始了对涅恰耶夫的研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阶段,对涅恰耶夫则是大力吹捧,将他捧为俄国革命者的楷模,甚至直接将涅恰耶夫的思想与行为同列宁—斯大林的政党挂上钩。譬如,A·加姆巴洛夫在其著作《关于涅恰耶夫的手记》(莫斯科,1926年)中写道:“历史不仅仅正在为涅恰耶夫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久远的先驱恢复名誉,历史其实已经为他正了名”。不过,在苏联,对涅恰耶夫的研究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尽管涅恰耶夫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但对一位像他这样极具颠覆力的人物的宣传毕竟是不利于对现有政权的巩固的。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斯学者才重新开始深入研究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费里克斯·莫伊塞维奇·卢里约等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对涅恰耶夫的生平、经历和历史意义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深入的分析。确实,在恐怖主义思想泛滥猖獗的今天,研究思考涅恰耶夫的精神特质,无疑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来源:《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