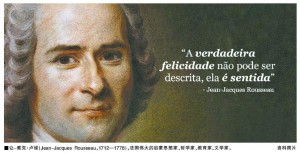“文如其人,”老生常谈,而亦谈何容易哉!
——钱钟书
只要惊人的书写艺术,或方便的书写,即我们所说的印刷术继续存在,他就会永远作为一种主要的英雄主义类型而存在。……他死后,就在自己的墓穴里统治着整个民族和一代代人,而他在世时,他们还不定给不给他面包哩。
——托马斯·卡莱尔
一、
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写道:“苏格拉底、佛陀、卢梭,这三位文明的代表者,各自埋葬了一段千百年的精神深度。”稍早些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论断更酷:“卢梭的笔造成的影响超过亚理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有史以来任何一人。”以撒亚·伯林坚持认为,“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噫,那是独步古今兼遗臭万年的待遇,斯何人欤?
保罗·约翰逊视卢梭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是他们的原型”,在他那本评判知识分子的专著《知识分子》里(该书侧重展示十余位人文精英令人咋舌的负面人品),卢梭理所当然位列第一。在以撒亚·伯林概括“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的著作《自由及其背叛》里,卢梭因年齿而屈居爱尔维修之后,在重要性上仍遥遥居前。英国学者尼格尔·罗杰斯、麦尔·汤普森合著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一书里,卢梭再次率先遭到犀利批判。
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如“自由、平等、博爱”,与卢梭密切相关。一个世纪后,乔治·奥威尔在法国的当铺和警察局门楣上都能见到这六个高悬大字,阿尔贝·加缪则在监狱和教堂里看到同样字眼。逮至20世纪,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又纷纷将卢梭视为自由最可怕的敌人,这肯定意味深长。
现当代民主思想固然从卢梭那里汲取了大量营养,反其道而行之的极权体制,竟也同样得力于卢梭的召唤。卢梭就像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既面向光明,又投向黑暗,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两极,同时发挥作用,而接受他思想照耀的那两类人,则视若寇仇,纷纷想取彼而代之。与卢梭同期的英国文豪约翰逊博士曾在一次文人聚会上拍案怒吼:“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之一,一个无赖,他应该像以往一样被逐出社会。”在私人行事及写作风格上与卢梭绝不相类的康德,却认为他“有一个无比完美的敏感的心灵”,康德对“视觉艺术毫不在意”,书桌上方却单单悬挂着一幅卢梭版画像。
卢梭坚信后世一定会为他塑像,并夸口道:“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次他说大了,卢梭晚年时遇到一个主动请求为他塑像的人,不仅手艺拙劣,把他的“漂亮脸蛋”弄得非常糟糕,而且,那家伙压根没有读过卢梭的书。不用说,“漂亮脸蛋”也是卢梭重申多次的自我评价。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认为卢梭属于这样一类人,“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对德国文学双子座歌德、席勒的影响也众所周知。在卢梭写出《忏悔录》之前,也有作者尝试以本人为书写对象,但大多注重自我的精神发展。古典作家对道德的追求——包括与身份意识相伴的体面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自我当作抒情、揭露或玩味对象。但在卢梭之后,就像山洪决堤,以“我!我!我!”为主题的作品,就“哦!哦!哦!”“啊!啊!啊!”地层出不穷了。——附带一说,约翰·密尔倒完全没有受到卢梭文风的侵袭,他那部致力于展示思想发展的自传,甚至一次没有提到母亲。
总之,卢梭文学上的影响实在太大,几乎无劳举证。以撒亚·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一书梳理了林林总总、形式各异的浪漫主义,它们共有一个祖先:让-雅克·卢梭。大量今人熟知且常被冠以“波希米亚风”的现代艺术家穿戴,亦可溯源到卢梭。是卢梭而不是别人,最早用一套愤世嫉俗的穿戴震惊了法国宫廷和上流社会,震惊之余,对时尚嬗变具有“狗仔队”嗅觉的诗人、艺术家群体,成为卢梭式穿戴的最早拥趸。在卢梭的早期模仿者里,我们可以找到雪莱、拜伦、乔治·桑的名字,之后就数不胜数了,以至20世纪20年代,据章克标《文坛登龙术》描写,在距卢梭时空上相当遥远的中国上海,也出现了大量长发飘飘的青年画家。
即使在那些对卢梭缺乏了解的人群里,我们仍能见到卢梭的影响。《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的作者写道:“那些喜欢‘天然矿泉水’的人是在不知不觉地对卢梭的观点表示敬意。”粗线条地看,这个说法成立,至今那些声称取自幽邃高山或火山喷发形成的泉井的矿泉水(如著名的维希矿泉水),仍能售出高昂价格,即可视为卢梭式敬意的一部分。但是,一方面维希泉早在古罗马即被视为圣水,另一方面卢梭在《忏悔录》里至少提供过两次反例,强调天然并不优于人工:他早年生了一场大病,病源即来自那些“有点硬,不易消化”的“山中的水”;当他的保护人华伦夫人为了卢梭早日康复而建议他直接去农民家喝新鲜牛奶时,卢梭的身体同样表示抗议。卢梭的影响力是如此错杂怪诞,沃尔特·李普曼曾感慨道:
卢梭生前的名望以及死后的影响力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关于人类易于受骗上当。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嗜好,他们拒绝接受他们不愿承认的证据。
稍稍延伸一下话题,世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亦回应着卢梭式影响。转基因食品恐惧者通常缺乏相关科学知识,其恐惧只是建立在一个单纯想法上:自然是好的,天然优于人工。这个最初由卢梭小说《爱弥儿》传播的观念,打从出世时就以其国色天香的魅影诱惑了无数人,尽管它一次没有被证明是一种科学论断。将学说的可信度建立在“美丽”上,会让世上哲学家、科学家不知所措,但民众总是热衷投其所好的观点,他们可以单凭观点的外貌涂层,决定取舍,于是,“美丽”便具备了最大的成功率和杀伤力,而提供美丽的观点,恰是卢梭所长。
二
笔者意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鉴于卢梭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学两大领域,我们研讨其知识分子作用时,就得留意属于文学的那部分影响力,避免混淆。赞美罂粟花的美丽与指出其毒性,并不矛盾,同理,一种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对文学发展作出巨大推动的写作手法,却对知识分子品格及其写作方式构成恶性示范,也是可能的。卢梭的文化伟人兼历史巨人身份要求后人对他的影响力慎重评判,而他的文学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又构成一种交叉互渗,我们很难将其截然分开。小说《爱弥儿》的副标题是“论教育”,这到底算文学创作还是学术论述呢?实际上兼而有之。
纠缠于文体之别是文坛学究的惯技,他们若不能对文体先行定位,就不知言从何出;而如卢梭这类老辣的文字玩家,热衷于打破体裁界限,让文字身兼多种功能,故钱钟书尝谆谆叮咛:“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
虽然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卢梭已辞世十年,但卢梭思想之于法国大革命,就像马克思主义之于苏联十月革命。以卢梭私淑弟子自居的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曾说:“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深入探讨了以卢梭为代表的作家、文人群体对革命的巨大影响,简而言之,那正是一场由“墓穴里”的哲学家主导的全方位革命。伏尔泰、卢梭等人影响下的法国,受到了“文学政治”的强烈感染,托克维尔写道:
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托克维尔甚至发现,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在诉状中称邻舍为同胞”。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九三年》里,我们也能得到可靠印证,小说里的保皇党人德·朗德纳克侯爵是这样解释法国大革命的:
想想看,如果伏尔泰被绞死了,卢梭被送去做苦工,这一切就根本不会发生!唉!这些才智超群的人,真是莫大的祸患!
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大量杀戮,侯爵坚持认为:“有耍弄笔杆的下等文人,就会有下手杀人的歹徒。”托克维尔的著名警告是:
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然而,奇怪的是,最适合向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卢梭著作《社会契约论》(伯林即认为“卢梭的名字是与《社会契约论》相提并论的”),当时却乏人问津。该书完成于1752年,十年后才得以出版,1791年又重印了一次。保罗·约翰逊告诉我们,“当时的500家图书馆中只有1家收藏了这本书。”他还提到一位学者琼·麦克唐纳,后者查阅了出版于1789-1791年间的1114种政治性小册子,发现只有12种参考过《社会契约论》。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声称受到卢梭思想召唤和鼓舞的人(也许包括后来死在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都不曾直接受教于卢梭的政治学著作。学者在对当时法国民众知识水准进行调查后发现,民众的知识水准糟不可言,普通巴黎人的受教育程度也仅限于阅读通俗文学作品——当然包括《忏悔录》或《爱洛绮丝》(一名《朱丽》)。至于《社会契约论》,在多数读者眼里不啻为天书。
以社会契约论影响后世的卢梭,实际上是通过非凡的文学才能,打开成功之路的。在卢梭的巨大成功背后,有一条无心插柳的神秘甬道:用小说来征服女人,再经由女人主持的沙龙,影响法国、欧洲和全世界。因此,声称受到卢梭思想启蒙的民众,很可能只是受到了卢梭文学作品——包括卢梭极具明星效应的愤世嫉俗穿戴——的感染;他们深受感染之余,就爱上了卢梭。他们无需了解卢梭在其政治学著述中表达了哪些见解,只要有人将卢梭的思想提炼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口号或格言,民众就会群起信奉。民众的口味决定了如下事实:只有把思想制作成听上去感人,看上去美丽,闻起来可口的格言,他们就会认定其中包含至理。孟德斯鸠感叹道:“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
卢梭自己就提供过证明,早在他流亡之时,民众对他的爱戴就具备了这种兼含无知和狂热的特征:每天都有人不辞辛劳、路远迢迢地前来晋见,卢梭在与他们交流后发现,“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1法里约合4公里,以当年的交通路况,这类瞻仰迹近信徒长途朝圣。卢梭获得的成功曾是如此巨大,以至年届花甲时仍忘情地吹嘘道:“在社会上,则只有一个看法,特别是女人们,对该书(指《朱丽》)及其作者都如醉如痴,以致我敢说,如果我下手的话,即使在上层女人中,也很少有不被我俘虏的。”
卢梭的经历告诉我们,哲学家的思想以绮丽的方式得到普罗大众的接受,就会轻而言之变成闹剧,大而言之变成灾难。
三
通常,我无意聚焦作者的个性人品,摘引蠢行劣迹就像描绘殊方异闻,写作者不难把文章弄得饶有趣味,但那也可能是一种错觉式趣味,纸上八卦横飞,说服力却并未同步增长。
因为,就有些作者来说,人品与文品可能奉行双轨制,人品之劣无损文质之优,培根即是一例。倘笔墨集矢于对方人品,反而误了我们欣赏杰作,得不偿失。有些高贵入骨的作者,会懒得展示人品,除非是负面的,如查尔斯·兰姆,他的自嘲热情比谁都高。记得赫兹里特写过兰姆的一个特点:如果有人嘲笑兰姆,他会当场配合,努力做出一副使该嘲笑得以成立的表情,不负对方挖苦之诚。
我们还能见到互补制,钱钟书摘引过一位法国妇人的妙语:“吾行为所损负于道德者,吾以言论补偿之,”人品上的卑鄙龌龊恰恰构成文字上道德光芒熠熠闪烁的前提。譬诸今日,大贪官下台前总会说些掷地有声、可堪传颂的廉政语录,民众也见怪不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又自成一类,据说,他生活品行之恶劣,远在他笔下所有可憎汉之上,但当他执笔时,他把自己客体化了,他冷静地挖掘、汲取、分析自身的种种卑劣,将充满不良品行的自我,改造成一座性格矿藏,供他写出让人哄笑、引人反思的种种滑稽人物。对这类作家,仅仅谴责他的生活举止,就过于迂阔了,相反,我们很可能愿意他(当然是怯生生地、私下地)继续混帐下去,只要伟大作品能构成回报。元好问所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确为妙谛真言。
但卢梭有所不同。他未必是哲学家里性格最古怪的,却是最擅长替自己辩护的。如果卢梭做过些令人不齿的事情,他会以“忏悔”的名义加以回护;如果这类事情过度不堪,寻常的忏悔都不能指望读者原谅,他就大刀阔斧、迎难而上,最终把这份不堪上升到哲学高度,好像他是出于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责任感,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比如,卢梭对于自己将五个孩子全部送进育婴堂且从此不加过问的行为,就有过既精致又无畏的辩护。他一个与之配套的能耐是,再无耻的事,都能用一种诚恳语调出之,仿佛作为加害者的他,原是更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兹举一例,以明其余。在《忏悔录》里,卢梭写下的第一桩够分量的忏悔,是诬陷女佣玛丽翁。事情是这样的:卢梭在拉罗克伯爵家偷了一条丝带,被人拿获后慌了手脚,遂一口咬定是玛丽翁偷的。卢梭承认,“玛丽翁不仅漂亮,而且有着一种只有山里人才有的健康肤色,特别是她态度谦虚、温柔,人见人爱。此外,她还是一位乖巧、绝对忠实的好姑娘。”卢梭栽赃成功,意味着在那个注重信誉、讲究贞洁的地区,玛丽翁这辈子就毁掉了。既如此,卢梭为啥要这么干呢?他提供了一条只有卢梭才说得出口的理由:因为友情,因为爱。卢梭说:
在那残忍的时刻,我并没有害她之心。当我诬告那个可怜的姑娘时,我是出于对她的友情……我把自己想干的事嫁祸于她,说她把丝带送了我,因为我心里是想送给她的。
这实在是个叫人崩溃的借口,如果“友情”可以直通最凶恶的伤害,“仇恨”或“报复”等词又有什么用呢?它们难道是“友情”的同义词?
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卢梭的不少忏悔,每有类似特征。深研过卢梭思想的学者,对卢梭的思辨能力多有所鄙夷,阿克顿勋爵和约翰·密尔几乎说过相同的话,均强调卢梭的推理具有似是而非的特征。实际上,卢梭的推理首先不是符合逻辑或常识的需要,而是用来张扬自我。
文贵有我,理尚无我,这是一个宝贵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界线。高扬自我的写作手法对于文学家多有益,对知识分子就多有害。尼采说过,“每种伟大的哲学都是它的创立者的自白,一种秘密的,不情愿的个人传记。”这也许是一个事实,但如果你在表达思想,更值得听取的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里对培根《伟大的复兴》里的一段话作出的回应:“让我们对自己保持沉默。”所有的观点都难免主观是一回事,竭力使思想或观点摆脱主观,用无所畏惧的客观性来夯实论据,又是一回事。
卢梭的非凡成功,几乎都是在践踏该原则时所取得的。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普遍没有读过卢梭的学术著作,又大多读过卢梭的文学作品,风闻过卢梭的言谈举止,因此,卢梭不是凭借思想,而是凭借那些不乏虚构的情怀和一枝超凡的文士妙笔,催眠了后人。后人自以为在追随一种思想,其实只是在追随一个妙人儿,一个幻术家。后人的误读成就了卢梭,而对卢梭来说,有些误读甚至是他特意营造的。他在这方面倒有着难得的坦率,他说:
要想让人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因此,我便采取了人们不容许我遵循的离奇做法,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这么标新立异。我这么做起先让我成为笑柄,但要是我持之以恒的话,势必会使我受人尊敬的。
当他发现外界流传一个谣言时(女性读者误以为卢梭就是小说《爱洛绮丝》中的主人公),他展示了一种与思想家无涉的精明,表示“我既不想证实也不想批驳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想法”。因为,他说,“要是真的做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声明,那就愚蠢多于坦诚了。”可见,虽然身为思想家,在卢梭的价值序列里,坦诚仍非要紧之物,只要有利于维持别人对他的“尊敬”,凡事皆可另行斟酌。
人们很容易发现,卢梭的“忏悔”往往构成一种交易,由于“忏悔”在先,他认定自己拥有了谴责他人的特权,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他人,于是,写着写着,“我忏悔”就曲径通幽地过渡到“我控诉”。但参照他的“契约”说,这份交易并不存在,也绝不符合“契约”精神。“忏悔”就像自我批评,不会也不应给“批评”增加额外效力,在两者中强行建立关联,只会使“忏悔”变成一种机心深重的权谋,好像那是一种苦肉计,醉翁之意乃是狠踹对方裤裆。
下回,我们将结合更多例子,来探究魅惑者卢梭笔下的难言之隐。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