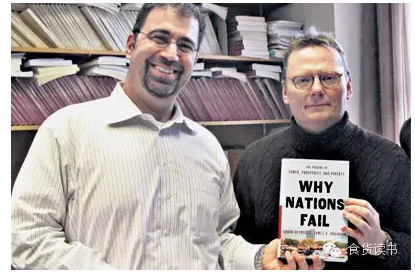一些国家长期繁荣,是因为这些社会在某个历史时间建立和巩固了包容性制度。一些国家陷入长期落后之中,是因为权贵要么不惜代价死守权力,要么以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拼命维持汲取性制度以便中饱私囊。
本文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读书笔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部书虽然不是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但读起来却感到“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
经济学(economics)以前叫“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但其实“政治经济学”重经济,轻政治,政治与经济间的关系写得含混不清;前苏联的教科书也有叫“政治经济学”的,不过那几乎全是政治教导,经济学内容看不见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奇才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科学系、经济系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2012年合著新书《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Crown Business,2012),讨论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即为什么全球化时代仍然有那么多国家陷于贫穷,而有些国家却非常富有。

对于这个主题,学界内外当然已经有不少意见。比如生物学家戴蒙德写了《枪炮、病菌和钢铁》,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早期文明在哪里繁荣,早期文明的繁荣又决定了现在哪些地方发达。还比如,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禁欲、节俭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有人踵武前贤,照猫画虎说东亚高速增长是儒家文化的胜利。这类解释其实并不成功。比如,16世纪初的富裕国家,现在却已经相对贫困落后,地理决定论如何能说明这种逆转呢?还比如,中国一直有中国文化,但100年前发展一个样,50年前另一个样,现在又是一个样,这靠中国文化很难解说清楚。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对于经典问题的回答方式,是遵循经济学的严格逻辑给出了替代性的制度解释。借助一个简明的制度分析框架,深入讨论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他们的回答方式与古典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而绝没有“不讲政治”或“没有经济学”的弊病。
按照宏观经济学传统,增长的来源可以分解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技术创新等因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些来源对于国家走向富裕非常重要,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怎样通过适当的制度框架得到这些增长因素。他们称激励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如保护私人产权、鼓励平等竞争、竞争性价格机制)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包容性制度相对的,是主要服务于少数权贵利益的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在权贵将有利于自己、但不利于社会的制度和政策强加于整个社会时,繁荣就会转化为经济的停滞或发展的逆转。沿着这样的思路,两位作者将国富国贫问题转化为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问题。在他们眼中,一些国家长期繁荣,是因为这些社会在某个历史时间建立和巩固了包容性制度。一些国家陷入长期落后之中,是因为权贵要么不惜代价死守权力,要么以社会其他人为代价,拼命维持汲取性制度以便中饱私囊。
话说到这里,就要介绍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很在意的经济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和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两个维度了。在他们看来, “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富裕或贫穷的关键,反过来,政治制度又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上面提到的保护产权、平等竞争等等,都属于经济制度,这类直接激励经济主体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是贫富的关键。
但经济制度又是如何而来的呢?最简单的说,经济制度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如果政治权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多元的利益集团手中,不管这个利益集团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还是资产阶级利益,或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利益,围绕经济制度的决策结果通常是有利于维持和服务该集团的利益。比如,俄罗斯改革过程中,在政治权力相当集中的条件下,少数权贵将私有化方案强加于社会。结果俄罗斯引进的市场只是表象,真正得到的是一种寡头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财产和收入分配建立在谁知道哪些国家资产可以低价出售以及谁拥有排除其他竞争者的更强能力基础上,那些与政权联系密切的人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了巨额财富。
反过来说,当汲取性经济制度不断制造悬殊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扩展权贵的财富时,权贵为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所能调动的资源也就更多,他们丧失政治权力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不顾一切维护权力的激励也就更为强大。所以,一旦权贵积累起巨额财富,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也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他们试图设置准入障碍来阻止别人一起竞争,还试图侵占民众积累起来的财富。如果这些都可以通过政治过程实现,即使已经建立局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也很容易向汲取性制度方向蜕化。
那么,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巩固包容性经济制度、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足够的集中;二是足够的多元(sufficiently centralized and pluralistic)。其中“足够的集中”条件,沿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意见。韦伯曾将国家定义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如果没有这种合法暴力垄断,国家无法发挥实施法律和秩序中的作用,比如索马里的政治权力分布于相互敌对的部族手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威能够控制或制裁某个部族去做什么事,这样就无法支持贸易甚至公民的基本安全。“足够的多元”条件可以理解为“民主条件”,它要求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比较广泛,而不是控制在单个个人或小集团手中,同时权力的运用受到约束。这类政治制度可以避免经济制度的变革沿着巩固权贵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的方向前进。如果政治制度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他们就称其为包容性政治制度;而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就都属于所谓的汲取性政治制度 。
制度漂变、紧要关头和制度分流
既然汲取性制度有利于权贵而不利于社会,包容性制度怎么可能产生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引入了制度漂变(institutional drift)、紧要关头(critical junctures)和制度分流(institutional divergence)概念。
所谓紧要关头,专指打破了既有政治经济平衡的重大事件。如黑死病、大西洋贸易或工业革命,都曾经发挥打破欧洲甚至世界既有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因而都属于紧要关头。
所谓制度漂变,指相似的制度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看起来不那么明显的次要变化。
当紧要关头与制度漂变的相互作用时,制度变革的方向就会出现分流。比如,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各国,城市和农村数百万人死于这场瘟疫。这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西欧(包括英国在内)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庄园制因之动摇,城市劳动者的地位得以上升;而东欧却与此相反,农奴的地位大为恶化,走上了二次农奴制的道路。再比如,黑死病之后,欧洲大西洋航线开辟出来,英国、西班牙等国家都从远洋贸易中收获甚丰,但西班牙从远洋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王室,结果贸易发展巩固了西班牙专制制度;而英国反对王室的群体也从大西洋贸易中获益,结果贸易过程也成为包容性制度的促进过程。1688 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发展出宪政政治,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代表多元利益的议会,进而衍生出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离,政党不再从事营利性活动,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也不再需要国家特许。这些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制度激励了民间创业和创新活动,最终使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
在解释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形成和分流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教授援引了大量世界历史上的制度漂变和制度分流案例,这些案例涵盖了五大洲有代表性的经济体。由于这些案例组织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既简练清晰,又因为取材广泛和背景宏大显得生气勃勃。我想,这是为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等媒体和包括五位在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者不吝辞句,赞扬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这部书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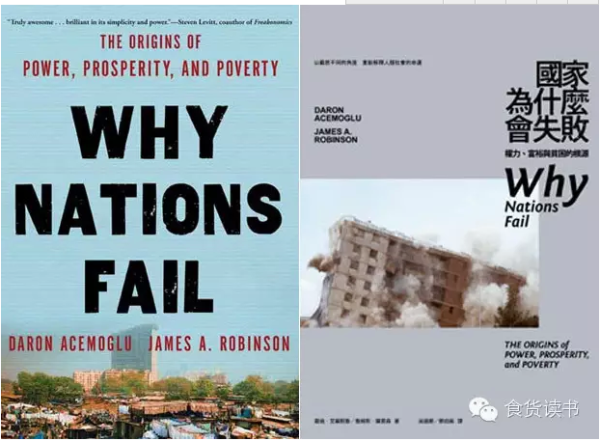
中国会迈向包容性制度吗?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部书虽然不是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但读起来却感到“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作者说经济制度变革是政治决定过程。回顾改革史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个重大进步(还有挫折)都与政治决策紧密联系。有时政治决策代表了广泛的社会利益,此时经济改革会得到重要推动。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都是经济改革的重大进步,也是政治决策的辉煌业绩,所以党史书上也不吝词句。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有的时候,政治决策未必反映社会的诉求,此时经济改革就不像听上去那么美妙。如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内部人控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国有经济进退维谷,也就始终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公共问题。
作者还说,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局部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也可能蜕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确实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走走停停,有的年份更是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情况。
作者说,在权贵的经济利益大为扩张时,他们就有更大的能力来调动资源维护汲取性制度。2005年后的国进民退潮流确实造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政治经济改革的重大障碍。
作者说,汲取性制度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条件下可以各种名义改头换面生存下来,我们也在改革过程中看到大量以改革旗号或爱国旗号扩展自己利益的行为。
如果借助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框架,观察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我想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是政治改革不深化,经济改革也无法完成。只有从威权发展迈向民主发展、法治发展,以多元化、相互制衡的方式分配政治权力,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可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二是经济改革过程必须服务于多元的社会利益。如果违反这一点,任何经济改革旗号都可能被内部人劫持。其实公众对这一点已经啧有烦言了。
来源:食货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