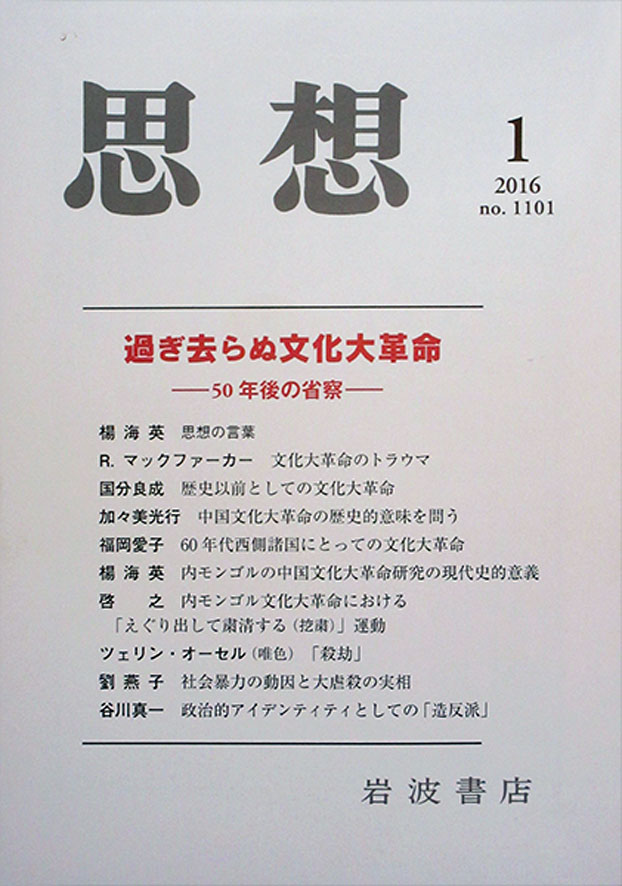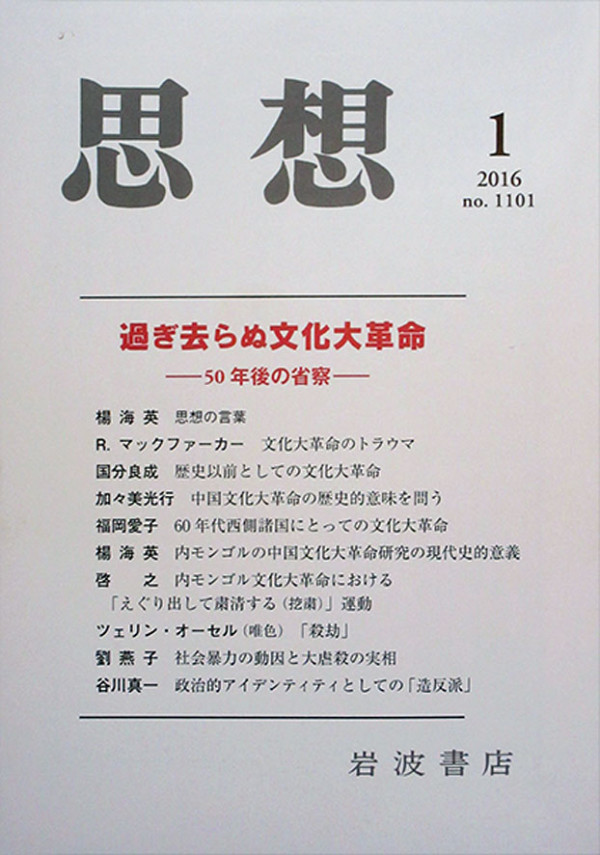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七)、大开杀戒
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领导尼木民众以暴抗暴的“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著名的“反动分子”,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在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被示众批斗,随后与17名藏人被押往南郊流沙河的刑场枪决。
一位在西藏当过解放军军人、后来任职厅局级的汉人,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站在被公审的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楚地看见:“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
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遭严惩。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与他的女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回忆说:“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曾与中共合作而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虚职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文革时被当作“牛鬼蛇神”遭游街批斗,没收财产。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被控“叛国”而遭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他的两个同伴也被枪毙,另一个女孩被判刑二十年。据说他在被处决之前已被打死,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名为“拉萨人民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的枪声中,一个个“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造总”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参与调查“边坝事件”的普卜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一百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九十多人”。
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八)、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翻身农奴”的“三座大山”,那么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解放军既然是解放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十世班禅喇嘛生前就曾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前面说过,我在采访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时,她坚决否认这些事件是派性之间的斗争。她说:“自治区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1968年7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解放军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反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点燃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当年“宁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的是,曾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六•七大昭寺事件”、“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沉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四十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的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一人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书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完)
写于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再改于2015年6月,北京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