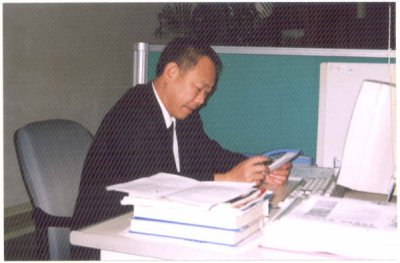他是中共抗日烈士身后留下的孤儿,所谓根正苗红,却在共产党中国却被打为右派,沦入社会底层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是一个天性善良、正直的人,一生不肯违背良心为人行事,却从肉体到精神遭遇了数说不尽的出卖、欺骗、坑害与摧残;他是一个出色的技术人才,本该学有所用大显身手成就一番事业,却被迫在完全不需要知识、更多的时候只需要顽强的求生意志的恶劣环境中,挣扎沉浮度过几十年时光;他从年轻时就怀着远大而热烈的人生理想,渴望加入中共,成为其中的一员,但直到快要退休前夕,才稀里糊涂流着眼泪反而成为民建党员;他是共产党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高级气象专家,可以预报大气空间的风云变化阴晴圆缺,却对近在身边的社会气候茫然不知,以至于反复遭遇来自社会气候的风霜雨雪饱受摧残;甚至连病魔这时也不肯放过他,就在他被打入社会最底层勉强苟活的岁月,癌细胞也趁火打劫光顾他的身体,医生已给他判处了“缓期5年执行”的死刑,但几年后他再去医院时医生也不得不惊奇的大叫一声:快来看,这个人还活着;连续经历异常惨淡的人生噩梦,甚至数度求生无望,在迟暮之年却意外得到新生,勉强学有所用,可以安享晚年……这就是陈金陵先生70年的荒诞人生,也是他通过这本20万字的《风雨苍黄70年》所讲述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总喜欢以小见大,把个人的命运解读为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把个人的历史升华为整个民族的历史,好像非此不能找到某一生命个体真正的人生价值。但在我看来,一切价值落到实处都是具体的个人的价值,如果某种价值最后不能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体现出来,那一定是“伪价值”。同样的道理,所谓民族的苦难,其实也是个人的苦难,所谓时代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我认为一个人在历史中特有的遭遇,既不必要升华为民族的价值或苦难,也不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而消失无踪。说到底,所谓民族灾难也好,时代悲剧也罢,它并不是由一个抽象的民族载体或无形的时间外壳来承受的,拷打、折磨、摧残、迫害、诬陷、审讯、刑罚……一切苦难总是由具体的人施加的,也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人的肉身来承受了。无论多大的历史悲剧,都是由具体的事件组成的,往来穿梭在事件中的,总是具体的个人。事过境迁,如果灾难亲历者本人把悲剧定义为时代性的,那这种“移情”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使任何惨绝人寰的苦难回想起来都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但事件以外的人如果也这样为灾难定义,那这种“移情”则是对灾难亲历者的冒犯与轻辱,是对历史罪恶的开脱与掩饰。
一切罪恶的背后都有具体的作恶者,一切罪恶之下也都有具体的受害者。比如陈金陵先生在被打为右派分子时,就有一个卑劣的告密者,把他私下所说的话反映上去;与告密者相伴随的,也有心怀鬼胎的倾听者、记录者;在把他正式确定为右派分子时,有具体的会议主持者、发言表态者;在此后的漫长右派生涯中,总有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对他实施惩罚与迫害……这些人并不是无辜的,所谓历史,其实就是这些具体的人的活动、言论、动机的总和。再如1946年山西土改中,12岁的学生陈金陵与作为烈士遗孀的母亲被惨无人道的关押、殴打,直到年轻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使他沦为孤儿,其过程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实施的,在实施者的背后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动机与欲望,甚至在实施时,他或她有丰富的面部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鲜活传神的方言土语……而这就是历史。其实历史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正如陈金陵先生记录1946年山西土改时所写的:“第三天就是轮流斗争了,对于每家的内容都一样:要跑了的人、要东西。打的方式也差不多,棍棒、拆了把的竹扫帚等等。打人的重点也因人而异,打我们最凶的是我成林表爷爷,他是我爷爷三舅家的小子,是他表弟,我三老老舅是我爷爷的三舅,因主持给我们分家时和我爷爷结的怨,所以才找到这个机会在他重外甥媳妇和重重外甥身上泄愤。还有就是我姑陈春仙、二姑陈改仙和我二奶,打我妈都打的很凶,我二姑打我打的凶。同学李长清、房后李菊香打我们都打的很凶,还有我堂弟小金荣,打我打的也很凶。第一次挨打就是李长清狠狠的打了我一顿,还抢走了我妈在城里给我买的一顶棉帽子。农会主席李太宏打人也打的很凶,还有杜旭林、杜可观,凡是被斗争的人都挨过他们狠狠的打……打我碾管老老妗最凶的是她侄女王小梅和侄子王道武,他们俩苦苦的打她,几乎是场场不拉……老老妗哭着和我妈说:我平时对这两个孩子也不赖,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不成想怎么恨成我这样。道修他叔王马成跳着脚骂,说:王碾管要敢回来,不用你们动手,我就绑上他交到农会来,让你们把他处死!……对我和我妈的斗争也升了级,先是钉竹签子。竹筷子削尖的竹签子,从我妈的指甲钉进去,十个手指十个竹签子;我是成林表爷给我钉的,也是十个,只是从指甲旁边的肉钉进去的,比我妈疼的轻些。……下一次斗争又换了花样,把手指绑上,往手指间钉子弹,一只手钉三个,一双手钉六个。给我妈钉的是杜旭林、李太宏,给我钉的是王成林。这回我妈又交出了我姥姥家放在我家的一部分衣物。农会干部们更兴奋了。下一回审我们就是烧红的烙铁烫了:把我和我妈一人绑一个凳子,面朝下、背朝上,烙铁一过,衣服着火、皮肉冒烟,问还有什么东西没交出来,先烙我后烙我妈。啥也没有问出来。审过两次后我们的背上、两肋、胳膊、小肚子上、大腿上皮肉都烂了,化了脓,双手也化了脓,晚上睡觉只能是弯腰爬着或靠着我妈靠一靠。根本不让家里人送被褥,天寒地冻,冷的人也睡不着,就这么硬撑着等死。李金汉奶奶、李化龙奶奶年纪大了,打过几次后就病了,又打过几次后就起不来身了,不几天就死在了牢房里,拖出去埋了。杜义孩爷爷的审讯则是把烧红的火炭放在他扎上腰带的棉袄里,脊背烧烂了,衣服也烧烂了。他是残废人,是唯一没有跑脱的”九代表“,王秀甫怎么能饶了他?对他也不是要东西,就是折磨他,扎竹签子他也扎了,钉子弹壳也钉了,他很快就发烧昏迷。后来他受刑不过,拿烂布条搓了根绳子,在很低的位置上,自己把自己勒死了。等发现人已经硬了。这个牢房我们在时死了三个人……”
往事并不如烟,从我引用的这一段原作文字,读者可以清晰看到60年前山西农村土改时的凶残与血腥。从作者严格、准确的记事中,读者还可以发现,罪恶并不是抽象空洞的存在物,它非常具体,具体到每一个局部的纹络都是那么清晰,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父老乡亲、它甚至就是作者的“二姑陈改仙”、“堂弟小金荣”、或者“成林爷爷”。把个人亲自经历的苦难故意升华到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非但不能以小见大,反而具有放大、稀释、消融苦难的作用,就像从哈哈镜中看那些拉长、放大、变形的身影,让人失去客观判别、辨认、识记的眼光,在客观上为苦难障目,为罪恶开脱。坚持一切苦难都是个人的苦难的立场,才能使所经历的苦难呈现出它实际为祸时的狰狞面目,才能既不夸大也不掩饰,才能使后人对苦难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也才能张显苦难的历史价值,一句话,才能使苦难成为苦难本身。
可贵的是,陈金陵先生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这本人生自述中,没有落入中国知识分子最熟悉的集体无意识中去,他用自己虽然缺少华丽的文字技巧、但不失流畅和质朴的文笔,把个人历史记忆中的斑斑点点全部打捞、并真实呈现出来,客观记录了个人在历史灾难中的承受与体验,使我们有机会从常见的宏大历史叙述中跳出来,去感受通常被有意无意隐藏在宏观历史背后的、作为个人的真实苦难,感知来自个人心灵深处的丝丝颤栗,也让后人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些传说中的历史烟云。在文革四十年之际,我期待有更多的历史事件亲历者,能像陈金陵先生这样,以个案的形式记录个人亲历的苦难与罪恶,为后人留一份难得的活的历史标本,帮助后人以感性的方式,记住那些本来不该遗忘的历史。
陈金陵先生所著的《风雨苍黄70年》即将出版,受其女儿陈静嘱托,将我的读后感写成以上文字,是为序言。
20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