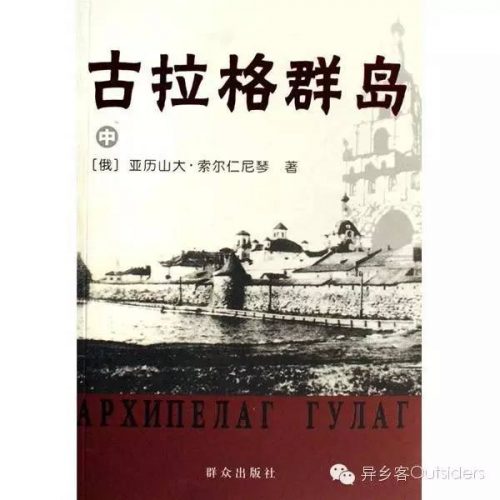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个苏联红军大尉军官,在挺进柏林的前线战壕,被苏军集团军政治部口头宣布“反革命罪”,判刑11年,送进劳改营,刑满后接着被流放。他仅仅因为在前线给同学写信,发发牢骚而已。“契卡-克格勃”(见原着,苏联肃反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称)在例行邮件检查中,发现了他写的可疑信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不能见容私下的牢骚和抱怨,斯大林将希特勒赶离莫斯科城下,国家主权如果不能维护个体生命的自由,它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古拉格群岛》通过对5500万(1917年——1959年,除战争死亡者,只含饥饿、监狱死亡者)苏联平民、军人、教师、科学家、教授、农民、学生、少数族裔等所有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者苦难历程的真实记述,犹如手术刀解剖血淋淋的尸体,完美的社会主义体制外表下,罪恶、肮脏、饥饿、苦役、死亡隐藏在光鲜制度的躯体内。每个有幸读到此书的中国读者,都会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古拉格群岛》真实到读者怀疑其真实程度的本身。
一
那些苏俄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描画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非常美妙,但他们的笔下,不曾出现北极圈、西伯利亚数千万计的政治苦役犯饥寒交迫的身影,更别说替他们辩护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大加赞美,对暴君屠杀人民的视而不见,反衬了索尔仁尼琴边缘和独立化写作的不朽。今天世人对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不再是出于个人体验。制度惯性的消失,建立在新制度的破坏和打碎的力度下。地域上的局外人身份,让我们更能看清楚自己投射在自由的背影,是大或者小。我们共同生存在共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被同一个魔鬼控制,都是共产制度的殉葬品。
制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秩序形态,人性的被改造和顺从性有时超过制度本身所规范的。即使最恶的制度,人性都有承受的能力。制度不光关乎意识形态的拣选、教化和强制,它由此可以构成强势的制度改造力量,人民被制度绑架、裹挟,让人性堕落为兽性,制度呈现普遍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被强势力量左右的社会状态,哪怕血腥到极点,但同样被独裁制度披挂上道德的大旗。
恶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对政治、经济、行政、军队、司法等等资源的全面垄断作为法理性前提,独占话语权,禁锢民间自由思维,从而对个人洗脑。制度能够训育思维方式和生存习惯的唯一性。制度还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都能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人性的情欲和私利本能,为任何制度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反过来,制度恰恰迎合了人性某些层次的欲望。恶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本能的最大剥夺作为存在依据的;反之,好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最大保护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二十世纪,为最好制度和罪恶制度同时提供了舞台,自由、公平、宽容、福利和财富指数,可作为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当人民被自己国土上的统治者,当作畜生一样任意宰割的时候,国家主权一文不值。人民被当作暴力政权的敌人,爱不爱国,没有什么意义,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二
历史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制度更有相同的地方。历史可以重演,制度可以复制。历史不能跨越时空,制度却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真实再现,不论种族、年龄、肤色、国别、语言、信仰。比如文明的程度:偶然邂逅,善意会心的微笑、点头,对自由、人权的追逐;比如残暴的等级。人性恶不经受文明涤荡,历史就会重复。历史是人性内在的延伸。人性的善,会被强大的恐惧遮蔽。人性的恶,会被私欲和逃生的欲望激发。制度可以控制人性,常常为了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以善的名义从事恶行,让善恶颠倒,人性背离。
我们可以看看《古拉格群岛》提供的272名有名有姓无辜者其中三个案例:一个国营商店的女店员,无意间用有斯大林头像的报纸,包裹食品,被顾客告密,按照苏联刑法,得到一张“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进劳改营。一木工干活,顺手将外套搭在列宁的塑像上,被告发,得到“十元券”。一家国营工厂领导开会宣布斯大林的一个讲话,宣读完毕,会场全体领导和工人起立,鼓掌。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了……大家仍然拼命拍打两个巴掌。竟然无人敢带头停止鼓掌,害怕被戴上对领袖不忠的罪名。每个人体力难支,面带微笑。终于,一个老工人第一个停下来,大家马上停止鼓掌,长叹一声。老工人被举报,得到一张“十五元券”。
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出卖与被出卖,监禁与被监禁,屠杀与被屠杀,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强大到让罪犯感到自己真有犯罪耻辱的地步,人的尊严、反抗意识,统统都变为毫无底线的顺从。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专政的对象竟然全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个人迷信更给独裁者斯大林增添了唯我独尊的兽欲,他可以随心所欲把任何一个将领、学者、科学家投进“群岛”的矿坑、伐木场、运河工地、北极区,任其虐毙。
三
暴力革命的本质是夺取政权,为己私欲,不是为民造福。通过蛊惑、煽动共产主义的美妙未来,完成社会动员。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并且这个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上,独裁专制便这样产生了。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其执政的合法性连执政者自己都内心不安。恐惧——害怕丧失权力得到清算,领袖和他那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党,所占据的权力资源,为他们支撑起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骄淫奢侈,掠夺财富,泽被子孙。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必然要不断地消灭潜在的敌人,甚至不惜扩大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些曾拥护并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都成为怀疑对象。革命的清算,不仅用在消灭国外敌人,还用在自己的权力对象身上。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晚上睡觉才可以安然入梦,不怕被人夺占皇位,推上断头台。任何美妙的暴力革命,都没有实质正义可言。成功的暴力革命,只是极少数人获得权力赋予的自由,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
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从“十月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起,就把劳改集中营在苏联广袤无际的土地上,像恶性毒瘤一样繁殖、复制。每四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被监禁、流放,整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制度。1980年代末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上帝终于让他们偿清了残暴和血腥的债务。《古拉格群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地打探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窥镜。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性扭曲和改造的强大力量,也同样相信民主制度对自由、人权尊重和保护更强盛的力量。中国远未出现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制度编年史巨着,它在中国大陆仍是一本“内部读物”。
2006年11月修定
首发议报第2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