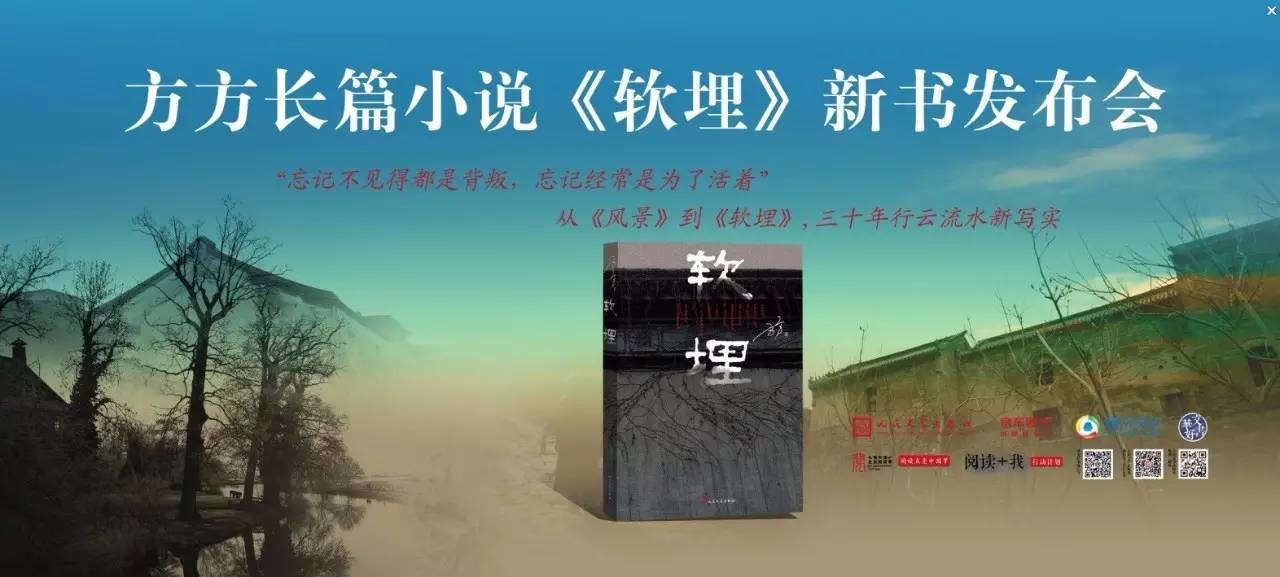第 一 章
1. 自己跟自己的斗争
这个女人一直在跟自己做斗争。
她已经很老了。所有皮肤都松软地趴着,连一条像样的皱纹都撑不起来。她的脸和脖子细痕密布。因肤色白皙,这些痕迹不像是时光之刀随意划下,而更像是一支细笔,一下一下描绘而出。她的眼睛也已浑浊不堪,但在蓦然睁大时,仍然能看到有光芒从中射出。
她经常盯着一处发呆,似乎若有所思,又似百般无聊。为此偶尔会有路人好奇,说:“太婆,你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她会露出一脸茫然,望着路人,喃喃说几句没人听得见的话。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在想。她只是觉得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拼命朝外跳,似乎在撩拨她的记忆。而那些,正是她一生都不愿意触碰的东西。她拼命抵抗。她的抵抗,有如一张大网,密不透风,仿佛笼罩和绑缚着一群随时奔突而出的魔鬼。她这一生,始终都拎着这张网,与它们搏斗。
丈夫活着时,曾经提议她不妨想一想,或许想出了什么,人就心安了。她愿意听从他的话,当真迫使自己静下心来,用劲回想。但几乎瞬间,浑身的烦躁如同无数钢针,迸射般地扎来,劲道凶猛,令她有五脏俱裂之感。此一时刻,她的痛,以及累,让她几乎无法喘息。
她绝望地对她的丈夫说:“你不要逼我。我不能想。我一想就觉得我该去死。”她的丈夫吓着了。沉默片刻,对她说:“那就不用再想了。尽量给自己找件事做,忙碌可以干扰思路。”
她依了丈夫的话去做,每天都忙忙碌碌。其实她也并没有什么事业,她的事业就是做家务。她每天都忙着擦洗打扫,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每一个去过她家的人,都会说,你家真是太干净了。她的丈夫是医生,也以此为傲。
如此,她的生活渐渐正常。
多少年了,她一直这样。每一年的时间,都如一张细密严实的膜,将她记忆背后的东西层层覆盖。一年一张,岁岁年年,由薄而厚,凝结成板,那些深藏在她意识里的魔鬼统统被封压了下去。
但那是些什么东西呢?她完全不知道。
她失忆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
很久很久以后的某天,她的丈夫从医院回来。他表情严肃,说“文化大革命”了,医院天天开会,也有人写了他的大字报,说他的历史有问题。她很紧张,不知道丈夫向她讲述这些意味着什么。但她的丈夫却突然说,你不会有事的,我会保护你。你过去的事,一辈子都不要想起来。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人,恐怕是那些你不记得的东西。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就行了。
她没有体会到这是丈夫的安慰和提醒,心里反倒是狠狠的一阵悸动。仿佛那些隐匿得几近消失的死敌,已然被她的丈夫所掌控。那到底是些什么呢?难道我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会知道?她想着时,甚至感觉到恐惧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份恐惧就在她的身边。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于是她明白,多年以来,这个她深爱的人也是她深怕的人。
为什么呢?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她很惶惑,也不明白。但这种感觉就是在。
2. 河流的声音
人们把她从湍急的河流里捞出时,她一丝不挂。从头到脚,浑身是伤。那是石头和激流相撞的结果。救她的人说,水把她泡得浑身发白,只剩头发是黑的,一下子都看不到伤在哪里。得幸有几个军医正在附近村庄出诊,他们直接把她送到了那里。急救之后,那几个医生迅速地把她带回了医院。
她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苏醒。当她清醒过来,试图回答人们的询问时,突然傻了眼。
你是哪里人?住在哪个村?你多大年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怎么掉进了河里?是翻船了,还是坏人把你扔下去的?就你一个落水的吗……人们交替着询问,即令声音温和,
也如一根根利刺扎过来,她的心瞬间剧痛无比。她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她想,是呀,我是哪里人呢?我住哪里呢?我叫什么呢?我怎么会掉进河里了?她完全没有了印象。我怎么会记不得呢?我怎么连自己都记不得了呢?于是她哭了起来。她说,我不记得。
她是真的不记得了。
于是人们说,你想想,仔细地想想。你是被人从河里捞出来的。你从河水开始想,也许能想起来。
她依着人们的要求,果然认真去回想。但她的思路一到河边,哗哗的水声便像炸雷一样轰响,莫名的恐惧随着水声汹涌而来。波涛中如同藏着魔鬼,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狠狠地袭击她的身心。她顿时失控,放声地痛哭以及尖叫,声音歇斯底里。
一位吴姓医生严厉制止了那些好奇的人。他说,她可能受了刺激。不要让她再想了,让她养病吧。
于是,人们不再追问,只是明里暗里都用怜惜的口吻谈着她。
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春天。
窗外的桃树满头缀着粉色花朵。院墙边的杏花也白成了一排,与白色的墙壁衬在一起,远了竟看不出花色。更远处,几株老银杏摇着碧绿的叶子,粗壮的树干已经猜不出它栽植于何年。更远更远,山的影子柔软地起伏着,轮廓像花瓣。院子角落的迎春花开得快要败了,那明亮的黄花却依然闪烁着明亮。五彩缤纷突然都进入她的眼里。回春中的鸟儿此刻似乎抖擞出精神,尽管风还有寒意,它们却在这轻微的寒意里兀自地唱。在这样的景致和这样的声音中,她慢慢地安静下来。
她人生新的记忆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是川东的一个小城。
后来,医院护士七嘴八舌向她讲述救治她的过程。她们说,吴医生他们带她回来时,大家都以为她活不出来的。又说,有一天至少三个医生认定她已经断了气,抬尸的人都被叫进了医院大门。多亏吴医生细心,看见她的中指动了一下,便坚持要求再留院观察。结果又过了几天,她醒了。在这样的讲述中,她记忆里储存了自己起死回生的经历。
这经历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医生,她的救命恩人。这一趟生死,和这样的一个人,都够她慢慢品味。虽然是很短的过程,但其中酸甜苦辣似乎都有。她想,她的人生只需要拿这个当开头就已足够。
这样子,她把自己失忆的东西,那些想起来就浑身有刺痛感的过去彻底放弃了。于是,她活到现在。
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这是吴医生跟她说过的话。
3. 她习惯独自待着
比起每天在公园跳舞和遛弯儿的那些老人家,时间对她下手似乎过于凶猛。她户口上的年龄显示着她七十出头——这是当年吴医生根据她的外貌估计出的岁数。而她的生日,则是她被人救起的日子。这也是吴医生信手填上的数字。之后它们便与她一生相随。
她看上去,似乎比同龄的太婆老出许多。照镜子时,她觉得是自己操劳所致。她从不参与跳舞,也不喜欢跟外人交往。她习惯独自待着,哪怕闲得冷清,她也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时有邻居大妈想要接近她,主动上门约她一起出去走走,说健身才能长寿哩。她还是不去。
她不是不想长寿,只是觉得自己心重。重得她不愿意起身,宁可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那里。于是每当阳光晴好时,她就会坐在花园山天主堂对面的台阶上。抬头望去,灰色的大楼就矗立在眼前,“天主堂”三个大字,虽被阳光照着,但她却看不到它的明亮。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亲眼看着它一天天颓败,又亲眼看着它一天天好起来,再又看着它一天天颓败的。她想这很有意思。以前她丈夫喜欢拖她出来散步,他们经常走这条路,然后从这里拐去昙华林。
散步路上,丈夫经常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给她听。有关这个“天主堂”的故事,她丈夫是这样说的,他说当年大清朝廷并不愿意在中国修教堂,可洋人们很想修,他们大老远来这里就是为了修教堂的。正急得没办法时,一个中国人替他们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们申请时就说要修一座“大王堂”,批准后,你在“大”字上加一横,在“王”字上加一点,就成“天主堂”了。洋人一听,这主意好,于是就这样写了申请。朝廷一看不是修教堂,立马就批了。批文下来,洋人就在“大”上加了一横,又在“王”上加了一点,改成了“天主堂”。地方官员过来查看,可是申请上写的就是“天主堂”,印鉴也有。官员不知道咋回事,就由他去了。反正他们被骗的事太多,也不在乎多这一件。
她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听时笑了。
只是现在,她坐在那里,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而是她喜欢看院子里的一丛绿树环绕着的圣母山。山坳处站立着露德圣母,她的脸上永远浮着一层纯洁和安详的笑意。每一次散步,他们都会过来看她,会在她的面前站一会儿。第一次来时,她曾经问:“她是谁?”丈夫说,当年,人们也问过圣母:“你是谁?”圣母说:“我是无染原罪者。”她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丈夫便在她手心里写出了这几个字。她问:“什么意思?”丈夫说:“就是说,没有原罪。”
她没有听懂,心里却狠狠地咚了一下。离开教堂,在路上缓缓散步时,她丈夫才继续说:“这是我们两个都要记住的,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无染原罪者。你和我。”
她还是没懂。最后丈夫说:“你记住她是露德圣母就好。她能让你内心平静。”
她到现在也没有明白丈夫的话意思是什么。但从此她只要看到露德圣母像,心里果然有了一份安静,甚至通体都格外的舒服。但是,她想,什么是无染原罪者呢?
街边一只麻色猫,生一副鬼灵精怪的脸,她坐在这里时,它经常一声不吭地蹲在她的脚边。它喜欢睁大眼睛望着她,有时还会伸出爪子扒拉她,一副似乎让她熟悉不过的眼神。她经常会伸出手,在它的背上抚摸几下,让它安静。有一天,它不在。她到处张望着,脱口而叫:“麻雀!麻雀!你在哪里?”麻色猫居然就跑了过来。她坐下时心想,我为什么会叫它麻雀呢?
现在,她就坐在街边的阳光下。她的脚边摆着一张藤箩,藤箩里面平摊着一些鞋垫,上面绣着鸳鸯或是荷花。那都是她亲手绣制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绣这些东西,也没有印象自己学过。但她拿起一只鞋垫,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她曾经在一位马姓教授家里当保姆。有一年冬天,马教授夫人给了她一双旧棉鞋。她嫌太大,便给自己做了双鞋垫。似乎想都没有想,也没有描线,她顺手就在鞋垫上绣了一朵海棠。马教授夫人拿着鞋垫横看竖看,然后说:“你手好巧。以前学过?很有艺术感觉呀。”
马教授夫人的话并未让她高兴,反倒如石头砸着了她,忽地就惊了她的心。她感到了恐惧,一种没来由的恐惧。仿佛所有她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危险存在。一切陌生的面孔或是声音,都让她战栗。如此这般,长达数月。此后她就再也不动针线。她在马教授家当保姆很多年,直到马教授夫人去世。马教授另娶年轻太太,她也就被儿子接回了家。
她的儿子叫青林。
4. 有些东西与她不弃不离
她和青林原本住在武昌昙华林的一条窄巷里。这是公租房,是她丈夫活着时公家分派的。他们在此已经住了很多年。她的丈夫就是当年在乡村出诊时救下她的那个吴医生。她很爱他。因为他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救命恩人。她获救醒来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医生。他也是她新记忆中储存的第一人。
她常常想,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他的呢?是第一眼见到他时,还是那次去他的办公室?她已经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去吴医生的办公室。她只记得,桌上有一本《红楼梦》,她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翻看。嘴里不禁喃喃地念出“黛玉”,这两个字让她心里一阵恐慌。正这时,吴医生从门外进来,见她翻书,脸上露出惊讶神情。然后他从她手上拿下书,凝视着她,似乎犹豫了几秒,方说:“不要让人知道你识字,这或许对你有好处。”她有些茫然地望着他。他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有人多疑。你来历不明,很容易让人猜想。明白吗?”
她不太明白,却记住了他的话。因为,她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恐慌立即消失,替代的是几丝温暖。
几天之后,吴医生介绍她去军分区刘政委家当保姆。刘政委是老革命,他的妻子也是干部。他送她到大路口,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去他们家做事,生活得会简单些,对你的一生可能有好处。”她再一次感觉到心头一暖,突然间有所领悟,觉得吴医生的话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只是这份重要中,又有一点令她害怕的内容。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爱情。
好多年过去了,她一直都记着这个人和他的声音。随着刘政委的升迁和调动,她跟着他们全家来到武汉。大家叫刘政委的夫人彭姐,她也这样叫。彭姐待她不错,说她是家里请过的最好的保姆。她为刘家带孩子煮饭做卫生,过着一种水波不兴的生活,朴素而安宁。她从未想过换工作,也从未想过换地方,甚至从未想过嫁人。他们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一辈子如此而已。
有一年,吴医生转业到地方,专程去看望他的老领导。他很惊喜地见到了她,不由脱口问道:“你一直在这儿?你过得还好吗?”
她很激动,不知道这激动缘何而来。她的声音在颤抖,她说:“很好。因为你,才过得这样好。”他深深地望了她一眼。她从他的这一眼中看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别人所不知的秘密。她并不知这秘密是什么,只是她的心蓦然间惊跳了一下。
那天,吴医生在刘政委家吃饭,桌上摆着她精心做的菜。饭间闲谈时,方知他的妻子已经病故。他的妻子小严与彭姐有着很特殊的关系,当年她们曾经同生共死,所以彭姐当即放下筷子抹起了眼泪。站在一边的她听罢心里扑通了一下。
刘政委叹息半天,然后问:“你现在呢?一个人?”
他说:“是的,一个人。”
刘政委说:“不再找一个?”
他说:“也有人介绍过,但没有合适的。”
刘政委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过呀?”他说话时,目光正好落在她身上,便不由把手一指,说:“不如我来保个大媒?你们也都是老熟人了,年龄也算相当。”
吴医生的目光顺着刘政委的手指转向了她。她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却望着她笑了笑。从那份笑容里她看出,他是欢喜的。
于是那一年,她离开了刘政委的家。刘家三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他们一齐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望着她的背影,最小的那个还抹了眼泪。
她没有回头,挽着吴医生的胳膊,走进了他的家门。进门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愿意娶我呢?”
他笑了笑,说:“你如果嫁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哩。”
她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外音,又似乎不太明白。自己想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回应了一句:“是的,我也不放心我嫁给别人。”
话一说完,她心里开始生出莫名的害怕。夜色降临,天光由灰至黑,她害怕的感觉随黑暗的浓度增加而更加强烈。她甚至不知自己害怕什么,但她就是害怕。当吴医生搂着她,身体与她贴紧时,她几乎浑身哆嗦。吴医生一边安抚她一边低语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明白。我明白。你不要怕,没有关系。”
在他的怀里,她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什么?明白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关系?”
这天夜里她做了噩梦。这梦凶恶到她把自己吓醒。早上起床,吴医生望着她说:“你不要太紧张。不要多想。我会护着你。我娶你回家,是因为我知道你被救起的过程。这世上只有我能体会你的感受。你什么都不用怕。”
这番话当时便让她热泪涔涔,情不自禁地扑到他的怀里。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背后仿佛藏有一根细细的刺,尖锐并且灌满毒汁。它一直近距离跟随着她,她下意识地生出提防之心,生恐有一天这根毒刺会扎着自己。
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婚后的生活,温暖亦幸福,虽有一份忐忑不安始终与她同行,但毕竟她不再当用人,而是一个男人堂堂正正的妻子。这个身份令她感到满足。
她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维持着日常。每天,她早起为丈夫做早餐,看着他出门上班;中午他下班时,饭已上桌;待他午休后再上班时,她又开始慢慢地做晚餐,然后等着他回家。她细心地服侍他,为他做所有的小事。她的心中渐渐多了欣喜,这份欣喜,努力地排斥着她的不安。她想,或许我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她很快怀孕了。吴医生兴高采烈。她心里亦觉兴奋。但是,每当她一个人独处时,莫名的恐惧又卷土重来。它隔三岔五地袭击她,就仿佛当年河流中的魔鬼,又悄然来此潜伏。它们在等待时机,随时给她致命一击。那段日子,她的恐惧感几乎到了无法抗拒的地步。她看墙,觉得墙后有东西;看云,觉得云上有东西;看树,觉得树叶片中藏有东西;看灯,觉得灯一关,就会有东西出现。蓦然的声音会让她心惊,突显的色彩也让她心惊,家里来陌生人会让她心惊,四周寂然无声更是让她心惊。她也不知道这惊恐的原因何在。但她明白的是,那些东西始终与她不离不弃,仿佛与生俱来。
吴医生每天都带她去天主堂,站在露德圣母像面前,跟她说,你看着圣母的眼睛,圣母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担忧。你什么事都没有。
她被圣母的目光所感染,会有些许平静。但一回到家,一切复旧。无奈之下,吴医生只好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并且告诉医生她失忆的事。心理医生推测她的过去对她有巨大刺激。解铃还须系铃人,如能让她回想起来,或许能彻底解决问题。
但她的本能却抗拒回忆。因为她一旦开始回想,便有莫名的痛楚包裹她的全身,令她无法忍受。吴医生劝她说:“咬咬牙。如果想起来,可能你就心安了。”她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回答道:“如果想了起来,我的心更加不安呢?又该怎么办?”
吴医生听了她的话,几乎沉默一夜。她知道他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吴医生说,那就算了吧,彻底忘掉可能是你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在不断袭来的恐惧中,她生下了儿子。儿子出世的当天,她觉得那只潜伏的魔鬼就要出来了。它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她,使她不停地发抖。安抚她的护士都烦了,叫了吴医生过来。她躺上产床时,吴医生也被允许坐在她的身边。恍惚之中,她突然觉得那魔鬼正是吴医生本人,恐惧便愈发沉重。她对着吴医生尖叫道:“你出去!你滚开!”吴医生大声说:“你不要怕。我什么都可以接受,因为我的亲人只有你。我爱你。”而她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已经被魔鬼的目光笼罩。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声音响彻整个医院大楼。接生的大夫和助产护士都不解。一个护士说,你怎么回事,人家产妇都巴不得丈夫坐在身边哩。她喘息着,没有理睬她们。
在吴医生走出门的那一刻,他们的儿子平安诞生。
再次进到病房,吴医生很激动,两眼噙着泪。他抚着她的脸说:“儿子很漂亮,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家添了后代。你不要害怕。无论如何,你都不用害怕。”
她已经无力回话,吴医生又说:“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我娶你,就是要你这辈子能安心活着。有我,你就不必害怕。”
或许这个安慰特别有效,那只她以为随时会出来的魔鬼,一直没来。而儿子却一天一天地长大。他明亮的目光和天真的笑声,给她最大的安心。她本想再生个女儿,可惜在怀孕两个多月时,流产了。吴医生依然安慰她说,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儿子也行。只要他健康成长,一切都可满足。
时光漫漫,她惊恐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那只魔鬼似乎也在慢慢地老去。
5. 毒刺被拨走了
出现的却是另一桩令她始料未及的事:她的吴医生没有陪她走完人生。他死在出门办事的路上。
那一年,汉口一辆公共汽车被穿城而过的火车撞了个正着。一时间,路口血流成河。她的吴医生不幸也在车上。她闻讯拖着儿子青林转了几趟公交车,奔到现场。在一片杂乱的哭喊中,她看到凌乱的尸体和遍地的鲜血。她的脑袋嗡的一下,恍然间有同样场景浮在眼前。而那只老去的魔鬼,此刻似乎也弓起身体,要朝她扑来。她浑身战栗,两腿虚软,跪倒在地。
青林哭了起来,拼命地拉扯她:“妈!你站起来呀!你站起来!”
她惊遽般挺立起身,对着救护的人们嘶喊道:“不要软埋!我不要他软埋!”喊完,她觉得这世界哪里不对了。
青林紧紧拉着她的手,不明白她喊些什么。丧事办完后,他小心地问了一句:“妈妈,软埋是什么?”她不解地回复了一句:“软埋?什么软埋?”然后一派茫然。
这两个字,恍如天上飘浮着一般。隐约中,似与她贴身,但又似距她非常遥远。遥远中有个人在大声地说话,声音沉重而苍老。那声音只要在耳边一响,她便顿觉浑身刺疼,疼得她没有气力回答青林。
只几天,她的吴医生、青林的父亲.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被烧成灰,装进了一只瓷坛,埋到了山上。从此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只有墙上的一张照片。他微笑着,亲切地望着他们,就像他活着时一样。青林不在家时,她常常去擦拭照片,手抚着他的脸,喃喃自语。
有一天,她擦拭时,突然发现,一直藏在她身心里的恐惧,已然消失。那只潜伏并且老去的魔鬼,也被这个成天安慰她的男人带走了,他同时还拔掉了生活背后那支毒刺。仿佛吴医生的死有如风暴卷走了所有令她害怕的东西,海面安静如镜。从此她的生活面对的便是这开阔而平静的场景。
她显然惶惑了。不明白为什么爱她的并且她也爱的那个人走了,她的内心反而变得十分安详。
6. 她内心空旷得只有时间
丈夫死后,她沉沉地睡了三天。睡得非常舒服,似乎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睡过觉了。起来时已近中午,她拉开窗帘,阳光正灿烂。明亮的光,从窗口一头撞进她的心里。似乎有点突如其来,轰的一下,她的心瞬间亮堂。她突然觉得生活从此安稳了。这份安稳,比身边站着一个保护她的吴医生更让她感觉踏实。
青林还小,日子要过。也就是从这年起,她再次出门给人当保姆,她这辈子只会做这个。她去吴医生工作的医院里当护理员,照顾那些住院的病人。她第一个照顾的人,便是马教授夫人。那时候马教授还不是教授。马夫人在医院生孩子。她像服侍吴医生那样,照顾马夫人。她的安静和温顺,让马夫人很是喜欢。出院后,马夫人说她身体不好,并且不太懂得照顾婴儿,希望她能去马家做住家保姆。她同意了。她不喜欢跟很多人打交道,也不喜欢医院的嘈杂。就这样,她一做多年。她把马教授家里的孩子带大了,也把青林养大了。
青林考上了大学,去了上海。他学的是建筑设计。她的收入不足以让青林更好地求学。于是她把房子租了出去。她用自己的工资和房租让青林的大学生活不致清苦。青林知道母亲的用心。他很努力。他给她写信,说将来一定要挣很多钱,给妈妈买一幢大房子。她很高兴青林能这样想,但她觉得有没有大房子都没关系,青林过得好就是她的满足。
毕业后的青林没有回到母亲身边,因为他们的房子被拆了。青林回来也没有家,而且他特别想挣钱。他选择去了南方,说在南方有更多机会。对她而言,青林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她总是说,你不用管我。妈妈对不起你,不能照顾到你,你自己好好生活才是。
打拼的青林永远忙碌,很少回家。他不断地换公司,换到第四个时,老板是武汉人,欣赏同样来自武汉的青林。他给了青林很多机会,青林的日子一下子好了起来。慢慢地,他在南方买了房子,也结了婚。他们没有办婚礼,而是出国旅行了一趟。出国前他把媳妇带回来给她看了看。在这边,他们也没有家,只是去酒店里一起吃了顿饭,还请上了马教授夫妇。媳妇很漂亮,对马教授夫妇很热情,对她很客气。她想她不过一个保姆,能让媳妇怎么样呢?
马教授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她陪伴着马夫人度过她最难过的时光,然后送她上了路。马夫人人土那天,青林赶了回来。他在花园山租了间小屋,说:“妈,你不用再做了,我有钱养你。只是妈妈还得再委屈几年。我的钱还买不了房子。妈妈就先住在这里吧。”又说,“等我发了财,一定让妈住最好的房子。”
她不介意青林是否发财,只是看到青林黑了瘦了,额上也浮出些皱纹,神情也开始像他的父亲,于是有些难过。
青林很快又走了。他的现实让他成为一个必须现实的人。
屋里只留她一个人。风吹时,窗户啪啪地响。隔壁的呼噜和呓语半夜穿墙而来。早上,太阳出来,光亮扫荡着寂静的房间。吃饭时,自己咀嚼的声音响得如同汽车轰轰开过。一切都太冷清,无聊也就翻倍。她时常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这世界安静到只剩她一个人。她的内心空旷得也只有时间。
7. 我不需要回忆
有一天买菜,她被一辆疾行的自行车撞着。身体一歪,她倒了下来,头碰在电线杆上,血当即从额上流出。隔着血液,她看到路边有一簇美人蕉。美人蕉旁边有个小地摊,地摊一角搁着一双手工刺绣的婴儿鞋。红色鞋面上浮着两条金色的小鱼。她的心蓦然一紧。
所幸她的伤不严重。额头缝了三针,包扎过后,被人送回了家。青林吓得不轻,接到房东电话当晚便从南方赶了回来。她脑子里一直浮着那两条小鱼。嘴里喃喃地说,那个鱼,那个鱼。青林以为她想吃鱼,次日一早跑去菜场买了几条活鲫鱼。
此时的她,已经缓解。看到儿子如此,头也不痛了,倒是给青林好好地做了一盘豆瓣鲫鱼。那是青林最爱吃的。
青林交代安全事项之一二三,便又赶回南方。望着青林的背影,两条小金鱼竟又浮在眼前。她不明缘故,只觉得自己有了某种冲动。于是不顾头上还扎着白纱布,当即上街,买回了针线和布头。她想起自己曾在马教授家绣过的鞋垫,于是,她比画着自己的脚,三下两下就把布剪成了鞋底状。
这天依然有很亮的阳光。她坐在窗前,拿起布,绣出了第一针。仿佛自己真是需要一双鞋垫,又仿佛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无聊。只几天,她就绣好了一双有着两条小金鱼的鞋垫。她在做这件事时,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安宁到如同幸福从天而降,就仿佛她生来就是为做此事而活。做完了一双,她又开始做第二双,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她绣了牡丹,绣了鸳鸯,还绣了麒麟。时间是在她的针尖上流逝的。她不知道自己绣了多少双。她的床靠着墙的一边,已经一层层堆满。低矮的枕头因平铺着鞋垫,也变成高枕。最后她觉得家里再没有地方可放,就买了一只藤箩。她想,她应该卖掉一些才是。
就这样,她走出了家门。她坐在天主堂的对面卖鞋垫。她并不缺钱花。她当保姆,存过一些。而逢年过节,青林也会寄钱回来。青林一寄就是一大笔。她把这些钱都存在银行里。她想,青林将来买房子一定需要。
她每天都能卖掉一两双,这样的节奏很适合她。她也只在晴天时出门,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不时望望对面绿树簇拥的露德圣母,觉得她的目光正与她对视,于是她有了惬意感。
只是,每当这惬意感生出时,另一些东西也不会放过她,它们若隐若现地在身边环绕。尤其美人蕉开出红花的时候,那些东西便在她的身后追逐。她拼命地逃避,但它们始终尾随着。她能感到它们在飘浮和移动,甚至挑逗、勾引她回头捕捉。她记起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惧,闭着眼对自己说,我不回头。我不上当。我不抓你们。我不要回忆。我不需要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更不需要想起我家里有什么人。我都不需要。我的记忆只需要从吴医生开始就可以了。我的生活有儿子青林就够了。忘记有忘记的道理,这也是吴医生说的。
吴医生说这话的时候,他真的还很年轻。
8. “钉子”这两个字
好些年,这个女人就是这样云淡风轻地过着日子。她认识的人很少,认识她的人也很少。她的名字叫丁子桃。
这名字也是吴医生给她起的。吴医生说她一直昏迷不醒,还发高烧。偶尔嘴里会喊一声:“钉子!”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待她醒来后,吴医生填写病历,问她叫什么。她摇摇头,说她什么都不记得。
当时正是春天,医院外的桃树开出了第一朵花。吴医生便在她的病历上写下了“丁子”,他写第三个字的时候,抬头望着她,同时也望见了窗外的桃花。于是,他写了一个“桃”字。他说,你得记住“钉子”这两个字,也许某一天,它会帮你想起往事。
丁子桃想,你就是我的往事。其他的,我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