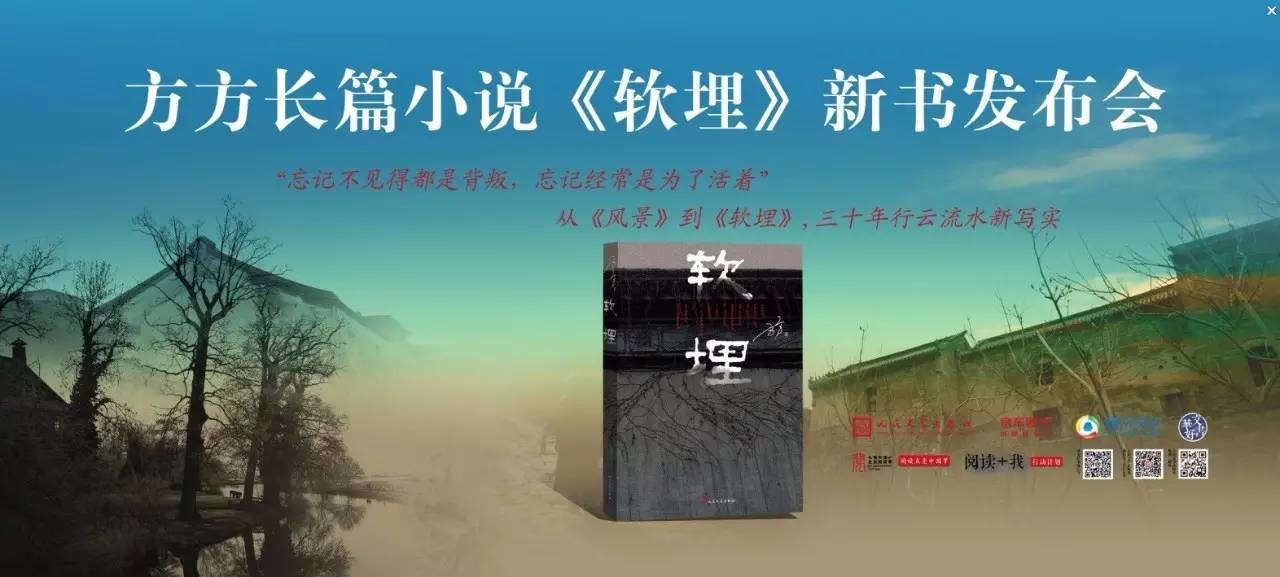第二章
第三章
14. 在面馆里遇到老乡
刘晋源每天早上去洪山公园散步。
他的头发胡子全白,连眉毛也是白的,脸庞却呈乌红色。红白对映,很容易让人记住这形象。沿路都有人跟他打招呼,全是走来走去看熟了的面孔。自从公园敞开大门不收费后,散步便成他的习惯。起先是跟老婆一起走,走着走着,就把她走没了。她是心脏病突发死的。死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长睡不起时,她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叹得有点长,但并没有人在意。
刘晋源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眼睛盯着电视机跟她说,当年我要帮吴家名留在医院,还往军分区跑了四趟路哩。他说了半天,见没人回应,几乎生了气。他有点愠怒道,难不成你忘记了你的命是人家吴家名救的?转脸间他才觉出哪里不对劲。一摸鼻息,发现人已经没了。
刘晋源跟老婆的关系谈不上有多么好,但不好不坏也过了一辈子,习惯了这个人的存在。尽管早知她有心脏病在身,仍然难以承受,瞬间老泪竟流得满脸。那天晚上,他家门口火急火速地来了两辆车,一辆是急救车,一辆是殡葬车。在家的两个儿子,小的送他去医院,大的送他老婆去殡仪馆。刘晋源后来根本记不得他是怎样进出的医院。只知回家后的第一天,他便接着去公园散步了。
他头一次如此形单影只,也头一次觉出自己的孤单落寞。便是这天,路上有个匆忙走路的年轻人,迎面走向他时,朝他笑了笑。这份笑容令他有熟悉感,而这熟悉又带着久远的亲切和温暖气息。他想以前是谁朝他这样笑过呢。那张脸似乎就在眼前,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在此之前,他从未注意路人,也没有在意过往来人们的脸上是笑着还是板着。现在,他居然看到了路上陌生的行人朝向他的微笑。他不禁也咧开嘴,笑了笑。
这一笑,便把心里存留的一点孤单落寞笑忘了。
刘晋源在这一带已住多久,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了。时间在他脑子里像一根漫长的绳索,长得打了结。并且是一团一团的纠结,混乱不堪。尤其退了休,人清闲下来,身边琐事便都像气泡一样冒出。首先是小孩子都成了大人,原本一个个淘气得恨不能揍死他们的两个儿子,居然都人模狗样起来。开着轿车带着妻儿回家,也一个个派头十足。老二刘小川,更是神气活现。只要他回来,一句话不说,先甩几条烟,号称上千元,又或是抬几箱特制茅台酒。而自称前来孝敬二老的他的下属几乎要排队。刘晋源很讨厌这些,却也不能不接受。毕竟,有人孝敬也是幸福。没有了权力,自家单位的人不再过来拍马屁,但儿辈下属的马屁,也一样是马屁,舒服程度完全相同。再就是屋前屋后房子马路都变了。楼高了,路宽了,车多了,以往熟悉的一切全都变得陌生,而相识已久的人,则是隔三岔五地失踪。他们去了哪里刘晋源自然知道,那地方他自己迟早也得去。有熟人去打前站,是好事。待他再去时,日子便会好过得多。所以他不悲伤。只是那些曾经的参照物,固定的和活动的,都一点点消失或变化后.他脑子里纠缠成团的绳子,便仿佛被人剪成了一截一截。存放在记忆中的东西也随那把剪刀的抖动而陆续删除。人就是这样,若无旧物提醒,很多事情就跟清零了一样,从未有过。以前他的老下级吴家名就经常爱说,忘记是人身体中最好的一个本能。
这天早上,刘晋源散步走出公园,突然想吃刀削面。他离家多年,早已习惯南方的菜肴,无论清淡还是麻辣,他都爱吃。儿子刘小川曾经总结说,爸爸的胃,南北兼容,东西并收,是一个开放大气的胃,相当符合改革方向。他很喜欢刘小川的这句话。但是现在,家乡的刀削面却像钩子一样,钩住了他的心。
邻近街边有一家晋面馆,是他老早就知道的。以前动念想要去吃,但老婆是四川人,对晋面全无兴趣,坚决不去。家里的事,一切都是刘晋源做主,但在吃的问题上,他却是听老婆的。因为做饭的人是她。所以,面馆的距离近到他甚至能闻到面香,却从来没有去过。
这天,他决定弯一脚过去。
面馆很小,摆着几张简陋的小桌和板凳。一看便知这店开一辈子也赚不了大钱,不过是一家人讨生活过日子罢了。面馆门口蹲着一只土狗,大铁链子拴着。刘晋源突然觉得,连这狗都有他老家刘洞村的感觉。
进门听老板一开腔,果然有家乡口音。而刘晋源一开腔,老板脸上也立见喜色,夸张地大声道:“哗,老乡见老乡,心里喜洋洋。”
刘晋源笑了起来,说:“可不?离家几十年了,听到家乡话就舒服。”
老板说:“看看,我早就说过,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家乡人相见,就是亲。最关键的是,心里还惦着家乡的面。”
刘晋源忙说:“是呀是呀,专门来吃面的。”
老板说:“今天是好日子,开门连着接待两位老乡亲。那边蹲着的大爷,您看那蹲式,咱乡亲百分百。”
刘晋源便朝老板手指处望去,果然有个老头,蹲在板凳上,埋头吃面。刘晋源笑了起来。那蹲式可真地道,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了。
蹲着的老头似乎感觉到有人在说他,抬头望过来,见刘晋源和老板正望着他笑,便微一点头,改换姿势,坐在了板凳上。刘晋源也朝他点了点头。
老板说:“要不你俩一桌?”
刘晋源说:“行。”
说话间他便朝那老头走去。老婆死前,他很少跟陌生人搭讪。他从未养成这种习惯,现在,老婆走了,他突然心生愿望,非常渴望跟人闲聊。
他的心大概是太寂寞了。
15. 活着,就是他现在的事
桌子很小,尽管女主人抹过,但看上去还是油乎乎的。刘晋源想,老婆挑剔,得幸她没来过,不然又得攻击他们北方人不讲究卫生。为这事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架。就算讲一千遍,她还是不明白,他的老家晋西北没有那么多的水用来讲究,刘晋源想,如不是因为天天挑水太累,老子才懒得出来革命哩。老婆是四川人,水多到抬头低头都是,根本无法理解这些。家里请的保姆也是四川人,观点跟老婆相同,她甚至比老婆还讲究,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不光是他和他老婆,就连孩子们,每天都要换短裤换袜子。她说她宁愿洗,也不愿家里有怪味。两个侍候他的女人,也让他对卫生尤其敏感。
桌上的作料架,也有些油腻。上面摆有酱油、醋和辣椒酱,所有瓶盖,都有脏兮兮气。刘晋源已经不习惯蹲食,所以他在凳子上坐下,那老头便说:“这里的醋最地道。”
刘晋源看了看瓶子说:“山西老陈醋,现在商店里都有的卖。”
老板端了一大碗冒着热气的刀削面上来。未近桌前,刘晋源便闻到那熟悉的味道,他的胃立刻就蠕动起来。老板说:“咱这是自家酿的米醋,您吃了就知道好。店里买的,名字是叫咱山西老陈醋,可味道跟家里的还真不太一样,也不晓得啥缘故。”
老头说:“水差一点,料差一点,酿造过程温度时间都差一点,味道就不地道了。”
刘晋源说:“那倒也是。兄弟是哪里的?”
老头说:“晋西北的,贺家沟。我叫贺全起,小时大家叫我小起子,老了就叫老起。”
老板忙说:“这名字好。老起老起,就是永远不倒呀。”
老板这一说,刘晋源和老起都笑了起来。
刘晋源说:“可是遇见老乡了。我姓刘,名字中带着咱们的晋字,小时家里叫小晋,老了,没人叫老晋,只叫老刘。你我乡亲,你可叫我老晋。”
老起说:“您也是晋西北的?”
刘晋源说:“当然。刘洞村的。抗战一结束,就出来了。”
老起高兴起来,说:“您的口音变化可真大。”
刘晋源说:“可不?大半辈子在南方晃了,没学会南方话,家乡话也变了味。”
两人吃着面,细碎地闲扯起来。真是老了,素不相识,随便坐一桌吃碗面,竟也有一堆话说得没完没了。
老起说他已经七十二了,十八岁时也想出来闯天下,结果家里出了事,爹娘齐齐病倒,没走成。现正在吃七十三岁的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刘晋源说:“老弟,千万别这么说,我马上就要吃八十四的饭了。”
老起忙搁下筷子,作揖致歉。刘晋源摆摆手说:“没关系,也就是这一说了。其实想想这辈子,活得还真值。什么事都干过。吃过苦,享过福,打过仗,剿过匪,毙过人,当过官,挨过斗,坐过牢。还去过朝鲜。兄弟,说句吓你的话,在我手上死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呀。当然,我自己也几次都险些死了。”
“您老厉害。我没打过仗,可是,”他突然压低了嗓子,“我参加过土改。那个吓人,比打仗恐怕不差。”
刘晋源说:“哦,听老家人讲过。那时我在医院里。听说我一个发小,穷得娶不上媳妇,居然在土改时分到村里大户人家的丫头,还是个美人坯子。”
老起说:“提不得,这事提不得。提起来让人脊背发寒。我姑一家,全死了。就剩一个儿子,被我堵在山外,没回去。几十年了,也不知道死活。”
刘晋源叹了一口气,说:“提不得的事多着哩。我打了半辈子仗,挨了多少枪子。这红色江山,有我的血呀。‘文革’了,居然抓了我去坐牢,说我是反革命。我革命一辈子,居然成了反革命。邪不?当时真想不通呀。死的心都有。唉,总算熬过来了。‘提不得’这三个字说得好,提不得的事咱就不提。兄弟也住在这附近?”
老起说:“是呀,户口还在太原哪。闺女在这边读书,找的对象是湖北的。也不问爹娘,自己一家伙就嫁了过来。这年头,爹真是白当。我只好偶尔过来住阵子,看看外孙子。唉,不习惯这边的天,也吃不惯这边的菜。咱说话人不懂,人说话咱也不懂。那个闷呀。”
刘晋源说:“我刚出来时,也一样。可现在怕是回去也不习惯了。我老婆是四川人,以前家里的保姆也是四川人。这俩人把我的胃变成了川胃。”
老起说:“可怜。那得多不怕麻辣呀。”
刘晋源笑道:“早习惯啦。”
老起说:“不过,就算胃变了,人也还得回。根在老家呀。”
刘晋源说:“岁月不同了,这年代不讲根不根的。一把火烧成灰,装进瓷坛里,还谈啥根?有块碑立着,也就不错。”
老起说:“倒也是。年年清明有儿女过来敬炷香,这一生就算得上美满了。”
两人说着都叹了气。
老板在擦着旁边的桌子,接过话说:“您二老还叹啥气?您二位活到这岁数还能拐着弯儿找到家乡刀削面吃,这就已经是人上人了。早走的去到那边的人,听到您二老叹气,还不恨得咬牙?”
老板再一次把两人说得哈哈大笑。刘晋源忙说:“该知足。是该知足了。”
走出面店,刘晋源打了好几个嗝。嗝出的气味令他通体舒服。他觉得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舒服感了。
上了大路,他和老起分了手。两人没留联系方式,都只说,还会来吃面的。他们相信,只要这面店还在,一定就会见面。不过,刘晋源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川菜真好吃,能吃麻辣,是大福。”他想念老婆了。
刘晋源慢慢悠悠朝家里走。
他完全无事。活着,并让自己跟时间好好相处,就是他现在的事。
16. 到南方去
刘晋源这天回来就感冒了。咳嗽,喘不上气。
老婆死之前,大儿子刘小安就跟他们住在了一起。刘小安早先在三线工厂,提前退了休。他最初跟着老二刘小川做生意,做着做着,老二让他回了。说他没有专业,也做不成什么事,不如全心全意伺候家里的二老,让他在外面安心。他负责一年给他二十万,另送一套房子一辆车。刘小安两口子一盘算,觉得合算,就回来了。俩人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住在爹妈家。吃用都是爹妈掏钱,连保姆费用都出自爹妈的工资,他俩就负责吃喝玩乐。刘晋源老婆私底下曾跟刘晋源说,老二不是给他们大把钱了吗?怎么在家里连伙食费都不交?连自家衣服都交保姆洗。刘晋源跟老婆说,算啦,有个儿子守着你,总比没有好。咱俩的退休费也够四五个人花了。钱留着不花,就是废纸。就算咱们的钱花光了,老二还能不管?刘晋源老婆一听这话,也想开了,索性把俩人工资都交给老大管着。反正你给我们吃好喝好就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么一来,两下都省事了。
刘小安两口子每天一早去街上跳舞,顺便买菜回来。刘小安的老婆不放心保姆买菜,总觉得她会故意贪菜钱。所以家里的采买一类的事,都是她和刘小安亲自出马。下午刘小安的老婆或是去美容院,或是跟人打麻将,刘小安则在家里陪父母。所谓陪,其实也就是他在自己的房间上网跟人下棋。到了晚上,自然就大家一起看电视剧了。刘晋源喜欢看战争片子。一边看一边指着电视说,哪能这样打?这不是让战士送死吗?又说,这场战役根本不是这样打的,打仗没这场面。刘小安便总是说,你瞎操什么心。你那时打仗,又没观众,打完了自家能保住命就很高兴了。人家这个打仗,多少万人盯着看,那就得打得好看,场面要气派,反正也死不了人。刘晋源没办法。儿子说得在理,他反抗也没用。
老了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刘晋源觉得也还行,毕竟家里有人进进出出,每面墙壁、每个角落都有人气。不像隔壁张家,儿女都出了国,老婆一走,老头身边就一个保姆照顾。虽说钱多,可没了花钱的力气,钱也是真没用。假如家里成天清冷得像冰库,就不如屋小人多的穷人了。
这天刘晋源没去散步,他起不来床。刘小安夫妇跳舞回来,见父亲没出门,忙跑进他屋里看究竟。一看刘晋源还躺在床上,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立马慌了。马上打电话,要救护车,紧急送往军区医院。好在医院也近,医生仔细看了一番,说关系不大,就是感冒了。又说武汉这地方,乍冷乍热的,老人容易感冒。
刘小安打电话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弟弟刘小川。虽然他是大哥,但刘小川是他的老板,他相当于给刘小川打工,所以家中万事都是刘小川做主。刘小安说,别的还好,烧也退了些,就是听爸爸咳嗽听得可怜。刘小川当即便说,这样吧,烧一退,让爸爸来深圳,等武汉热了再回来。
刘晋源身体底子不错,打了三天吊针,退了烧,精神也好了起来,但咳嗽却一直未止。他不想住在医院里,坚决要求回家。他知道有些老人,进到医院,闻惯了药味,变成心理依赖,根本就回不去了,然后就死在医院。他这辈子别的事不怕,最怕的就是住院。闻到医院的福尔马林气味,他就头昏脑涨。当年,他但凡有病就直接把军分区医院的大夫吴家名叫来家里。这个吴家名是他从深山老林带进部队的,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了医生。吴家名性格安静温和,什么病用什么药,都能说出个道理来。重要的是,这些道理会让他心服口服。他升职调来武汉,幸运的是,吴家名也转业来到这边。大病小病,只需一个电话,他就会亲自登门。这是他一生相当得意的一件事。可惜吴家名死得太早。不然,刘晋源想,我这点小病还用得着住进医院?还用吊瓶子?吊了几天还咳个没完?人家吴家名几服草药,不声不张的,啥问题都解决了。
刘小川电话打来家时.刘晋源正咳得下气追不到上气。刘小川急了,电话里大喊大叫,要刘晋源明天就坐飞机去深圳。刘小川说,公司正好有个经理回总部,刘小安只需将父亲送到机场就是。
刘小安真是巴不得。他和老婆一直想到台湾玩玩,因为父亲的缘故,根本脱不开身。现在父亲去南方,少说也会住一个月,这样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在外面晃。于是忙说好好好。
当晚即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的,刘小川那里什么都有。刘晋源自己只拿了他的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因他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要听新闻。这是刘小川那边绝对没有的东西。刘小川经常说,看电视多好。刘晋源却说听惯了。他心想,你们哪里懂?看电视就得坐在那里什么事不做地傻看。听广播呢,可以一边刷牙洗脸,一边刮胡子,一边泡茶一边看报,啥事都不误。他明白老辈人的想法跟小辈人不一样。他的孙子们连电视都不看,进家门都是泡在网上。
刘晋源现在真不愿意跟年轻一辈人说话。他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而要命的是,他们也觉得他什么都不懂。有一年春节吃饭,他跟孙子们讲述当年在川东剿匪的事。说为了送情报,他的一个朋友被抓住,惨死在了土匪手上。他想说明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料小孙子说:“嗨,爷爷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那一代人。思想太守旧,脑子又笨。叫你们学上网,死活都不学。他要是会上网,办法多的是。随便点一下,情报不就送过去了?真是活该白死。”刘晋源气得把筷子狠狠往桌子上甩了几甩,甩得啪啪响。他大吼了一声:“你懂个屁!”结果孙子还委屈地顶了嘴,说:“明明是你们不懂,还说我不懂。”儿女辈的人都大笑不止。老二刘小川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他还能说什么?刘晋源顿觉自己成了孤军。那个春节,尽管儿孙满堂,他却没有过好。他觉得除了吃饭睡觉这些琐细事,他们彼此聊天,相互都不懂对方。
次日,刘晋源一早就到了天河机场。刘小安跟那个经理也熟悉,一见面就握手拍肩地打着招呼,说:“青林,你看来越活越精神了呀。当了分公司经理,年薪涨不少了吧?”
刘晋源忽觉得这个经理有些面熟,似乎以前见过。又想刘小川的下属经常去他家里送这送那,或许他也去过,面熟太有可能。这经理见刘晋源望着他,忙说:“刘伯伯好。”
刘晋源一想,他好歹是个经理,也忙说:“经理好。”
刘小安和那经理都笑了起来。刘小安说:“爸爸你跟他客气个啥呀,当自家人使。他叫青林,是小川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管办公室时,他也是我的手下。”
青林也笑,说:“对呀。刘伯伯您叫我青林就好。我保证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
因为这后一句话,刘晋源立即对他有了好感。这是他所喜欢的语式。
刘晋源的脸上露出笑容。青林这个名字,他似乎也有点熟悉,只是他不知自己的这份熟络在哪里。转念又想,既然刘小川和刘小安跟他都认识,想必他们在家里经常提。
刘小安把刘晋源交给青林,自己便匆匆而去。候机和坐飞机的时间都很长,但青林很细心,很善于照顾人,一路上都陪他聊天,为他沏茶。沏茶时,还会拿些小点心给他,让刘晋源觉得自己好久都没有这样愉快地跟年轻人相处了。
刘晋源问青林怎么去的刘小川公司。
青林说他在这之前已经换了好几家公司。到刘老板公司面试时,刘老板一听他的话里有武汉口音,立即用武汉话跟他聊天。老板又说他的名字取得好听,有诗意。不像他家,爹妈懒得很,他们生在哪里,就随便从当地的地名挖个字当他们的名字。他哥哥在西安出生,就叫刘小安;他在四川出生,就叫刘小川;他妹妹在武汉出生,就叫刘小武,也不管适不适合女孩叫。他妹妹懂事后,自己到公安局把名字改成刘小舞。幸亏她喜欢舞蹈,这样叫也还蛮不错。
刘晋源大笑。他觉得儿子说得是。当时他们确实觉得取名字麻烦,便就地取字。青林说:“我当时回答刘老板说,您父母不是懒,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做个记号。叫你们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当年的故事。我想他们做的事一定很有意义,他们不想让自己忘记过去。刘伯伯,您知道吗,我被录用,就是因为这段话。因为刘总说我对他人有体贴之心,他的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您相当于是我的恩人呀。”
刘晋源笑了起来。这是他很高兴听到的话,而青林说得恰到好处。
飞机到深圳时,刘小川亲自到机场接父亲刘晋源。有下飞机的一二客人跟刘小川打招呼:“刘总好!”“刘总,亲自来机场呀。”
刘晋源十分不解,说:“你咋认识这么多人?”
刘小川只是哈哈一笑。青林说:“天下人都认识刘老板,刘老板也认识天下人。”
刘晋源坐上刘小川的专车,他叫青林也上车。青林摆摆手,说:“刘伯伯,再见。我们不是一个方向。”说完,他站在那里,看着刘小川的轿车开走,一直摆手摆到他们的车远去。
在车上,刘晋源说:“小川你应该捎人家一脚哩。”
刘小川笑道:“我敢捎他还不敢被捎哩。”
刘晋源说:“顺便坐下车,算个啥。”
刘小川说:“当年你们军区的一个排长敢坐您的车吗?”
刘晋源没吱声。他想,他是不敢坐。
刘小川说:“生意场上,跟你们当年差不多。”
刘晋源说:“你派的这个经理我瞧着顺眼。”
刘小川说:“穷孩子出来做事,勤快,又会做人。哪像我们家大哥,懒得抽筋。”
刘晋源说:“别这么说你大哥。他也不容易。既然人家是穷孩子,你也好点待他。”
刘小川说:“当然。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当年他身上只有一百块钱,现在钱多得已经买得起别墅了。”
刘晋源说:“说这大口气话!”
刘小川又笑,说:“别的不敢说大话,这个还真可以。”
刘晋源不作声了,他不喜欢儿子这种口气。跟儿子在一起,哪儿都别扭。倒不如那个他只认识了几小时的青林。他和他在一起时,始终都有舒服感。这种舒服是一种贴身而又暖心的舒服,甚至是一种久违了的舒服。好久好久,他都想不起来,以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与某个人在一起,也有过这样的感受。
过去的事,留在刘晋源脑子里的,都只剩影影绰绰的印象,它们已然连不成片。他想他的记忆真是一种丢盔卸甲的状态,他大概是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