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寻根”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地平线》译者徐和瑾说,在这部小说里,莫迪亚诺把他以前作品的全部内容压缩为一个哲学问题:“生活该把时间及时间的流逝变成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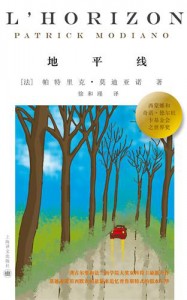 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连贯,全都突然中止,出现了一张张无名的脸,以及短暂的相遇。这一切都是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短暂的片断,不能跟他一生中的其他岁月衔接起来,就依然悬浮在这漫长的现时之中。他会不断对它们提出问题,但永远不会得到解答。对他来说,这些片断将永远是个谜。他开始把它们一一列出,仍然想找到一些坐标:一个日期,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个他无法拼写出来的名字。他买了一本黑色仿皮漆布面记事本,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这样在白天任何时候想起一件忘却的往事,他就可以随时记下来。他感到自己如同在打通关。但他在不断追忆往事时,有时会感到后悔:他的思想为何顺着这条思路,而不是顺着另一条思路?他为何让某一张脸或某个头戴奇特皮帽并牵着一条小狗的身影消失在陌生的地方?他想到可能发生却并未发生过的事,不禁感到晕头转向。
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连贯,全都突然中止,出现了一张张无名的脸,以及短暂的相遇。这一切都是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短暂的片断,不能跟他一生中的其他岁月衔接起来,就依然悬浮在这漫长的现时之中。他会不断对它们提出问题,但永远不会得到解答。对他来说,这些片断将永远是个谜。他开始把它们一一列出,仍然想找到一些坐标:一个日期,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个他无法拼写出来的名字。他买了一本黑色仿皮漆布面记事本,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这样在白天任何时候想起一件忘却的往事,他就可以随时记下来。他感到自己如同在打通关。但他在不断追忆往事时,有时会感到后悔:他的思想为何顺着这条思路,而不是顺着另一条思路?他为何让某一张脸或某个头戴奇特皮帽并牵着一条小狗的身影消失在陌生的地方?他想到可能发生却并未发生过的事,不禁感到晕头转向。
这些破碎的往事跟你在生活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那些年份相对应,当时你面前有许多条路可走,因此你很难作出选择。他在记事本上写下的话,使他想起他曾把一篇关于“暗物质”暗物质是由天文观测推断存在于宇宙中的不发光物质,如不发光天体、星系晕物质等。的文章寄给一本天文学杂志。他清楚地感到,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却不知道有过这回事。如同在天文学上那样,这种暗物质比你生活中的可见部分更多。这种物质多得无穷无尽。而他只是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这暗物质中的几个微弱闪光。他见这些闪光极其微弱,就闭目思索,寻找能产生联想的细节,使他能再现整体,但整体并未出现,只有一些片断,一些星尘。他真想投身于这暗物质之中,把断掉的线索一根根接好,是的,要回到过去,抓住一个个影子,了解其来龙去脉。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只有找到那些姓。或者名字。它们能起到磁铁的作用,能再现你难以弄清的模糊印象。它们存在于梦中,还是在现实之中?
梅罗韦?是名字还是绰号?别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这个上面,否则闪光就会消失。能把它记在记事本上就已不错。梅罗韦。装作在想别的事情,是使回忆变得清晰的唯一办法,当然不能勉强。梅罗韦。
他沿着歌剧院大街走着,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这街区靠近林荫大道和证券交易所,现在是否是时候了?梅罗韦的脸现已浮现在他的眼前。是个青年,金发拳曲,穿着背心。他甚至看到他身穿青年侍者的工作服——就是饭馆门口或大饭店总台的侍者,样子像未老先衰的孩子。这个梅罗韦也是这样,他虽然年轻,但脸已憔悴。他的声音显然已被人遗忘。然而,梅罗韦声音的音色,是一种金属质感的音色,一种珍贵的音色,依然清晰可辨,他可以说出蛮横无理的话,就像调皮的孩子或纨袴子弟那样。接着,突然响起老人的笑声。是在证券交易所那边,大约在晚上七点,办公室下班的时候。职员们一群群蜂拥而出,他们人数众多,会在人行道上撞到你,把你卷入人流中带走。这个梅罗韦和人群里的两三个人一起从大楼里走出来。一个肥胖的小伙子皮肤洁白,跟梅罗韦形影不离,一直在听他说话,显出既害怕又欣赏的样子。一个金发男子面孔瘦削,戴着浅色眼镜和镌有姓氏首字母的戒指,往往保持沉默。他们中年纪最大的约有三十五岁。他的脸在博斯曼斯的记忆中要比梅罗韦的脸来得清晰,他的脸臃肿,鼻子很小,而棕发又往后梳,使他的脑袋活像斗牛犬。他总是面无笑容,显出蛮横的样子。博斯曼斯已看出他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他跟他们说话时一本正经,仿佛他在教训他们,其他人听他说话,就像听话的学生。梅罗韦只是偶尔插上一句不礼貌的话。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博斯曼斯已经记不清了。他们只是些影子。梅罗韦这个名字使他感到不舒服,那是在他想起“欢乐帮”这三个字的时候。
一天晚上,博斯曼斯像平时那样在这座大楼前等候玛格丽特·勒科兹,梅罗韦、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首先走出大楼,并朝他走了过来。办公室主任突然问他:
“您是否想加入欢乐帮?”
梅罗韦发出老人般的笑声。博斯曼斯不知该怎么回答。欢乐帮?对方的脸仍像平时那样严肃,目光冷峻地对他说:“欢乐帮,就是我们。”博斯曼斯听到他凄凉的声音,反倒觉得这事滑稽可笑。他在那天晚上对他们三人仔细端量,觉得他们仿佛手拿粗棍,沿着林荫大道走着,不时突袭一个行人。每打一次,仿佛都能听到梅罗韦的尖细笑声。他对他们说:
“欢乐帮嘛……让我考虑一下。”
他们三人显得失望。其实,他跟他们才刚刚认识。他跟他们单独见面也只有五六次。他们跟玛格丽特·勒科兹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是她介绍他跟他们认识的。脑袋像斗牛犬的棕发男子是她的上司,她必须对他显得殷勤。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在嘉布遣会修女大道遇到他们三人,就是梅罗韦、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他们刚从一家健身房出来。梅罗韦非要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茶,吃一块杏仁饼干”。他在大道另一边的塞维尼侯爵夫人茶馆里坐了下来。梅罗韦把他们带到这家茶馆,似乎非常得意。他像茶馆的常客那样把一个女服务员叫来,用刺耳的声音要了“茶和杏仁饼干”。其他二人看着他,显出宽容的样子,办公室主任持这种态度,使博斯曼斯感到惊讶,因为他平时极其严肃。
“那么,对我们欢乐帮……您是否已作出决定?”
梅罗韦口气生硬地对博斯曼斯提出这个问题,博斯曼斯则在寻找起身离开的借口。譬如对他们说他要去打电话。他就可以跟他们不辞而别。但他想到玛格丽特·勒科兹和他们是办公室的同事。他每天晚上要去接她,还会遇到他们。
“那么,您是否有兴趣参加我们的欢乐帮?”
梅罗韦不断提问,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仿佛想跟博斯曼斯决斗。其他二人像是准备观看一场拳击比赛,脑袋像斗牛犬的棕发男子,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脸上毫无表情。
“您要知道,”博斯曼斯用平静的声音说,“在寄宿学校和军营生活之后,我对帮派不是十分喜欢。”
梅罗韦听到这个回答感到尴尬,发出老人般的笑声。他们就谈起别的事情。办公室主任声音低沉地对博斯曼斯解释说,他们一星期去两次健身房。他们在那里进行各种训练,其中有法式拳术法式拳术是1830年从英式拳术和踢打术派生的拳术,拳击者可以拳打脚踢。和柔道。那里还有练剑室和击剑教师。每星期六,可以报名参加在万塞讷树林举行的越野障碍赛跑或在铺煤渣的跑道上赛跑。
“您应该跟我们一起参加运动……”
博斯曼斯感到主任是在对他下达命令。
“我可以肯定,您参加运动不够多……”
他直瞪瞪地望着他,博斯曼斯难以忍受这种目光。
“那么,您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运动?”
他那张斗牛犬般的胖脸露出了微笑。
“就在下个星期挑一天,好吗?我给您在科马坦街报名?”
这一次,博斯曼斯不知该如何回答。是的,这种坚持己见,使他不由想起在寄宿学校和军营生活的遥远年代。
“刚才您对我说,您不喜欢帮派?”梅罗韦尖声问他。“您也许更喜欢跟勒科兹小姐做伴?”
其他二人听到这话一脸尴尬。梅罗韦仍然挂着微笑,但他似乎还是害怕博斯曼斯会作出反应。
“是的,确实如此。您显然说对了。”博斯曼斯温和地回答说。
他在人行道上跟他们三人分手。他们在人群中渐渐走远,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并排走着,梅罗韦稍稍落在后面,回过头来跟他挥手告别。他是否记错了?这也许是在另一天,晚上七点,他在大楼门口等玛格丽特出来。
几年后,大约在凌晨两点,他乘坐的出租车要穿过科利泽街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司机见红灯停车。就在马路对面人行道边上,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子挺直,披着黑披风,赤脚穿着凉鞋。博斯曼斯认出是梅罗韦。他的脸瘦了,头发剃成板刷头。他站在那里守候着,在稀少的车辆开过时,他每次都露出微笑。但不如说是在怪笑。他如同皮条客,专为坟墓里出来的客人找姑娘。那是在一月份的一天夜里,天气特别寒冷。博斯曼斯想要走到他跟前和他说话,但心里又想,对方是不会认出他的。他透过后窗仍然看到他,直到车子在圆形广场拐弯。他无法把目光从这身披黑披风、一动不动的身影上移开,他突然想起那皮肤洁白的胖胖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常常跟梅罗韦一起走,似乎对梅罗韦十分欣赏。这小子后来怎样了?
这样的影子有几十个之多。不可能说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于是,他只好在记事本上记下模糊的迹象。脸上带瘢痕的棕发姑娘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奥尔良门到克利尼昂库尔门这条地铁线上即巴黎地铁南北向的4号线。……往往是一条街、一个地铁站、一个咖啡馆使他们从往事中再现。他想起穿华达呢衣服的流浪女子,走路的样子像以前当过模特儿,他曾多次在不同的街区跟她迎面相遇:寻南街、阿尔博尼街、科维扎尔街……
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的几百万居民之中,竟会在很长时间之后又遇到同一个人,而每次遇到的地点又跟前一次遇到的地点相距甚远。他的一位朋友看了最近二十年的《巴黎赛马报》,以研究概率论,他在赌马时曾向这位朋友请教过。不,对此无法回答。于是,博斯曼斯在想,有时命中注定如此。你就会跟同一个人迎面相遇两三次。你要是不跟这个人说话,那就是你的损失。
(本文选自莫迪亚诺《地平线》,译者徐和瑾,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经过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