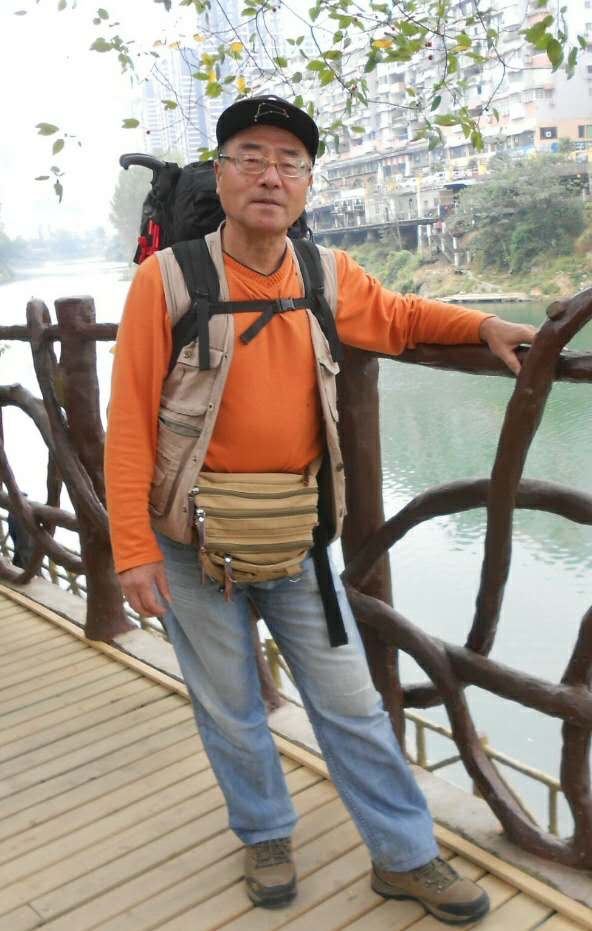看了你的小说《细麻绳》,很有感触,陆文,你让我想起插队时的一件事。我没有你幸运,你插队在田少人多的公社,跟我相比,种田像消闲,难怪你有精神跟女插青轧朋友。而我那个生产队,田多得吓人,平均每人达七亩之多,而且那儿还有血吸虫。我第一次到那儿,乘坐的是轮船,那儿汽车不通。到队里,满眼都是泥墙草屋、芦苇河流。村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平日赤着脚,冬天穿双芦花鞋、破棉鞋。已婚妇女到了夏天,上衣都不穿,就系个红肚兜。她们甚至不穿内裤,一个妇女下田劳作,裤子不小心撕开,只好露出屁股回到村里。上茅坑,很容易碰到屁股翘起的女人。她们不避嫌,哪怕男人在旁边大便,仍然放屁“披披披”的,小便“痴痴痴”的,只当呒介事(若无其事)。
村民还有小偷小摸习惯,目标都是生产队里的东西,比如柴草、稻谷、米糠、麦粞、蚕豆、黄豆,不是燃料就是食物。这也难怪,因为即便一个强劳力也没法养活自己,年年透支。大队了解这种情况,不认为小偷小摸,认为顺手牵羊,所以发生偷窃都走过场,从来没认真的捉拿过小贼。
生产队劳力缺乏,只好延长劳动时间。农忙,哨子“居居居”的,像半夜鸡叫,挺惊心动魄,让人害怕。我现在仍听不得这种哨音,哪怕是篮球场上裁判的哨音。不是瞎说,下半夜三点就出工,深夜12点才收工,不过睡二三个小时。由于没有肉吃,没有副食品,饿得头昏眼花,一天要吃两斤大米。收工回家,摇摇晃晃,路都走不稳。长期的体力消耗,使我对女人没了向往,甚至早上起床,生殖器也软塌塌的像蜒蚰,没反应。一个年轻泥瓦工的家主婆(妻子),独守空房,呒不白相(没有性游戏对象),用粮食和眉眼引诱我,我都没上钩。究竟坚守道德原则呢,还是没有力气,还是自认为童男子,不肯轻易失身,只有我自己明白!
当时我年轻,比较本份,或许喜欢表现,让贫下中农有好印象,所以出工十分积极。遗憾的是,长期水田作业,两只脚出了问题,皮肉浸胖,嫩得像豆腐,先是蜕皮,后是脚趾间溃烂,后来出脓出血,因为每天下水田,疮口没法愈合。我向队长请假,歇了两天,仍不见好,队长上门催出工,没得法子,我逃到城里父母处,可住了不过两天,队长就出现在我面前。说我懒泼(懒惰),请我父亲叫我回队。我兄弟姐妹六个,三个插队,三个读书,父母不胜负担,讨厌吃宕空筲箕饭的(吃白饭),也不愿我长期赖在家里。
无处可去,被迫回队,下田出工。田水发黄,像尿水,热气蒸腾,达四五十度,黄蟮肚皮都朝了天。两只脚伸进水田,拿起秧苗,给第二茬的双季稻插秧,真是钻心痛呀!我哇哇哇的,龇牙咧嘴的,社员看了都笑了出来。那时候我的感觉,队长只要完成农忙,哪怕我烂掉两只脚。还感觉,我好像不是来插队,而是来接受劳动改造。这种被迫的水田作业,跟强迫劳动有什么两样!插队青年跟四类分子有什么两样!实在坚持不住,我不听队长号令,自作主张回到了队里的住屋。
队长没有上门捉我去下田,不过第三天分双季稻稻谷,每人一百斤,居然没我的份。队长明知我米窠朝天,仅剩几天口粮,就是利用职权,一粒谷都不分给我。
问队长要口粮。队长说,一粒谷都不会给你,看你拿我怎么办?我说,人民政府不饿杀人,你想饿杀我,就是逼上梁山,逼我犯法!逼我拼命!你要晓得,我宁愿犯法,也不愿饿杀!队长说,你去死,跟我不搭界!我拿出五元钱,恳求:我用铜钿买,总可以了吧!你要给我活路,报复不要太结棍,难道你们这儿的人,真像外面传说的那样:“一条××(河名)笔立直,一半强盗一半贼!”我不下水田,不是因为偷懒。队长说,在这儿,我说了算,铜钿没有用场。不给你,你拿我怎么办?我说:你再说一遍!队长说:就是不给你,看你拿我怎么办?我一记耳光,队长倒了下去。
我不晓得自己的手劲大呢,还是队长禁不起打,还是他诈我。反正他倒在地上不起来。我慌了神,要紧拉他起来。队长四十多岁了,已未老先衰,他赤着脚,赤着膊,瘦瘦的,肋骨根根看得出,而且头发长得像野人。样子不像干部,倒像个奴隶。我说,你逼我动手,我不是有意打你。我付钱,你给我稻谷,不是完了嘛!为啥要搞得水火不相容呢?我请你吃过酒,平时也敬你烟,你为啥不给我面子呢?
队长不说话,爬起来,一溜烟的往大队部去了。我晓得他去告状,但不晓得事态会怎么发展!我心神不定,呆在住屋里,两只眼睛密切注视大队部那儿的动静。
一会儿,看见妇女主任小黄往我这儿来了。小黄虽然做妇女主任,其实还是姑娘,挨家挨户动员妇女戴环都脸红,通知男人结扎,都叫赤脚医生陪着去。她不像前任那样跟民兵营长勾勾搭搭,差点养了私囡。平时我们关系不错,路过我这儿,她总是跟我先搭腔。她对我说,书记叫你去一趟,并安慰我,有事好商量,不能动手哇。我一边解释,一边跟着她往大队部赶。
踏进大队部,只见写字桌旁,围坐着六七个人。有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就是那个朝前任妇女主任乱使枪的民兵营长,还有会计和两个其它生产队的干部。我还没有跟他们解释,大队书记就拍了记桌子,高声喊: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这时,我才明白跌进了陷阱,怪不得他们叫小黄来,原来麻痹我。那时候,我像吃了豹子胆,突然跳到办公桌上,拿起算盘,我说,谁上来,我跟他拼个死活!我反正不想活了,看谁愿意陪我死!我杀气腾腾的眼睛死盯着民兵营长。他不敢动手,果然没有人敢动手。
从那以后,明白一个道理:一人拼命,万人莫当!所谓的法律和秩序都是建立在百姓恐惧的基础上的。这些大队干部,一年比我们多拿一二千工分,折算钞票不过一百多元,尚且怕死,现在的干部,年薪十万,肯定更不敢主动出面跟哪个草民做什么冤家,保命要紧啊!死了,钱别人用啊!就此而言,怕死的统治者都不是强者!
后来,他们打电话叫公社派出所的警察来收场。那警察细皮白肉,是个年轻人,他好言好语,把我请进派出所。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又像推着我,又像扶着我,叫我去会议室谈谈,待我踏进门,后面的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原来是牢房。四面都是墙壁,墙角落有只马桶,二米上方才有一个装有铁栏杆的窗户。我在里面喊:你开门呐,人民政府不能不讲道理啊!队长想饿杀我,难道你们也想饿杀我!我在里面不停的喊,喊得喉咙都哑了。
隔了三小时,那警察开锁,跟我谈话。他说,你叫得这么起劲,证明你还没饿昏。队长是老党员,你居然敢打他的耳光,没王法了……你向队长道歉,我叫队长分稻谷。我感激的说,蛮好,早分给我稻谷,我也不会动手打他耳光。我向你保证,我出了娘胎,从来没跟任何人动过手,不信你问我爷娘。
江苏/陆文
2007、8、24
陆文说明:
插青采访录,根据录音整理,基本保持原貌,语言不通的地方稍有修饰。当事人不愿公开姓名,只好将他的姓名及插队地点隐去。对“小黄”的描绘比较繁杂,问当事人啥原因。原来他对她有所好感,可以说是个暗恋对象。他承认,英勇壮举有可能是由于她在场,而激起了他的雄性力量。
文章来源:博讯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