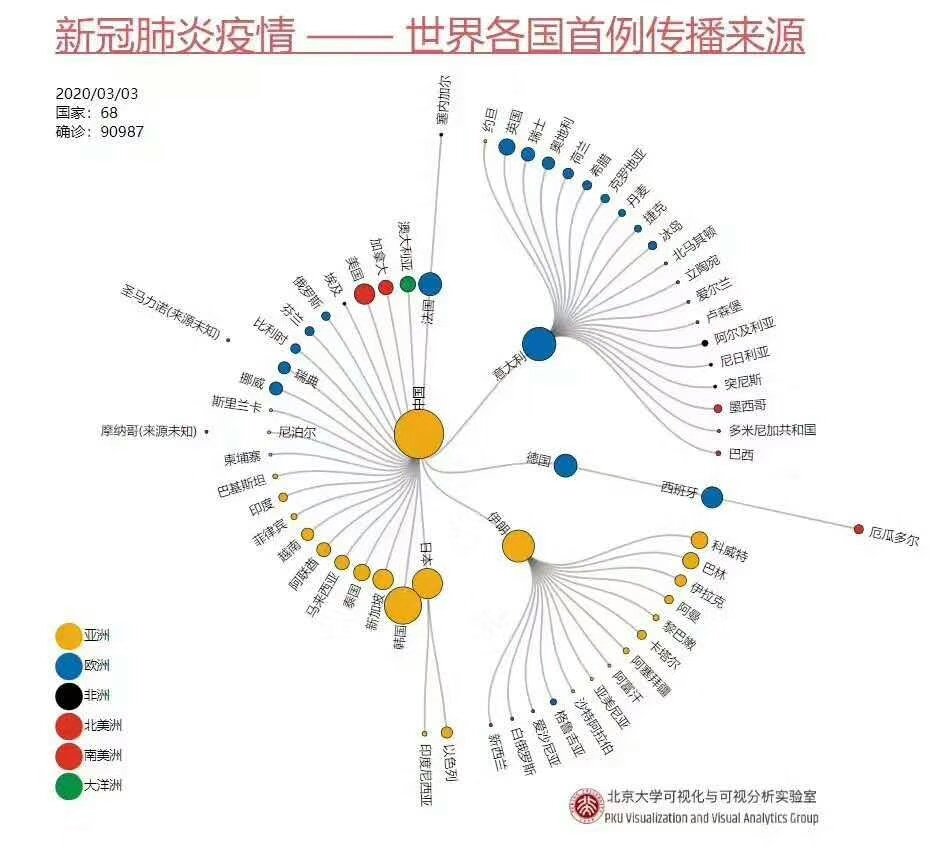新周刊 2020-03-05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1月25日,困在湖北省作协和文联大院的方方开始写“武汉日记”。
凌晨等着看方方的“武汉日记”,已经成了许多人入睡前的一种默契。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身处武汉现场的方方,用带着个人体温的笔触,记录下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个小人物,描述那些生与死、哀与乐。
至3月2日,“武汉日记”已经写到了第35篇,武汉仍未解封。
凌晨2点29分,方方在写完第35篇日记后,接受《新周刊》专访。她说,武汉解封之后,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更新“武汉日记”。
01
太多人阅读
我自己是有一点恐惧感的
新周刊:过去你的写作只被小部分人关注,这次读者群则是数千万人。这种关注对你的表达本身有影响吗?
方方:我是很习惯、也很喜欢自己的作品被不多的人关注的。所以我在微博上写的时候,一直很放松,也很随便。而且长的长,短的短,随时可以打住。现在人多了,的确会谨慎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我是请人帮忙转发的,不由自主会小心一点。一定会影响表达的。所以,太多人阅读我自己是有一点恐惧感的。
新周刊:这一个多月来,读者发现你写的日记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和你的心态有关吗?
方方:心态和情绪肯定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新周刊:日记里,你常提到自己的三个哥哥。你们兄妹四个,在疫情期间,关系和以往有什么变化吗?
方方:我们兄妹四人本来关系就挺好。其实跟平常一样,依然各自住在各自家里,各自聊各自的话题。当然,以前比较多的是看我哥哥的孙辈们在干什么,现在他们经常转一些别人写我的东西。
新周刊:有评论认为,知识分子、作家群体在此次疫情期间集体失声。你怎么看?
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其实很多作家都在写,在记录,只是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同而已。我因为长年在微博上写东西,更公开一点,所以被关注到了。至少在湖北,不存在失声的问题,我所知的一些作家,也都在记录。至于在省外的作家,人家不了解这边情况,真的也不好说什么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并不成立。
新周刊:从封城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很多媒体都在梳理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你来说,有哪些值得被关注的时间点?
方方:封城本身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封城后,我想初一应该是一个节点。因为从那天起,武汉的疫情引起全国关注,而外省驰援的医疗队也是那天过来的。政府也开始拿出具体的办法。大家心里多少都踏实了一些。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恐慌。
但是,这之后是武汉人最惨烈、最无助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医院无床位,而病人到处奔波,四方呼救,却无法及时得到帮助。无数人都是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这样被感染的,实在是很恐怖。这个时间一直到方舱的建立以及省市领导换人,病人有了安置地方,可以得到治疗,这让武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两个节点。
现在我们应该进入的是第三阶段,那就是郁闷。尽管不恐慌,也不惨烈,但漫长的等待,何时是个头,也是问题。各种心理疾病也会产生。很多人家还有生活的压力。
新周刊:近两个月里,有发生过什么让你感到特别后怕的事吗?
方方:当然有。当钟南山院士说出“人可传人”这句话时,我们所有人应该都会很愤怒,因为之前我们是很警惕的,但官方一直说,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它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就是,只要我不吃野生动物,不去汉口华南海鲜市场,就不可能感染。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听到钟南山这句话后,我想很多人都在回头检索自己这半个月来的行踪,每个人都不敢排除自己是否被感染。
我更担心的是,我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而我女儿跟他吃饭不久,所以我很害怕女儿会被感染。所以,我女儿1月22日夜晚从日本回来,我就让她隔离在她自己家。我开车去机场接她,我们路上都戴着口罩。那天,是我最紧张的一天。
02
如果没有志愿者的出现
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新周刊:你觉得这次疫情中,有哪些人和事被忽略了?
方方:当集中精力让病人有床位可去时,非新冠肺炎病人被忽略了,他们的悲惨,一点也不亚于新冠肺炎患者;还有家中无劳力的老人被忽略,后来又发现老人院和福利院被忽略。总之,一直到这些被忽略的社会边缘人拼命呼喊,才开始慢慢调整。从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我们的管理实在太有问题。尽管有不得已的疫情问题,我想也会有是否尽职的问题。目前,非新冠肺炎患者,还是存在很大问题。
此外,封城这么长时间,健康人的生存即生活压力问题,也同样在被忽略。
回过头来,觉得被忽略的人及事,委实太多了。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桶边的百孔和千缝,却无力顾及。
得感谢无数志愿者的出现,这些年轻人太了不起了。是他们见孔便堵,见缝即填,比如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封城一个月中,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还有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很多很多的他们。其实并没有人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看到没有人管,主动接盘。按说,政府各部门都有管理人员,他们在封城同步,就该各负其责,相应地考虑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及时补漏填缝的志愿者。没有他们,武汉不知还会有多少糟糕的事。
03
首先不想做的
就是不想再记录这个日记了
新周刊:这一次疫情,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方方:我太知道武汉这一次为什么会延误二十天了。这既是习惯性延误,也是有意的延误。你只要核对记者调查拉出来的时间表,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所以,最应该反思的就是:你是要其他至上,还是民生至上。
新周刊:在你随笔集《武汉人》的后记,自嘲作为武汉人“有些夹生”,那么通过这次疫情,你对武汉和武汉人,有了什么新的看法?
方方:疫情让武汉人受到很大伤害,但这对性格不会有什么影响。当开城之后,时间会慢慢冲洗掉人们的悲伤,他们仍然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某些私人之间,会因为疫情中同病相怜可相互照应,产生一些感情,这个可能会有的。
新周刊:如果疫情过去,武汉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我首先想到的是最不想做的事,那就是不想再记录这个日记了。然后好好休息一下,继续完成我计划在春节期间要写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