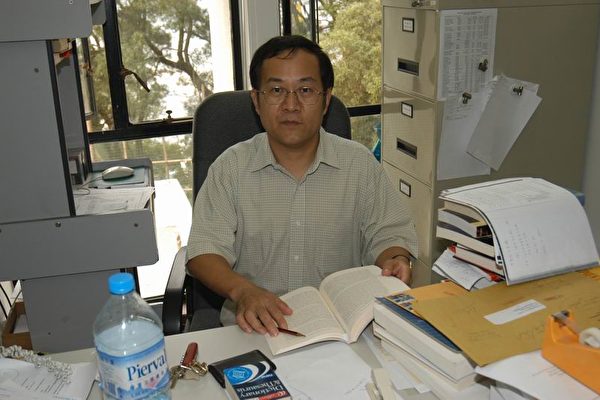之四:我爱愚人节
(2020/04/01)
我喜欢今天这个日子。是的,四月一日,西俗“愚人节”。同是所谓“节日”,这一天,比起五月一日、七月一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八月一日、十月一日,不是都高明得太多太多吗?也许仅有六月一日可以与之媲美:天真的儿童们,与另类天真的傻瓜们,真是世间最可爱的人。
这个日子不仅天真,而且智慧。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年365天里最有智慧的一个日子。或曰:这不是愚人的节日吗,怎么就智慧了呢?我说:那么,你知道谁是愚人吗?
好像没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愚人节的英文说法之一,是All Fools‘Day ——这也是我钟意的那种说法;我甚至愿意将之译为“全愚人节”。也就是说,我将之理解为:所有人都是愚人;而不是理解为:所有那些傻瓜。后一种理解当然更为流行,但事实上,它必定导向我那种理解。
有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说你是整个希腊最聪明的人呢?”苏格拉底说:“因为我知道自己无知”。反过来,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愚人。当你说“所有那些傻瓜”时,你以为自己不是傻瓜;但按苏格拉底的逻辑,这恰恰表明你是傻瓜。你以为别人愚蠢,正见出你自己愚蠢;因而,所有人都是愚人:有被人看作愚人的愚人,还有许许多多看别人是愚人而自己不自认愚人的愚人。于是,四月一日,是我们所有人的节日。当然也是我的节日,所以我喜欢这一天。
你如果懂得了上述道理,那么,愚人节就是对我们的警醒与祝福。至少,在这一天,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傻瓜,因此开启了智慧之门的一道门缝。一年364天中的傲慢与自以为是,到了四月一日这一天,你是看到别人是傻瓜而加倍傲慢并自以为是呢,还是警醒到自己也是傻瓜而稍稍打消那种傲慢与自以为是呢?在这一天,如果你还不能有片刻的自我反省,恐怕你就将永与智慧隔绝了吧?
而且,这还是个充满幽默的日子啊!这个好笑的世界,并不是每天大家都有心要讲讲笑话的吧?哪怕是恶作剧,也比剧作恶要好太多太多吧?单单为了这一条,我倒宁愿每天都是四月一日呢!
兼具天真、智慧与幽默,这不是人生在精神上的最高境界吗?更何况,这一天,四月天,正是春风和煦、杂花生树的日子呢!这就好比一个天真、智慧、幽默的人,还有一张美丽且微笑的脸,有一副温和而轻柔的好脾气,有一种青春的生机勃勃——那简直就要是一个完美的人了哈。
之五:记忆力的贬值
(2020/04/02)
自从有了电脑,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人的记忆力似乎就迅速地、大幅度地贬值了。我把这看作人类的一个转折性的退化。很多灾难由此而生;甚至,将来有一天,如果人类灭绝了,我相信一个根本原因是在这里。
大贬值当然有大贬值的理由。开初时,有了电子计算器,小学生就不大需要死背小九九了。可那种计算器,与今天的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苹果手机等等相比,其间的差距,简直就像石器时代的一块燧石与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现在,就是用自己的电脑储存资料,也早就远远落伍了。网上连线找资料,方便快捷;自己的电子资料,也都放到了??上。有了这么方便的外脑,而且是记忆功能比人类大脑强大到千万倍的外脑,人的记忆力,相比之下就很没有价值了。
于是乎,人们致力于发展能够保存记忆的硬体,鲜有人还在乎如何去开发自己那个外头一层不很坚硬的壳子、内里储存容量有限的大脑的记忆力。说实话,如果单是为了记忆,人们真该砍掉自己的大脑,在那个部位安装上同样那么大一块的硬碟,那岂不人人都要比天才还要天才了吗?
可惜,在人类还没有能够这样改头换面之前,现在这个肉质的大脑就已经退化到了近似老年癡呆症患者的记忆水准。当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来袭时,人们(包括生活在当年重灾区的香港的人们)居然鲜有忆及2003年的萨斯者。每当看到有人说这次疫情“突如其来”,我就想:17年前您还不记事呢吧?天下有什么事会第二次“突如其来”呢?
就是一个当年还不记事的某人,其实也没有理由那样说。人类有集体记忆——这早在1925年就有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来了。岂止人类?动物也有集体记忆,而且能够代代传承这种记忆,这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些年,不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年轻人,他/她会一脸无辜地表示:您说的那事儿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呢!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回答这种人呢:是的,您还没有出生,人类也就还没有开始,因此那都与您无关。
因此,前两天得到一位在加拿大某大学任教、大陆背景的年轻教授的电邮,很是让我安慰。他回忆说:17年前,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一,当时旁边宿舍的同学因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实习,不幸中招去世,他也因此被隔离了两周。我看,他对当前情形的认识,因此便有了时间的深度。
没有记忆力的人,恐怕只能说是白痴吧?没有记忆力的民族,难道能够有未来?没有记忆力的人类,应该很快就会灭绝掉的——我这样猜测。
之六:神农架中“十日谈”
(2020/04/03)
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航班就将降落在罗马达芬奇机场。舷窗外是一片最后的夜色,怀拥绵绵云朵在时间的秒钟中缓缓旋舞的幽微光线,展示着黎明正如花苞般在天际一丝丝绽放开来……
可惜,这是一趟已经取消了的旅程。此刻的我,还坐在家里的客厅中,刚刚用过简单的晚餐,喝了一杯红酒,正是一天最为慵懒的时刻。
但我此刻的心绪却完全说不上轻松;它坠入了宇宙间最深最深的陷阱,那就是时间的深处。我仿佛置身公元1348年:在义大利,“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到了那一年的初春……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是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名著《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开头(译文参见方平、王科一译本)。大约十天前,我在这里引用过了。当时,除了对义大利人的祝福,我只有短短十几个字的感想:“谁承想,672年之后,此悲惨情景再现……”
所幸,那场灾难开出了绚丽的文明之花。没有文艺复兴,便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直接以那场黑死病为背景而展开的《十日谈》,在这奼紫嫣红中自有其绰约风姿。我对此书钟情已久;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由于某种机缘,我在入学研究院后写的第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十日谈》与《红楼梦》”(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3期)。难免,这两个多月来,我好多次对内人说到:武汉之后,中国也应该有本《十日谈》吧?
同样好多次,我随即否定了这种奢望。原因无他,盖:没有反省,没有智慧,没有新观念,人类就只能被灾难所摧毁,而不可能在灾难中新生。三十年来,或许更长时间以来,中国还有反省、智慧与新的观念吗?就是那些已经甚为古老的智慧,也大都早被压制、摧毁、埋葬了吧?谓予不信,不妨听听这句话:“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应该不算什么石破天惊之语了吧?然而,在中国,今天谁敢这样大声宣告呢?
我想像,有那么几个青年男女,在武汉封城之际,逃进了神农架的一个什么地方,在那儿互讲故事,犹如《十日谈》那般。要讲述当代中国官员、富豪、甚至小民的荒淫故事,其“精彩”应绝不下于《十日谈》中所载;但要表达反省与新观念呢?很难想像有人能说出上引绮丝梦达在《十日谈》第四天所说的这种想法呢!无奈,结尾恐怕只能安排她们都死在神农架,大家一“贱”到底算了。
——《纵览中国》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Sunday,April 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