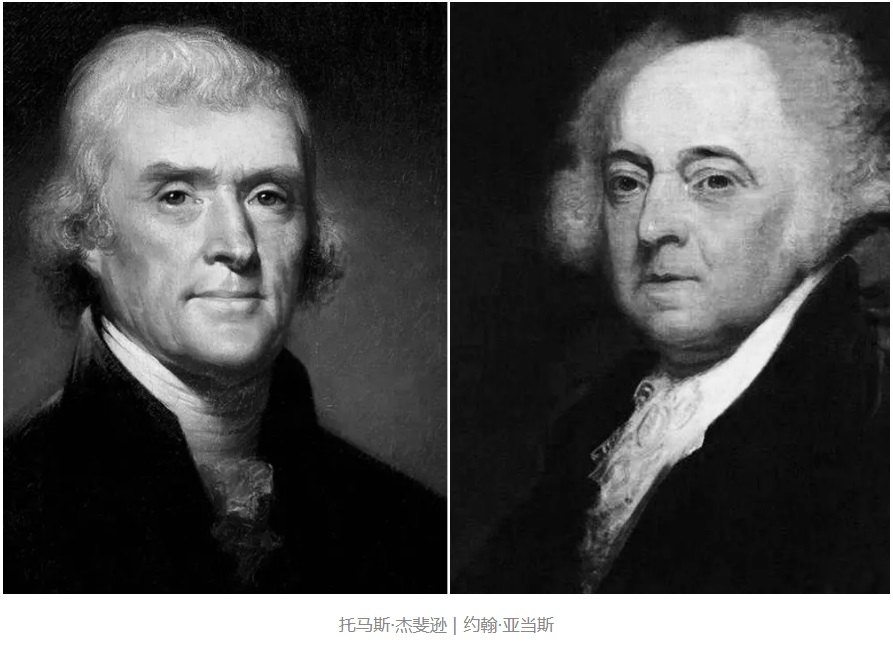川普的支持者们经常会说,川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美国人民并不傻,所以应该信任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总统选举真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每次都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我们现在就以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的几起争议为例,来看一下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存在的的问题。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所谓的间接选举,它不是按比例由公民直接投票选出总统,而是先由各州选出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然后再由选举人团投票选出总统。最开始设计这个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要保护小州的利益。建国初期,州与州之间的人口差别非常大,像纽约这样的大州有几十万人,特拉华这样的小州人口只有几万,如果按比例分配,美国13个州中只需5个州就可以决定多数,小州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另一个原因是,像麦迪逊这样的开国先贤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没有信心,由于美国地域辽阔,那时候通讯交通都不方便,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也不高,他们对总统候选人缺乏了解,如果让他们选出他们信得过的当地精英(选举人)来投票选举总统,更能保障选出所谓的“自然贵族”。那个时代,民主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价值,开国先贤设计一种间接选举制度,恐怕也有对民众易被阴谋家煽动而出现狂热的多数暴政的恐惧。
选举人团制度,是按照各州参众两院的人数来分配选举人指标的。参议院每州两个名额,大小州相同。众议院按照人口比例分配指标,但最小的州至少有一个指标。宪法只规定选举人的指标和由选举人团投票选举总统及选票送达格式,但每个州具体怎么操作联邦宪法是不管的。联邦宪法中的联邦权力是州权的让渡,除了明文规定的联邦权力外,剩余的权力都是州的权力。
这样,后来选举人投票演变成赢者通吃就很自然了。比如某个州的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候选人得票51%,共和党候选人得票39%,另外10%的选票投给了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恰好这个州的参众两院最高法院法官多数和州长都是民主党人,他们就会改变选举规则,规定只要本州的多数人选择的是民主党候选人,那么选举人票就全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这种赢者通吃就实现了党派利益的最大化。当一个州这样规定,其他州能不跟着效仿吗?因为每个州都有一个占多数的政党,看到某个州赢者通吃,其他州如果不跟进,其多数党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他要把选举人票分给对手。如此一来,所有州的选举人票最后都变成了赢者通吃,那么这就不再是一种间接选举,选举人团变成了仅仅是一个名额的概念。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直接选举,起码不是按人口比例的直接选举,选举人团的名额分配跟人口比例极不相称。比如,罗德岛人口是加州的1/60,他的选举人票是加州的1/18,也就是在加州是60万人一个选举人,罗德岛18万人一个选举人,各州选民选票的含金量差别太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总统候选人赢得全国总票数多数甚至超过半数,却输在了选举人票上,典型的代表就是2000年戈尔和小布什的选举,戈尔多出53万张普通票,却败给了小布什,小布什获得271张选举人票。从1961年,美国的参众两院人数就固定成538人不再增加,它的一半是269个人,也就是谁获得270张选票以上谁就获胜。当时小布什获得271张选举人票,只多出两张,获得了美国总统职位。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经过了好几次来回的诉讼,最后由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决定了总统归属,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民主的讽刺。
迄今为止,历史上发生多次类似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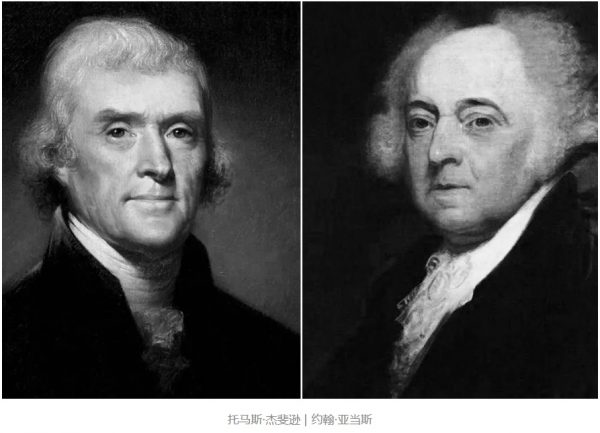
第一次选举危机出现在1800年亚当斯与杰斐逊竞选美国第四任期总统时期。那时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一起投票,托马斯·杰斐逊和阿隆·伯尔作为民主共和党候选人参选总统与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和查尔斯·平克尼代表联邦党人搭档竞选总统副总统,每个选举人可以投两张票,但为了防止地方主义,有一张选票必须投给非本州的候选人,得票最多且过半数者可以就任总统,得票第二者为副总统。
选举结果杰斐逊与伯尔得了相同的73张选举人票,亚当斯和平克尼分别得了65和64张选举人票。显然,亚当斯和平克尼落选,但因为杰斐逊和伯尔票数相等,而那时候选票并不区分总统副总统,这样谁是总统就成了问题。按照联邦宪法规定,当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时,应该由国会众议院一州一票进行表决,过半数者当选。但如果众议院截至总统就职日(3月4日)(此时只剩两周时间)还无法决出胜负怎么办?联邦宪法并无规定。而且吊诡的是,联邦宪法规定国会会期是每年的12月份起,当时已经进行了国会选举,民主共和党大获全胜,但必须到1801年12月份才能开会。这样,决定总统命运的投票只能交给已经落选到期即将离任的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去决定。联邦宪法实际上漏洞百出。问题是联邦党人的选项不止是杰弗逊和伯尔,一篇署名“霍雷休斯”的短文发表在《华盛顿联邦党人报》上,通过对联邦宪法进行解读和推理,得出结论:只有一种途径可以终结“总统难题”:如果众议院陷入僵局,行将离任的联邦党人国会和总统应该通过一个新的法律任命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官员”担任总统以取代托马斯·杰斐逊。这个官员应该是谁?霍雷休斯没说。但按照他的逻辑,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时任国务卿兼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约翰·马歇尔。而后据考证,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正是此公。
对于联邦党人的阴谋,民主共和党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杰斐逊告诫亚当斯,此时一种非常危险的实验正在酝酿着,志在通过国会立法挫败总统选举……这一措施很可能导致武装抵抗,后果不可预料。实际上,民主共和党人控制的两个极容易组织起来向华盛顿进军的州长职位——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门罗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托马斯·麦凯恩已经采取措施,筹建他们各州的民兵组织以采取有效的行动。虽然联邦党人的报纸叫嚣要“武装马萨诸塞州的六万民兵以摧毁那些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外国人或者弗吉尼亚的一些气势汹汹的滋事者所形成的力量”,但鞭长莫及,新英格兰离得太远。对于联邦党人来说,更为不幸(却是美国的幸运)的是,本来在美国与法国冲突之际,汉密尔顿曾想组建一支常备军由他亲自指挥以应付法国可能的入侵,但由于亚当斯跟法国达成了和平协议而使这一动议搁浅。
在经过35轮投票后,杰斐逊一直以8票领先于伯尔(6票),那时共有16个州(两个州因两人得票持平而弃投),杰斐逊没过半数。此时,特拉华州的唯一的众议员联邦党人詹姆斯·贝亚德站了出来。如果继续僵持下去,一旦发生内战,特拉华州将成为战场,这是这个小州无法承受的,据说其通过私下与杰斐逊谈判,贝亚德在第36轮投出了支持杰斐逊的关键一票,使危机得以化解。
经过这一次争议以后,美国的国会开始修改宪法,增加了第12修正案,主要是解决总统和副总统分开投票问题,总统就是总统,副总统就是副总统,以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但这并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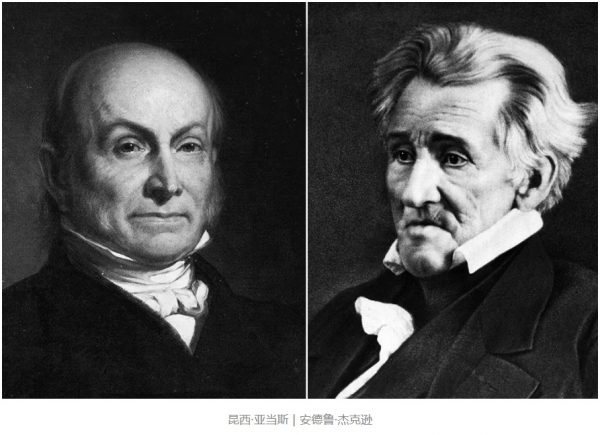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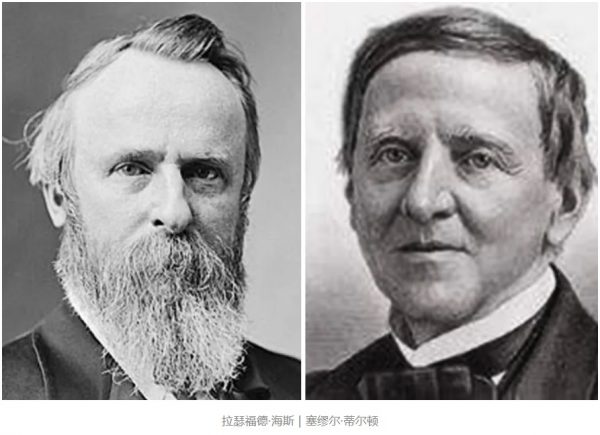
第三次是1876年民主党人蒂尔顿与共和党人海斯竞争。蒂尔顿的选票多出海斯25万张,他的选举人票也多,获得184张选举人票,海斯是165张选举人票,但蒂尔顿落选了。奇怪蒂尔顿为什么会落选?因为他差一票(185票)才能过半,这个时候出现了争议。当时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南方党争激烈,南方的四个州(南卡罗莱纳、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报来的选举结果报告都有两份。本来,按照宪法规定,要有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在两院全体会议上当众拆封,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但现在,如果由他来决定,肯定选择有利于自己党(共和党)的报告(当年杰斐逊作为参议院议长拆封宣布佐治亚州不太合规但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报告有效,避免了更复杂化的局面的出现);如果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决定,则肯定是蒂尔顿当选。于是国会就组成了一个15人(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各派5人)的选举委员会(其中,民主共和两党各7人,无党派的大法官1人),进行投票,1877年3月2日,离总统宣誓就职仅剩两天,委员会以8:7裁定,海斯获得四个州的选举人票,以一票之先当选总统。
民主党在南方占多数,选举结果不利于南方,然而南方为什么会接受这一结果?因为他们达成一项肮脏的交易,总统给共和党的海斯,但是北方军队撤离南方,结束南方重建和对黑人的保护。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两党“妥协的真正受害者是南部的黑人,因为它正是以他们为牺牲品而达成的,从而使写入第14和第15条宪法修正案的各项保证的实际施行,延迟了三个世代之久”。
为了弥补这一宪政漏洞,1887年国会制定并通过了《选举人票计算条例》,规定某州的总统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时,州立法机关应在选举团正式投票选举总统的前一个星期,按大选前制定的选举规则,解决争议,产生该州总统选举人名单,以免把矛盾推给联邦国会。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期”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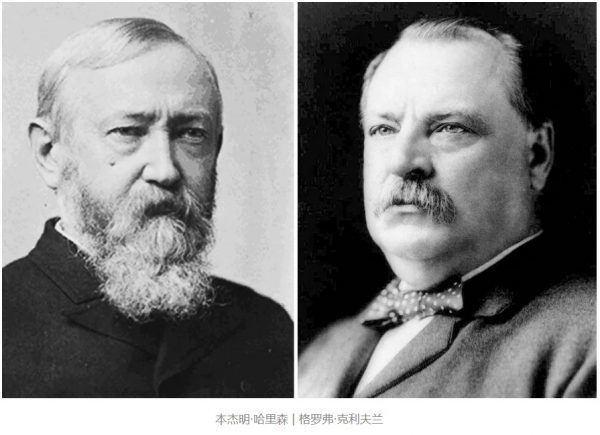
第四次争议出现在1888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与共和党人哈里森竞选时。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得了5540050张普通票,168张选举人票;共产党人哈里森得了5444337张普通票,233张选举人票,哈里森当选,受伤的又是民主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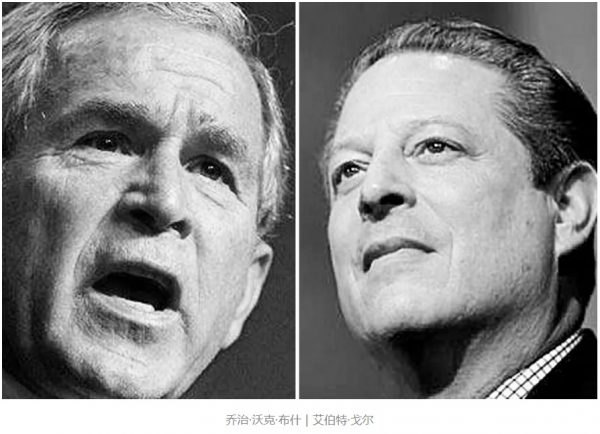
2000年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竞选总统,戈尔的普通票多出了53万张,这不是个小数,但小布什以271张选举人票微弱多数当选美国总统。
国内有些反美人士曾经说,美国也是世袭制,因为老布什当完总统,其儿子小布什继续当,这种说法很无聊。戈尔跟小布什一样,也是政界元老的后代。小布什的爷爷是康涅狄格州国会参议员,父亲老布什是两届副总统加一届总统,小布什本人干了好多年德州州长,干得不错;戈尔的父亲是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戈尔本人的政治经历也非常辉煌,28岁当选众议员,后来当选参议员,当过8年的克林顿的副总统,不管是出身还是个人的经历都不输小布什。
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导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使得总统竞选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摇摆州。对于深红州和深蓝州,基本不存在竞争,比如纽约等这些大州,是民主党的票仓,有些州则是共和党的票仓,因此这些州也就没有多少竞选的价值。民主党票仓主要是北方几个比较开明的大城市,共和党的票仓主要是西南方向这些偏远的落后的小州。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受伤的都是民主党现象?因为大州是民主党的票仓,民主党在总人口上是占优势的,而小州在选举人票上占优势的,至少每个州都有两个参议员席位。
2000年大选前,双方算来算去,有三个摇摆州最关键,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11月7日计票开始,选举结果很快出来了,双方都拿下了自己的“票仓”和预计获胜的州,同时戈尔拿下了宾州和密歇根州,如果再拿下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将入主白宫。计票截止日东部时间晚9点,媒体报道戈尔获胜。正当民主党欢庆的时候,10点多,媒体宣布数据有误,佛罗里达是未定之州。到次日凌晨2点,CNN宣称小布什赢得佛罗里达25张选举人票,最终获得271张选票当选。于是戈尔打电话祝贺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然后驱车前往田纳西州州议会大厦,准备公开认输。此时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民主党人)给戈尔打电话,通知他先不要急于认输,因为两人得票差距不到0.5%。按佛州法律,如果两个人的选票差达不到0.5%,可以重新计票。戈尔立即给小布什打电话,称现在不承认败选,要重新计票,刚才的祝贺作废。
11月8日下午,佛罗里达完成了67个县的计票工作:在大约6百万张选票中,小布什赢了2909135张,戈尔赢了2907351张,其他候选人赢了139616张,小布什仅比戈尔多得1784张。票差不到0.03%。按照法律规定,各选区(县)选举委员会必须重新机器计票,另外,候选人有权在选举结束后72小时内提出人工重新计票的要求,由县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可行。11月19日,经过机器的重新计票,小布什比戈尔只多327张票,这下戈尔更不甘心了。于是戈尔方面要求对棕榈滩县等若干属于民主党势力范围的选区进行人工计票。
对于佛州的重新计票,小布什阵营非常不满。11月12日,小布什方面向佛罗里达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法院下令停止人工计票,但地区法院以人工计票属于州法管辖范围,联邦法院不能随便干涉为由,拒绝了小布什方面的要求。小布什方面决定向在亚特兰大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16日,该院以相同理由驳回。
佛罗里达州务卿、共和党人哈里斯女士宣布,11月14日(当选结束后第7天)是各县上报选举结果的最后期限,逾时概不接受。对此民主党人难以接受,因为棕榈滩等县的人工计票刚刚开始,不可能在法定时间内完成。棕榈滩等县向州法院申请宽限被驳回,它们立即上诉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决前签署任何选举结果。此举终于成功。11月20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开庭。法庭辩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1)县选举委员会是否可以决定进行人工重新计票;(2)州务卿是否有权拒绝逾期上报的计票结果。
11月21日,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以7:0(法官中有6位民主党人)做出判决:首先,如果机器计票和抽样人工计票的结果出现差异,县选举委员会有权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其次,州务卿的确有权拒绝逾期报来的计算结果,但这一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因为选举权是州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是其他公众自由的基础,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技术性法律规定不能凌驾于选举权的实质内容之上”。为此,它宣布:棕榈滩等县可以继续进行人工计票,但计算结果必须在5日内(11月26日下午5时前)上报州务卿,后者必须将这些结果包括在大选的最后结果中。这一判决显然是民主党的胜利,但是5日内完成几十万张选票的人工统计,谈何容易。11月23日,迈阿密-戴得县选举委员会宣布停止人工计票,因为不可能在5日内完成计票工作。对此,民主党方面立即向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其下令该县立即恢复人工计票工作,被驳回。截止到11月26日,只有一个县完成了人工计票。当晚,州务卿哈里斯正式签署了佛罗里达选举结果:布什赢得2912790票,戈尔赢得2912253票,布什领先537票。哈里斯拒绝了迈阿密-戴得和棕榈滩县的计票结果(戈尔在两县分别净增加168和215张选票),理由是前者报来的只是部分统计结果,后者则超过了截止时间。民主党不服,向佛罗里达巡回法院提出紧急请求,要求下令哈里斯接受上述两县的计票结果,并命令迈阿密-戴得县完成人工计票工作。法院作出判决:下令两县将争议选票运到法院备查,但没有同意恢复迈阿密-戴得县的人工计票。
戈尔方面又把这个要求上诉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12月8日,最高法院以4:3推翻了佛罗里达巡回法院的判决:棕榈滩的计票结果和戴得县不完整计票结果都应该包括在最终的统计结果中(这样使两人票差缩小到154票。);另外,下令在全州范围内人工统计6万张漏选票。
布什团队立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推翻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以5:4否决了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维持佛罗里达巡回法院的判决。简言之,最高法院判决小布什赢得了大选。5:4阵营是这样划分的,投否决票的5个人中,有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斯卡利亚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这三个是保守派的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和奥康纳大法官是中间偏右的大法官,所以他们支持了共和党。理由之一,计票时间远远超出了1876年的《选举人票计算条例》规定的时限;理由之二,要求对作废票进行重新审核并没有统一标准,违反了第14修正案平等对待的条款。对立阵营中4位开明派大法官,是史蒂文森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苏特大法官。开明派的理由一,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有权对佛罗里达的选举法进行解释,而联邦最高法院无权干涉州最高法院对本州司法的解释。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并没有创设新法,只是在执法。理由二,选举的制度就是由各州各县自己来决定的,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要求有统一标准并且平等对待,是很荒唐的;所以,要求维持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持续了36天的纷争,终于在2001年1月6日结束,尴尬的是由美国参议院议长戈尔宣布竞选结果,小布什以271票当选美国总统,这就是布什诉戈尔案最后的结果。
于是问题出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不该干涉美国的总统选举。最高法院是是唯一非民选的机构,是总统任命的,是最没有资格干涉美国总统选举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先例,它们一般是只涉及司法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因为政治是民主;虽然参众两院的选举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单一选区的格里蝾螈问题,但毕竟是民选,而最高法院不是民选的,最高法院只是执法,只是解释法律。在美国的传统上,即使最开明的沃伦法院时期,也基本上不插手美国的政治,只是对宪法进行解释,进行司法审查。
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是一个保守派,伦奎斯特法院是个保守法院,保守派更强调州权,更应该尊重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布什诉戈尔案被大家认为是违反了保守派自己的司法理念的一个典型案例,原因可能是:一,这些保守派大法官本身是共和党任命的。二,他们面临着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接任者将会由新任总统任命,这涉及未来最高法院将是一个保守的最高法院,还是一个开明的最高法院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党争,就是政治。而我们知道,开国先贤们在费城立宪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美国政党政治的,在总统选举制度设计上注重了对民粹的防范,却忽视了党争的危险。这就要求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应该尽量远离党争,保持专业与独立。虽然最高法院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去化解一场宪政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福是祸,实难定论。因为,选举人团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宪政危机是如此明显,已经不是一个宪法解释或司法审查的问题。不管是1800年杰斐逊与伯尔之争,还是1876年蒂尔顿与海斯之争,危机过后,国会都及时对宪法进行了修正或立法补救;但小布什和戈尔之争由最高法院解决,使得民选议会并未承担起宪法创制的责任,去解决这一宪法危机。布鲁斯·阿克曼谈到美国为什么可以屡屡化解宪政危机时,把原因归结为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幸运;而这一危机在不久后的2016年总统大选中,以一种更为严重的姿态重新出现,不知道未来的政治家是否还有这种超凡能力,亦或幸运继续降临美利坚。

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65853514张普通选票、227张选举人票,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获得62984828张普通选票、304张选举人票。后者当选,前者多出接近290万张普通选票却落选。仔细注意一下会发现,两人选举人票之和531张,并不等于总票数538张。少了7张?这就是所谓的“叛票”——选举人没有投给赢得选举的候选人,而是投给了别人,比如本是希拉里的票却投给了桑德斯。这岂不荒唐?但竟然合法。开国先贤设计选举人团制度本来是信不过民众,但现在却是你要不要信任选举人团的“精英”的问题。川普是人民选出来的吗?当然是,是美国46.1%的人民选出来的,同时也是48.2%的美国人民反对的(明确支持希拉里)。但问题在于,这46.1%,可能就是开国先贤最信不过的那一部分。川普上任后的所作所为及其最近应对疫情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选举制度带来的宪政危机,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选举人团制度的问题出在哪?
首先,从以上分析来看,美国开国先贤设计的这种间接投票,其目的并未实现,带来的一个直接效应却是对民意的极度扭曲。且不说选举人票数与按比例的普通票数的巨大背离;更为严重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的出现,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使得两党竞争战场主要设在了几个人口较少的摇摆州,使得深蓝州、深红州都没有太多争夺价值。也就是说,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成比例的主流民意,而是摇摆州的“权重”民意,这样选出的总统就可能不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这就是哈耶克所担忧的“少数暴政”现象。川普就是一例。美国是一个以自由理念普世价值(决不是基督教)为立国根基的国家,但川普代表的显然是一种白人至上宗教极端主义和市场原旨主义的极右保守主义思想谱系,这不仅扭曲了美国价值观,也影响了包括中国思想界在内的世界思潮,贻害无穷。而这些保守势力看中的是总统通过任命大量保守派地区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实施更长远的社会控制。
其次,这种赢者通吃的选举模式固化了前一缺陷,也固化了两党制,使得美国政治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妨碍了多党竞争。如果前一缺点是对主流民意的歪曲的话,此一缺陷恰恰是妨碍了多元化民意的政治表达。因为如果按比例计票,可能会有第三党或者独立候选人当选,如果州与州之间累加,可能在某个州第三党都是相对少数,但由于两大党竞争激烈,这个州共和党相对多数民主党是极少数,另一个州民主党相对多数共和党极少数,那么第三党或者独立候选人就可能变成第二候选人,全国的计票结果很有可能超过第一名,当选总统。但是按照现在这种赢者通吃的计票模式,票数不能累加,第三党或者独立候选人就无法当选,因为你在几乎任何一个州都不会是第一,这样就使得美国永远是两党制。
综合以上两方面,随之而来的就是,由于主流民意的沉默和其他选项的阙如,党争造成的极化成为趋势,社会认同也会出现极化或者撕裂;而反过来,要想赢得选举,必须尽量争取极端选民。一个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依赖于拥有一个庞大的温和、稳定的中间群体,两极化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社会严重撕裂和极化,是产生狂热分子的温床,同时也就成了煽动家引领民粹的战场。川普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恰恰违背了开国先贤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所以,布鲁斯·阿克曼认为,这是“建国之父的失败(阿克曼书名)”。
 [美]布鲁斯·阿诺德·阿克曼
[美]布鲁斯·阿诺德·阿克曼
Bruce Arnold Ackerman,1943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危机?或者回到前面我们的问题,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司法审查解决类似危机是否是长久之策?
多年以来,在研习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个疑惑,作为自由主义者,我赞同自由价值的优先性,特别是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必须得到宪法的保护,不可商讨,当然不可以通过民主投票以多数名义随意剥夺。但同时,宪法的最终权威来源于哪里?当然是人民,人民主权,这是民主的第一要义。这是一个终极价值的悖论。
民主一元论者与权利本位主义者的矛盾不是不可协调的,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就试图协调二者的矛盾。在阿克曼看来,对于常规政治时期,也就是两次大选之间或者没有宪政危机的常规选举中,民选的议会履行常规立法的任务,甚至公民在选举中可以不用过于积极地参与,更多的是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最高法院则以其宪法权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时权利本位主义的权利优先理念得以实施。但如果出现了类似于南北战争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重大宪政危机,人民就要出场承担起积极公民的角色,行使人民主权,通过选举使自己的代言人进入国会,行使高阶立法权,不但可以废除旧法,而且可以创制新法。这时候最高法院作为非民选的机构,必须服从人民的权威。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走到今天,以290万张选票的误差,让46.1%的人民的意志凌驾于48.2%的人民的意志之上,选出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总统,不仅仅破坏了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正在侵蚀美国的价值观,这既说明了美国的撕裂和极化,也说明了选举人团制度的失败。怎么办?一切取决于美国人民。2020年11月份的大选,美国人民需要出场,用自己的选票向保守主义者和川普说不。人民从来不是一个集体概念,只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单凭个人却无法从现有法律得到救济时,他们就用选票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我们(合众国)人民。
我相信美国的未来,但对于最近期的未来信心不足。因为布鲁斯·阿克曼的理论仍然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愚蠢怎么办?那只有靠文明去战胜愚昧,这是人类长期的艰难使命。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