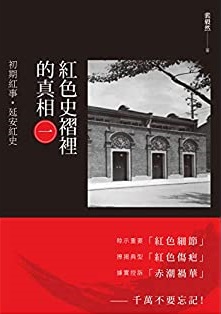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2)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2)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延安论争
1938年1月5~25日,梁漱溟以国防参政会参议员身分考察延安,与毛泽东前后谈话八次。除两次不甚重要的宴会与送行,其余六次谈话,每次至少两小时,最长的两次通宵达旦,从晚饭后直到黎明。所谈内容自然是当时最紧要的中国前途。而欲探讨中国之明天,必然牵涉到对中国昨天的看法。「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梁漱溟自述》第181页)正在这一点上两人分歧重大,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不同点。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及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且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触生,而非内部自发,此特殊性即由中国老社会之特殊构造而来。毛泽东同意梁漱溟以上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但他强调的是中国社会还有其一般性,即与西方近代社会的相通处,阶级压迫方面存在共同性。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重视特殊性而忽视一般性。梁漱溟则坚持己见:「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同上)两人各持一端各执一词,争论没有结果,握手而别。
梁漱溟强调特殊性,意在劝阻中共放弃对内的武装斗争,走和平宪政之路。因而,梁氏此行之旨即在于考察中共,想看看「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毛泽东坚持一般性,实在于为阶级斗争立说。从逻辑上,只有坚持中西社会的相通性,俄法革命的阶级说才能顺理成章地引进并运用之。否则,中西社会本不同质,医治手段又如何一致呢?表面上的形而上之争,实质意在形而下。双方都十分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故而针锋相对不予相让。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他当然强调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1]
不过,令我难解的是既然都明白对方不肯稍撤半步,又何以如此认真像煞有介事探讨个没完?这里,是不是双方还真有那么一点书生气,将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了?毛梁同年,其时均为45岁,已相当成熟,总不至于在那儿长时间玩虚。因此,很有可能两人都真诚地认为对方错了,是认识上错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现实政治的制约。阶级斗争乃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共「一大」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写入党章的。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岂不是抽去共产党赖以存身的基础?毛泽东之所以死死守住「中国问题的一般性」,对他来说,实在是形格势禁,不得不然。设若后退一步,可谓万丈深渊矣!如果承认了梁漱溟的「中国问题特殊性」,承认了梁漱溟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并非截然对立,又怎么谈得上下一步的苏俄为师,实行阶级颠覆,行无产阶级专政?又怎么照搬马恩理论,搞阶级斗争?因此,梁漱溟谈的是纯学理,毛泽东坚持的则是政治。这就是所谓学者与政治人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角度,即合乎中国社会现实角度,自是梁近而毛远。
这一场争论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甚多,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兼容梁漱溟。从历史角度,被动方的梁漱溟就是错了,也只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主动方的毛泽东,因是实际治国者,影响就大了。若毛泽东能考虑到梁氏所说的中国的特殊性,至少有可能避免1950年代的“全盘苏化”,有利于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经过50多年的历史检验,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提出「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便是历史对梁论有力印证。更何况从哲学上来说,差异是绝对的,中国社会又如何能全盘照搬人家的西方模式?从绝对意义上,强调共通性总不如强调特殊性更为实际,更容易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症结。尤其对毛泽东来说,多考虑一点特殊性,政策的制定也就多了一份现实针对性,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之路也就有可能避免一些曲折。
不过,政治人物的毛泽东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坚守逻辑的整体性,「此一时彼一时」的实用主义乃是其最大的原则。1959年,当张闻天要求「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强调必须尊重经济工作的普遍规律,即强调经济规律的一般性以纠正左倾虚热症,毛泽东此时则反过来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不承认什么一般性了。
比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差异生发惊讶与兴趣,亦在于对相同处带来的思考,更在于异同之中所寄寓的意义得到抉发与揭橥。读史鉴今,此之谓也。
[1] 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参见《梁漱溟自述》,页296。
2001年 上海·国权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