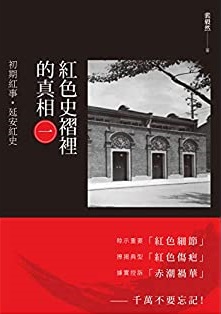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7)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7)
一桩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1942年9月,延安众多学院之一的自然科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前身),因种种原委未组织人马夏季烧炭。中秋将临,冬天已近,学校财政枯乏,无钱买炭,于是发动群众,全校师生停课一周,外出「搞生产」——搞钱以购越冬木炭。
学校教员大多为来自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学部与预科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总共六七十人,补习班学生占大多数,年龄14岁上下,且多为女生。除了组织一批学员上被服厂打工,搞钱的门路很有限。
医训班学生、缅甸归侨马兴惠(1916~ ),1938年底赴延,最初服务于延安东面40公里的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这次决定上那儿想想办法。临行前,向校总务科借了一条扁担、两只草编笼子,再向新巿场贸易公司经理借了六万法币(延安亦随全国通货膨胀),加上自己的两万元,离开延安南门外杜甫川的学校,上路了。途经盐站,突然决定买上盐带去,或许能赚点钱。于是,他用八万元法币买了100斤盐。百步无轻担,何况百斤之担,走出不远就大汗淋漓,接着疲劳饥饿,最后简直迈不动步,走一小段路,就得卸担歇息。从日出走到黄昏,仗着年轻,总算到达甘谷驿兵站医院。
医院里的老熟人热情接待他,可马兴惠关心的是盐价,得到的却是一盆从头淋到脚的凉水:「这里的盐比延安还贱,你要卖给谁去?」啊唷喂,不仅一天的拼搏付之东流,还要蚀本哩!医院里的人议论纷纷,非常同情,最后总算以原价留给医院,保住老本。医院上下,从首长、医生到护士、炊事员七嘴八舌劝他休息几天,回延安另想办法「搞收入」,只有个别人建议他再往前赶一站,上延川县轧轧苗头。马兴惠不甘心空手而回,接受了这一建议。
次日清晨,大睡通宵的马兴惠醒来,四肢疼痛,挣扎爬起,吃过早饭后没精打采地向延川走去。走出没多远,一中年男子挑着重担走来,样子比自己昨天还狼狈。两人交会,汉子停担,喘着粗气哭着央求:
同志,你在干什么?能不能帮我把这担鲜葡萄卖给医院?
马兴惠回答:八路军的医院,谁能有钱吃得起葡萄啊?!
但此人像抓住救命稻草,让马兴惠坐下,倾诉其苦。原来,他是离此三十里延长县农民,家在延河边,院中两株葡萄树,没舍得上当地集巿,等着中秋节运到延安卖个好价钱。今天阴历八月十四,夫妇俩清晨即起,小心翼翼剪下葡萄,就在夫妻俩抬着驮筐往驴背上放时,不小心碰着驴屁股,驴子受惊跑了,夫妇放下驮筐追驴,不见驴影,老婆央求邻居寻驴,他则揣几个馍馍挑担上路,生怕葡萄烂掉。他说这挑担子足有120多斤,自己从未挑过这么重的东西走长路,看看太阳,估摸已走了四小时,才走了三十里,已是苦不堪言,可距离延安八九十里,实在挑不动了,既担心这担葡萄卖不出去烂掉,损失大大的,更惦着家里驴子是否找回。他苦苦哀求眼前这位「八路」替他想想办法。最后说:
不行,我情愿不要葡萄了,也得回去找驴子。你能不能把这些葡萄买下?
马兴惠:八路军没钱,买不起这么多。
农民:这也没过秤,集上没货也没个价,你到医院里去看看,借着多少钱都行。
马兴惠:借不着的,我昨晚送了一担盐来,医院里许多人费了好大劲才凑给我八万块。都给了你,我今儿一天的饭钱也没有了。
农民一听他有八万元,高兴了,追着求着:
好同志,多少就八万元吧!我还有几个干馍,你带去路上吃。
马兴惠发慈心:这东西值多少钱我也不懂,看你急成这个样子,我就帮个忙,要下试试吧。
于是,交了钱,两人对换筐担,「八路」马兴惠再次负担上路,当然掉头向延安。为了赶中秋市场,也怕葡萄烂,他没进兵站医院,直接赶路。这挑葡萄加上筐,足有130斤,比昨天的百斤盐担重得多,也是一开始还行,越走越重,及至中午,太阳当头,大汗淋漓,实在走不动了。幸好在延河边,找个阴凉处,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喝着延河水啃完那几个干馍,检查一下葡萄筐,舍不得吃整串葡萄,只吃了碰掉的几粒,哇!真甜!咬牙挑起担再上路。
上午走了40里,下午体力更差,每走二里就得歇担大喘一阵,走十里则要「大休」一阵。「大休」之时,他趴在路边,给自己「充电」——掏出日记本挣扎着写一段,用得最多的词儿是「坚持」、「拼搏」,最起作用也是最后一句:「坚决完成学校任务!」
终于,马兴惠顽强到达杜甫川,肚子饿瘪、汗已出尽、力已衰竭、浑身发抖。此时,天已乌黑,窑洞灯光多数已灭。幸好一位同班同学外出归校,替他挑担上山回宿舍。不过一里多山路,这位同学歇担数次。马兴惠:「我实在没有本事再客气地说一声『让我挑吧』!」
学校晚饭时间早过,马兴惠只得空肚一头倒下,立即昏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宿舍里空空荡荡,同学们都外出了,早饭时间已过。马兴惠饿着肚子咬牙忍痛挑担上街,勉强挨到新市场沟口,喘息未定,一位穿着地方制服的中年男子走来:「你这葡萄是卖的吗?」马兴惠点头。「多少钱一斤?」
马兴惠因不知行情:没价,多少钱都它,独一份!
来人亲切地:好好说,我都要了!
马兴惠编著说:你看值多少?这是我从200里外的延川县担来的。
中年男子:这东西确实没价,延安多年都没见过了。我是边区交际处的,来了外面客人(按,可能榆林新一军长邓宝珊和西安国民党人物),咱们商量作个价,好不?
马兴惠也老实交底:好吧!我是杜甫川自然科学院的学生,干这事是领导动员搞生产,为买过冬木炭的。
对方:时下一斤猪肉2.7万元,这一斤算两斤肉钱,怎么样?
这么高的价,大大出于预料,马兴惠有点懵了,却故作镇静:
太少,几百里路担来,你雇个毛驴,也得给来回四天的运费!
对方:那就一斤给你六万元,再贵我也不敢买了。
马兴惠见好就收:你是给公家买的,我是给公家卖的,我们是给公家办的事,同意你说的了。
那人转身向商店借来一杆大秤,果然130余斤,两个筐算十斤,按120斤成交,马兴惠挑担送到交际处。开收据时,那人说:
你太辛苦了,又给送到门上,条子就写730万元吧!(多给十万)
然后,他从金库领出七八捆崭新法币付给马兴惠。
一趟买卖净赚91倍还多,短短一天,八万成了730万!出了交际处大门,马兴惠高兴得忘乎所以。临近中午,两顿没吃了,路过新市场,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买了一斤粘糕、一大碗羊杂碎汤(公家人一般吃不起这两大件),美餐一顿。回到学校,放心松体纳头再睡,又是一昼夜!醒来时,同学们又都外出了。马兴惠独自在铺上思量,虽说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但还有五天时间,似乎还可「发展成果」。想到甘谷驿医院接受伤兵,熟人多,可能会有人帮着想法赚钱……四下无人,大主意只能自己拿,担上筐又上路了。
毕竟二十来岁的青年,两顿饱饭加上胜利喜悦,浑身都是劲。肩腿还有点疼,已不在话下,健步如飞,过甘谷驿时,他改变主意,没进医院,直奔延川县。翻过雁门关山,赶到石头河时,已是农村入睡时刻。他叫开骡马店大门投宿,次日黎明上路,下半晌赶到延川县拐昴村赵老二家,1939年他收伤兵时住过的房东。老房东见了他很高兴,说你上次不是给老侯家闺女治过病吗?如今她招了个绥德养老女婿,开了油坊,榨磨些香油、做些绿豆粉丝,日子过得不错。那闺女总说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咧,明早我就去把她叫来看你。
第二天上午,老侯一家男女老少五口人都来了,一阵亲热问候,打问这次来意,马兴惠实话相告「搞生产」,老侯便说那就拿些咱家的油和粉丝。四十斤小磨香油、四十斤打好捆的绿豆粉丝,就算他们家感谢马医生的救命之恩。马兴惠说八路军有纪律,再说送这么大的礼也不敢收,至少得给成本价,这都已是对他的极大支持了。最后,硬塞给80万,老侯勉强收下。
这次,他挑着80斤担子上路,比前两次的担子轻松多了。200里路,不到两天就到了。进了延安城,太阳还在西山顶上。他挑担径直走进边区交际处,找到那位买葡萄的同志:
我是个医生,两年前救活了这家病得快死的独生女,这是他家为感恩而送我的「搞生产」,我象征性地硬丢下八十万原料钱,你看看作个价留下吧。
此人是交际处专搞物品的大内行,一看便说:
这两样东西都是延安的高档缺货,多年都见不到了,且质量特别好。边区干旱,不种芝麻,芝麻都是从河东运来,香油贵贱买不到哩!这样吧,油每斤给你按四斤肉钱算,粉丝作油的半价,斤量就你说的数算账。我不能拿公款送礼,但也不能亏坑什么人,尤其像你这样好的大学生。
如此这般,马兴惠又捧着650万元出门。
650万+730万=1380万!扣除本钱、伙食费、路上所丢同学的钢笔(赔款十万),马兴惠上缴1300万元——五头大肥猪之价,这次全校「搞生产」总收入亦未达此数。
然而,好事难做,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正当马兴惠庆庆幸斩获颇丰,喜滋滋等待表扬,校内传出闲言碎语,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怎么就他一人能耐?短短一周搞来这么多钱?马兴惠在正式上交钱款时给院长徐特立写了「情况汇报」,简述这次「搞生产」过程,信和钱款一并由党支部转呈学院。
马兴惠所在支委开会专题讨论马兴惠「搞了大钱」,有人认为「方向」不对。支委在上缴钱款与马兴惠给徐老的信时,附上支委这一讨论意见。学校领导层也有议论,班主任与总务科长将他叫到办公室核实情况,「我自然感到压力,胜利的喜悦被一扫而光。」
这边正在「核实情况」,那边徐特立捏着马兴惠的信来了,班主任还未汇报完毕,徐老摇手打断:
我派去边区交际处的同志回来了,情况和这信上写的完全一致,人家十分夸赞学校和这个学生,感谢给他们解决了招待贵宾的困难。而我们自己有些人则说长道短,全校学工人员,在这次生产中,谁曾爬山走过几百里路?谁曾出过那么大的力,流过那多么大的汗?谁曾上交这么多的钱?这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好事还是坏事?难道还不清楚吗?!古人都主张「是是非非」,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是非分明,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马兴惠站在一旁,感动得热泪直流,徐老用衣袖替他擦拭。
我赶紧躲过,并且深深一鞠躬之后离开了。[1]
这则资料乃当事人马兴惠五十年多后的回忆,题名〈徐老断是非〉。可见,马兴惠在乎的还是五十年前的「是非」。笔者读之,感慨甚多,分述如下:
一、延安自然科学院之所以出现质疑「方向」的声音,乃是对商业的鄙视,对「暴利」难以接受。质疑者看来,这不是「投机倒把」么?「搞买卖」能等于「搞生产」么?不靠生产得来的「利润」,其它都是歪途,除了剥削岂有它哉?!可见,当时延安思想界已对商业发生根本认识上的偏颇。「方向」之争实为此后全国严禁私人行商之先兆。徐特立能断一事之是非,却无力阻止此后全党整个「方向」之是非。
二、农民求卖葡萄、老乡平送油粉、交际处感谢购得缺货,挣了大钱的马兴惠除了大苦大累,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撞大运撞出来的「利润」。于乡农于学校于交际处,三方各得其利,皆大欢喜,何有什么「方向」问题?这方向哪来的?符合谁人利益的「方向」?还不是根据教条、根据那些马列名词——「剥削」、「投机倒把」。众所周知,2009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正式从法典中摘去「投机倒把」。[2]五十多年呵,这点认识上的进步不容易呵!
三、退一万步,就算马兴惠「搞生产」手段有问题,但他上缴96%的利润,按说也能证明「无私」,不说捞好得表扬,至少不应受怀疑吃批评吧?吃了大苦、赚了大钱,竟要流大泪,好人伤身又伤心,说明什么?当然是红彤彤的延安逻辑出了问题。奈何当时延安人难以发现耳。而且,五十年后的马兴惠,在忆文中也不明白悖谬何在,说明赤左思潮严重拧歪延安一代的判断力,连常识都弄不清楚了。徐老为小马的辩护,仅仅根据「无私」,而非认识到「手段」本身其实也没问题。商业使各地互通有无,物尽其用,利尽所归,流通也能创造价值。延安红色意识形态的这一偏差,乃是日后出现「三大改造」、「投机倒把」的价值基础。
四、延安那会儿物流极其不畅,生意太好做了,百里之遥,商利至少五倍。一个学生,手持八万,短短六天,来往两趟,获利162.5倍,今日商人还不羡慕煞?!再次证明:要想富,走商路。只要赶上了,真的可以空手套白狼。后来,「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都「公」了、无私了,乡农倒是不被「剥削」了,但他们栽种的农副产品也无法变现。因为他们不能上市场去卖,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全国商业因缺乏竞争而一家独大,懒散蛮霸,不仅全国无商不活,乡农的日子反而越过越穷。农民当然会算帐,权衡利弊,当然宁可受「剥削」也要将东西卖出去,多少能得一点。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么?要求商人一个个都做「活雷锋」,几人能长年坚持?再说运输销售都要成本,亏本生意谁做得起?况且,要求商人无利,不也是对商人的剥削么?而没了商人,各地之间如何互通有无?如何物流其畅、物尽其用?这么浅显的ABC,中共政府竟需要40年时间才「觉悟」,要邓小平「九二南巡」才结束绕死人的「社」「资」之辩。
马兴惠好心无好报的延安「仇商」故事,凝聚了十分典型的延安风味,可咂出许多来自革命源头的滋味。西汉《盐铁论》(桓宽):「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两千多年前古人对商业的认识都高出一大截呵!
2009-8-28于沪
[1] 马兴惠:〈徐老断是非〉,载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150~157。
[2] 〈「投机倒把」将成历史名词〉,原《解放日报》(上海)2009年8月25日。《文摘报》(北京)2009年8月25日摘转。是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四部法律中删去「投机倒把罪」,「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原载:《档案春秋》(上海)2010年第7期
转载:《特别关注》(武汉)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