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胃
民以食为天,提起吃,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兵团初期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伙食费是每人每天四毛五。按说这个标准比当时大多数家庭还要高些,可是由于物质匮乏,吃不到什么东西。早饭似乎永远是被称为老三样的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为了把这个东西吃到嘴里还很辛苦,每天必须早早起床,集合好队伍浩浩荡荡来到食堂。如果饭还没做好,大家就一起用饭勺敲打饭盆,搞得噪声大作以示催促。后来就有了新章程,到食堂后不准敲饭盆催饭,要高唱革命歌曲,真是应了那句饱吹饿唱的俗话。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养成了基本不吃早饭的习惯,还引经据典地宣扬什么“废朝食”的益处,其实就是嫌麻烦,反正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还不如睡懒觉。
兵团初期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伙食费是每人每天四毛五。按说这个标准比当时大多数家庭还要高些,可是由于物质匮乏,吃不到什么东西。早饭似乎永远是被称为老三样的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为了把这个东西吃到嘴里还很辛苦,每天必须早早起床,集合好队伍浩浩荡荡来到食堂。如果饭还没做好,大家就一起用饭勺敲打饭盆,搞得噪声大作以示催促。后来就有了新章程,到食堂后不准敲饭盆催饭,要高唱革命歌曲,真是应了那句饱吹饿唱的俗话。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养成了基本不吃早饭的习惯,还引经据典地宣扬什么“废朝食”的益处,其实就是嫌麻烦,反正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还不如睡懒觉。
中央1956 年制定过一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1967 年之前,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要达到400 斤。为了上纲要,大家都去种产量高的玉米,结果人们的口粮中棒子面要占60%至70%。有些荒诞的是,一旦遇到灾害,玉米减产,反而可以吃到一些进口的加拿大小麦。当时中国一再向全世界宣称粮食自给自足,因此不能说进口粮食,只能说进口饲料。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很愿意享受牲口待遇,这点觉悟大家还是有的,更何况有细粮吃。一些人(包括我)的头脑中甚至掠过希望灾害继续发生的私字一闪念。
至于小麦究竟是人吃还是牲口吃,加拿大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是不能让中国人用进口的小麦来当种子,据说为此对出口中国的小麦进行了专门的处理,好像是抽掉了什么东西,结果营养要差不少,这种做法也太不白求恩了。
还有一个更坏的国家,竟然把真的用来喂牲口饲料卖给中国人民吃。那种玉米面是白色的,蒸熟了以后颜色像白面馒头一样诱人,模样却像一摊牛粪,吃起来黏糊糊的。这倒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经常吃到发了芽的小麦磨出的面粉,同样难吃,但糟糕的是吃了那种进口的饲料后很容易蹿稀,一时间团卫生队人满为患。

我们还吃过90 粉和全麦粉,同标准粉相比,颜色黑一些,口感有些粗糙,由于被算作粗粮,不占用细粮指标,很受欢迎,这个东西总比棒子面强。
我最不喜欢吃的主食是红薯面窝头,嚼起来像胶皮一样难以下咽,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堵铁水。蔬菜中我最讨厌海带,每年的国庆节一过,就开始了漫长的汤季,几乎天天喝海带汤,喝得大家无精打采,一直要熬到来年春天。好容易去昆区的饭馆改善一顿,木樨肉里也放了许多海带来冒充木耳。食材假冒是包头饭馆的传统,一位老服务员曾告诉我们菜里所谓的玉兰片实际上是苤蓝皮。直到现在,我早已原谅了红薯面,但对海带的厌恶长久不衰,一见到它就会出现历史性反胃。


当然连队也想方设法改善伙食。钢丝面是经常吃的特色食品,用玉米面压制而成,很有韧性,吃得大家腮帮子直疼。炊事班经过反复试验,把两种最难吃的东西红薯面和玉米面按一定比例掺在一起,再做成钢丝面,结果负负得正,口感非常好,很受欢迎。任何年代都有值得怀念的东西,我最怀念的竟然就是钢丝面。现在偶尔吃一次钢丝面或莜面,还要呼朋唤友,场面搞得很隆重。尽管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仍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吃大锅饭的时候,星期天经常要自己包饺子,起初大家很高兴,后来也厌烦了,开始抱怨炊事班偷懒不愿做饭,总让我们自己动手。其实这是解放军的传统,让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的过程中联络感情,促进团结。

包饺子以班为单位,和比赛一样,从领面领馅开始争分夺秒,为的就是早包完早去伙房煮,头一锅用沸腾的清水煮,煮出来饺子不容易破,口感也好,来晚了的只能用剩下的汤煮。有的班没人会擀皮,只好把面擀成薄片,再用茶杯扣出一个个饺子皮,辛辛苦苦包完后,往“汤的汤的汤”里一倒,最后捞出一锅面片。我们班有金占晨这样的高手,不但会擀皮,还会挤饺子,速度飞快。也有赵哲这样什么都不会的。什么都不会也有用,赵哲经常被派去打探各班的进度,甚至被派到炊事班霸占铁锅,不让别的班先煮。他凶神恶煞般往那里一站,还真是起点作用,尤其是女同胞往往知难而退。
我包饺子还可以,中规中矩,唯一的毛病是馅大,其实我也愿意少放点馅,煮起来不容易破而且样子好看,但馅大可以少包几个,比较省事。为此我常常受到指责,饺子煮好后大家又专挑我包的吃,连头也不抬。
有时我们也会搞一点花样,包几个藏有硬币的饺子,平添了不少乐趣。后来发现有些人如赵哲吃得太快,很容易把硬币吞下,于是改用牛奶糖。还记得有一次排长大刘吃到了幸运饺子,正眉开眼笑地接收着众人的祝贺,又咧开嘴吐了出来,原来吃出一块肥皂。
休息日只吃两顿饭,上午吃饺子,下午就吃剩饺子,至于是吃两顿饺子还是两顿面片,取决于煮饺子的先后次序。冬天宿舍里生火炉后,有的班就索性在自己的宿舍里用脸盆煮。大家都知道,脸盆的用途非常广泛,并非仅仅是洗脸。尽管刷了又刷,仍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实在无法接受,索性去昆区下饭馆了。
环境改造人,到兵团没多久,以往一些挑食的毛病全没有了,甚至一些禁忌也被打破。北京知青夏国安是回民,非常老实本分。他偶尔犯禁时会很紧张,有一次吃饭时他发现另一位回民佟广才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吓得头也不敢抬。其实老佟是在搞恶作剧,他自己的碗里就有所谓不洁之物。
记得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包子,一笸箩包子刚抬出来,男生们一拥而上瞬间抢光。女生们起初在一旁讥笑男生,后来发现势头不对,也奋勇争先加入争夺,一位女生甚至被挤到笸箩里。一轮争夺完毕后,喧闹声立刻平息,大家都在专心地享用战利品,空中回荡着上百人同时咀嚼的声音。
小时候看《西游记》,宴席上唐僧嫌八戒吃相难看,要八戒斯文些,八戒回答说“斯文斯文肚里空空”,当时觉得八戒没出息,此时才理解这句粗鄙不堪的真理。再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竟然从这句话中咀嚼出一些意味深长的禅意。俗话说“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有学问的人说“三分勇敢加上七分厚颜无耻可以无往不胜”,都是一个意思,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环境。
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饥饿。由于肚子里没有油水,饭量大得惊人。记得一天早上我把四个窝头放炉子上,转眼就不见了,我大声追问谁把我的窝头拿走了,无人回应。回忆了许久才想起来原来是被自己吃了,吃完后肚子还是空空如也。早饭尚且如此,午饭自然吃得更多,有一段时间我和金沛搭伙,每天中午要吃近三斤炒窝头,金沛吃一会儿就撑得坐不住了,开始拿着勺子转圈,我则勤勤恳恳地吃到锅底朝天。
究竟谁的饭量最大已经无从考证,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的战绩,谁也不服谁。赵哲吃饭不怕烫,谁也比不了,吃的时候被烫得一个劲流眼泪,边吃边拼命吸凉气,荣获敢斗奖应该没有争议。
周经来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经常把两个馒头用力捏在一起,好像在吃一个馒头,效率高又显得很文雅,可以颁发最佳技术奖。

吃得最快的要算李培楠,风卷残云一般,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肉包子才停下来和人争论包子是什么馅。肚子明明已经饱了,还要闹着再溜个缝儿,一转眼又吃进一斤挂面。培楠吃冰棍也是一景,他抱着一箱冰棍,拿出一根横在嘴里,像含着一只口琴,然后轻巧地一拉,抽出木棍,别人刚吃完一根,他已经吞了七八根。
有一次外号“小左”的赵春林饭后和别人打赌,赌注是两斤点心。结果他硬是又塞了几个馒头,赢了之后和输家一起去服务社买点心。过了一会儿他们空着手回来了,大家都等着吃他赢来的点心, “小左”拍着肚子回答说在路上吃完了。身材瘦小的“小左”一战成名,堪称最大的黑马。
吃集体伙食也能长一点学问。人类消化食物究竟要多长时间?大家都说不清,后来吃葱头,就有答案了,厕所里很快就会弥漫着令人作呕的似乎是洋葱炒大便的恶臭,从进口到出口,大约五六个小时。连续吃一个星期的葱头,几十年不愿再碰它,那股独特的恶臭和它换来的学问却永远盘踞在我的脑海深处。
算起来大概有十几年了,每当逢年过节,我就不想吃东西,胃口差了,节日的乐趣也去了大半。在兵团时完全相反,总是无比期待着节日的会餐。大家最喜欢红五月,五一节过后,马上又迎来了五月七日,还可以吃一顿,因为这一天是毛主席发布五七指示的纪念日,也是内蒙兵团成立的日子。
每年的春节会餐是重头戏。兵团刚组建时三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能在春节期间探亲只是少数幸运儿。为冲淡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春节会餐被赋予了特殊使命,有时还会演变成兄弟连队之间的竞赛。
节前好几天,连队就纷纷派出各路斥候,希望搞到其他连的食谱。有人故意夸大敌情,诱使领导拼尽老本,力争以砸锅卖铁之势压倒对方,哪怕节后只能连续喝汤亦在所不惜。

为了迎接这顿饭,有的人从早上就开始尽量少吃东西,腾出肚子,并借用了一个时髦的词“清理阶级队伍”。除夕晚上,全连欢聚一堂,在此起彼伏的欢呼中,一道道菜依次端上,品种丰盛,场面辉煌,不输于为座山雕先生祝寿的百鸡宴。大家横扫过去,只恨自己不能像牛一样有四个胃。这些往日情景,已经化做永恒的口水记忆。
一年里的节日会餐少得可怜,于是催生出一种变态的精神会餐。临睡前躺在床上,大家纷纷谈起自己对最喜爱的美食的深刻怀念和对色香味的细致描述,说得个个馋涎欲滴,在饥肠辘辘声中昏昏睡去。不过望梅并非总能止渴,有时恰恰相反,会促使人一跃而起,采取某些实际行动。
都知道日本鬼子爱抢老百姓的鸡,这种事知青也没少干。杨子荣的唱词被我们改为“这一带常有匪出没往返,番号是建设兵团十三团”,时常吼上两句。昆都仑召离我们很近,是重灾区。有一次一位杭州知青杀了老乡的羊,人家顺着血迹找到宿舍里时,只见到了一堆骨头。一提起我们,老乡就骂“十三团,土匪窝”。
一天夜里培楠和绰号翟子的北京知青翟元彬去菜窖偷菜,扭了半天身体,好容易从门缝里挤进去,忽听一声惨叫,原来里面还有捷足先登者,居然还是位女性。这位巾帼大盗显然受了惊吓,转眼之间不见踪影。培楠和翟子才发现该菜窖早已被人动了手脚,一个洞直通外面,可供梁上君子任意出入。
卿本佳人,也来做贼,时代不同了,贼不分男女,该出手时就出手。
包头知青张成很早就担任班长,是最早入党的先进分子。他有一次和李培楠在果园外窥测,被凶猛的牧羊犬追得抱头鼠窜,一溜烟地逃回宿舍补裤子。
被狗撕咬还不是最可怕的。采石场有炸药和雷管,不难搞到,有人到昆都仑水库炸鱼。水库很大, 防不胜防, 管理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旦发现远处有入侵者举枪就打,也只有这样的疯子才能吓退这群馋鬼。
公共食堂、大锅饭之类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后来兵团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自己花钱去食堂买饭,还可以自己做饭。不少人自己开伙,听说食堂一个晚上曾丢失了二十多把菜刀,连长一咬牙,又买了一百把。
当时许多知青组成搭伙吃饭的“公社 ”,我在兵团当过最大的官就是这样一个公社的书记,虽然微不足道,也可享受叼着牙签指使别人洗碗的特权。杨建国任社长,调皮捣蛋的苑再励被鼓励性地封为五好社员,具有牲口级饭量的李培楠被打入另册,属于被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经常被派去买饭。四类分子真是好使,尤其是食堂卖肉菜时,培楠出马,绝不会空手而归。他能挤能钻脸皮又厚,如果去晚了,就让排在前面的熟人代买,后面的人敢怒不敢言。他偶尔还能用粗粮票买回馒头,不知采用了什么手段。
 由于饭量大,我们吃饭不用碗,用二百二,就是220 毫米口径的锅。吃完饭后也不认真刷,锅里沾了许多污垢,有时竟能磕出一个小锅,我们称之为粘包,本来这个词是指铁水因温度低而凝固在铁水包里。粘包的习惯跟随了我很久,后来在学校工作时,炊事员都认识我的饭盆,一看到这个脏盆就拼命往里装肉,有一次引起一位学生不满,总务处的主任大老李眼睛一瞪,厉声喝道:“你怎么能和刘主任比?他是草原上来的狼!”学生们闻言惊诧,大老李躲在一边向我做怪脸。
由于饭量大,我们吃饭不用碗,用二百二,就是220 毫米口径的锅。吃完饭后也不认真刷,锅里沾了许多污垢,有时竟能磕出一个小锅,我们称之为粘包,本来这个词是指铁水因温度低而凝固在铁水包里。粘包的习惯跟随了我很久,后来在学校工作时,炊事员都认识我的饭盆,一看到这个脏盆就拼命往里装肉,有一次引起一位学生不满,总务处的主任大老李眼睛一瞪,厉声喝道:“你怎么能和刘主任比?他是草原上来的狼!”学生们闻言惊诧,大老李躲在一边向我做怪脸。
我最后一次向人展示草原之狼的风采是1994年,当时单位在国贸参展,中午吃饭时总是吃我不喜欢的涮火锅,我提意见也不被重视,只好想其他办法。有一次我一连吃了二十多盘肉,几乎把办公室主任大郭“吃立了”(即付不起账),凭着这样的实力,以后我终于在吃的领域内有了一点话语权。
比起边疆,内地尤其是北京的供应要好很多,每个人探亲回来都像骆驼一样带许多食品,最少也有四五个提包。糖精、酱油膏一类的东西现在几乎已经绝迹,当年却是很常见的必备品。我最喜欢陈斌儒的母亲做的辣酱,一层浮油下面,深棕色的酱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红色辣椒,散发出诱人的色彩。一勺入口,肉末与熏干叠加出富有层次感的香味,加上恰到好处的辣,一股热流从舌尖直冲鼻孔,脸上的汗水和泪水立刻涌出,全身通泰。我吃得连连呼出热气,对老陈说:“还可以再辣些。”俱往矣,现在陈氏辣酱恐怕已经失传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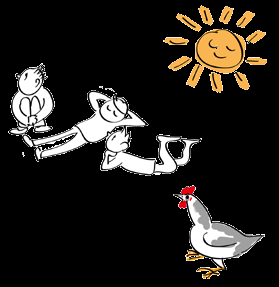
无论带多少吃的东西也应付不了几天,弹尽粮绝后大家经常在室外一起“吃鸡蛋”——就是晒太阳。这是栾荣康不知从哪本书里看到的,晒几个小时太阳相当于吃一个鸡蛋,老栾引经据典煞有介事地推荐给大家。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个画饼充饥的忽悠大法是困难时期河北省委鼓捣出来的。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鸡蛋?就是晒成母鸡也骗不了肚子,要解馋只能苦撑到发津贴后买个罐头调剂一下。
玻璃瓶罐头的铁皮盖子很不好开,韩建民非常厉害,用牙咬几下就能开启,现在民子也六张多了,不知当年的利齿尚在否。当年最爱吃的罐头是咖喱鸡,搅拌在米饭中,总会开出一场饕餮盛宴。闻味赶来的人们蹲在地上,把饭锅围得密不透风,头也不抬地吃着,只有金沛时常起身往锅里撒上一把盐。在那些北风呼啸的日子里,我们在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分享着快乐,充满了万物皆备于我的惬意,然后心满意足地拍着鼓起来的肚子各自散去。这么一个售价一块七净重340 克的小东西竟然蕴藏了如此令人晕眩的幸福,现在这种廉价的幸福再也买不到了。

阀门厂归地方后,铸工每个月能买一点保健肉,有了这点物质基础,雨后春笋般催生出一批自封的名厨大厨。当时出版的《大众菜谱》中介绍的第一道菜竟是令人鄙视的熬白菜,人们自然不会受这种菜谱的束缚,而是肆意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陈斌儒名副其实,不但继承了儒家老祖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更对烹调有一种无师自通的灵感。有一次老陈做红烧鸡忘了放酱油,结果无意中创造出一道名菜黄焖鸡。老陈有兴致时会做最拿手的蛋饺,就是用鸡蛋做的一张张皮来包饺子,然后下在锅里,再加入白菜、粉条和豆腐,把味道的鲜美推到极致。与口感成正比的是工艺的繁琐,老陈在烟熏火烤下操练的辛苦自不待言,我在一旁抵抗阵阵肉香,咽着口水焦急地等待时也备受煎熬。老陈还做过一次酥肉,不是很成功,味道非常好,可惜太不出数,放入一大锅肉,最后所剩无几。由于太不划算,以后不再尝试。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在烹制过程中实在无法抵御阵阵诱惑,只好不断地偷吃锅里的半成品。老陈后来上大学走了,没了张屠夫,肉还是要继续吃的,我索性把整块肉往锅里一放,小火煮一夜,第二天蘸着酱油吃,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亦是一种境界。
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是最快乐的,贯穿假期始终就是吃,吃回去,回去吃,再带回一堆吃的。记得有一年回京探亲,先是一群朋友为我送行,在昆区的饭馆里猛搓一顿,上了火车后又在餐车里冒充回民吃了一大盘炒鸡蛋,途经呼和浩特时与吕晓林在火车上会合,继续吃晓林带的东西。卓资山的烧鸡在京包线上享有盛名,尽管鸡变的越来越小,甚至被怀疑是乌鸦冒充的,但路过时仍然不肯放过,就这样一路吃到北京。

到北京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吃,在饭馆里点了一大堆,服务员给我送来了两套餐具,我轻轻地推开一套,他一下愣住了。吃饭的过程中,不断有后厨的大师傅伸出脑袋看我这个可怜的饿鬼,直到目送我起身离去,大概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饭桶。
当时我的母亲被赶到干校改造,北京已无落脚之地,我只能住在东单二条的人民日报招待所。在兵团时,上个饭馆往返要三四十里,而这里出门就是饭馆林立的王府井大街,真是如鱼得水。
据说老北京的饭馆有八大楼、八大庄、八大园、八大居之称,“文革”中早已七零八落,但王府井仍保留了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有东安市场(“文革”中改名为东风市场)内的五芳斋、峨眉酒家(后改为湘蜀餐厅)、东来顺、小小酒家和经营西餐的和平餐厅,还有东华门的馄饨侯和春元楼(当时它的招牌已经被改成俗不可耐的山东饭馆,但是在菜单上还悄悄地用括号标出“原春元楼”四个字),附近有八面槽的萃华楼和康乐,当然也少不了全聚德王府井分号。
饭馆虽然还在,菜品已经乱了套。三不粘是同和居的招牌菜之一,结果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这个东西,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北京,最后居然在海淀五道口的一个什么工农兵食堂里找到了,难吃的很。全聚德的九转肥肠也不做了,幸好春元楼还有,价钱不便宜,九毛钱一盘,色香味俱佳,回味至今。

一次在春元楼吃饭,哥哥提起了当年的著名厨师丁少伯,少顷,一位老服务员一边擦桌子,一边悄悄地问我们和丁老先生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敢假冒,回答了些久仰大名之类的客气话。那位老服务员感慨万分地说:“丁少伯是我的师爷,现在饭馆里上班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些了,您二位顾客倒还惦记着。”一代名厨的弟子被安排当服务员,想必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他提到师爷时毕恭毕敬,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饭馆吃饭也偶尔会和人斗气,有一次在丰泽园点了一个笋鸡,我们问服务员为什么菜里没有笋,服务员也是个年轻人,他冷笑两声,撇着嘴回答:“切,笋鸡就得有笋啊?笋鸡就是小鸡!”我们恍然大悟,自己的见识不够,菜里没有笋我们接受,但对方的话里有损,我们忍受不了那种轻蔑的态度。老栾反击说“小鸡?小鸡叫雏鸡!”我也跟着起哄:“或者叫子鸡,奇珍阁的东安子鸡,听说过吗?哪有叫什么笋鸡的?哪个饭馆这么叫?”这下轮到那位年轻的服务员晕菜了,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有一次在新侨,点菜时一连几个都没有,没想到换菜时稍一迟疑,服务员嫌我们点得慢,竟然翻着卫生球眼珠不耐烦地走了,实在搓火。后来我们把要点的菜和备选的菜写在纸上,继续点菜时,我们飞快地把菜名报了一遍,服务员当然记不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我们也不再理她。过了好几分钟,服务员问:“你们要吃什么呀?”马文然大声说:“我们要吃麻婆豆腐!”西餐馆里怎么会有这道菜,马文然接着解释说“就是麻婆给我们端来的豆腐!”原来是讥讽服务员的脸上长了雀斑。
和平门烤鸭店刚开业时,我们去过一次,吃完后才知道这里的鸭架汤竟然要另外花钱单点。哪里有这样的规矩,自然又大闹一场。
当时全国各地的服务态度没有不恶劣的,大家都遭遇过白眼,自然也会还以颜色。现在当然不会这么做,但年轻时涵养不够,不出这口气很难受。服务员当然也会觉得委屈,但总还有工钱拿,我们花了钱,为什么要受这种气。
处处皆学问。有一次在中国照相馆旁边的闽粤餐馆吃饭,哥哥点了一个扁食燕,我很奇怪,问这是道什么菜。哥哥说这个和饺子差不多,你没看过《水浒》吗?《水浒》我当然看过,但是光看热闹不求甚解,根本没注意这些细节。还有一次在老莫点了鱼子酱,菜上来后发现旁边摆了几片柠檬,不知道怎么吃。还是哥哥想起了《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记载的与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的细节,才明白了柠檬的用途。看来多读书,认真读书还是很有用的,至少可以少露怯。

说到吃饭露怯,总会提到老莫,尽管西餐并不合口味,人们总要附庸风雅,结果出尽洋相。当时有笑话说有人点了一大桌菜,端上来才发现全都是汤。有一次我和朋友在老莫吃饭,忽然进来一位背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农民,一看就是在附近的动物园逛累了想找地方吃饭,不知道被哪个缺德的家伙诳到这里来的。这位老乡也是见过世面的,他把行李往地上一堆,然后纵身一跃,像老鹰一样蹲在靠背椅上,边擦汗边吼道:“跑堂的,六两饺子!”声震屋宇。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随即笑得前仰后合。
和包头饭馆普遍使用的五寸盘相比,北京饭馆的菜分量充足,最小的也是七寸盘,味道更是要好上十万八千里。价格也便宜不少,一般的家常菜每份只要四五毛钱,啤酒四毛钱一升,一块多钱就可以吃到特色菜或鱼虾类的菜了。老字号饭馆的菜也不算贵,烤鸭按照大小计价,四至八元一只,东来顺的羊肉串四毛一串,都一处的烧麦一块六一斤,三鲜的也不过两块二。印象中最贵的是晋阳饭庄的水晶肘子,要卖到三块钱,我们没当这个冤大头。当然西餐的价格要高不少,老莫的一份红鱼子酱要九毛钱,黑鱼子要一块三,不过听说这东西在苏联只有专供特权阶层的小白桦商店里才有货,非土豆烧牛肉可比。





自兵团撤销,阀门厂归地方管理后,我们成为工人,加上保健费、夜班费等,收入不算少。内蒙古物质匮乏,花钱的机会不多,大家也比较节俭,每年探亲回来便挥霍一番,正所谓逛窑子吃豆腐渣,该省的省,该花的花。那时动不动就要去老莫搓一顿,我们不知道西餐是每个人自己点自己的菜,不知道应该先喝汤,更不知道甜品叉与主餐叉的区别,我们根本也不想知道,不屑于知道。我们是山里人,三月不知肉味,今天代表劳动人民来扫荡一番,喧哗中打着响指召唤boy,年轻的胃和胖胖的钱包使我们充满了自信。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