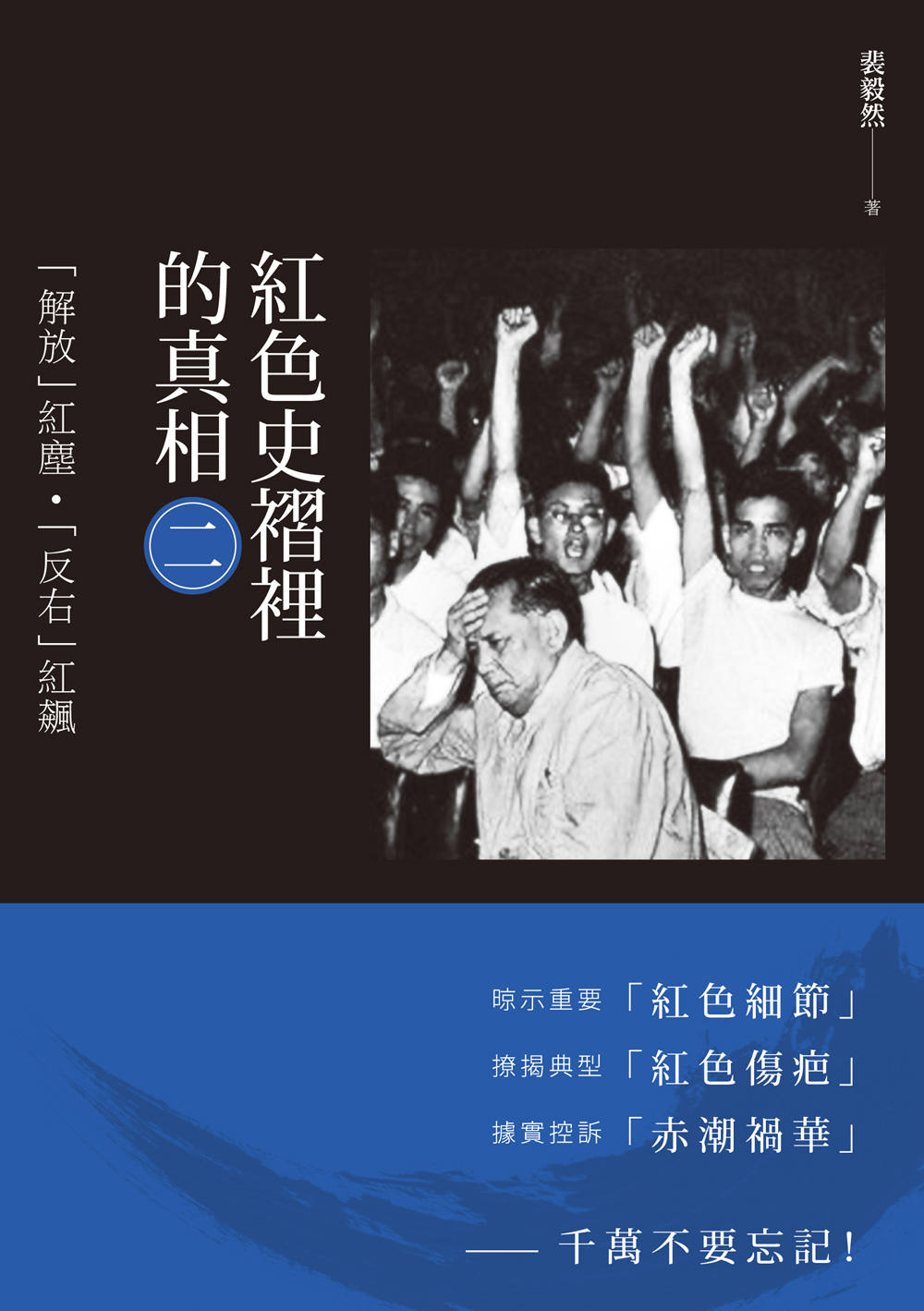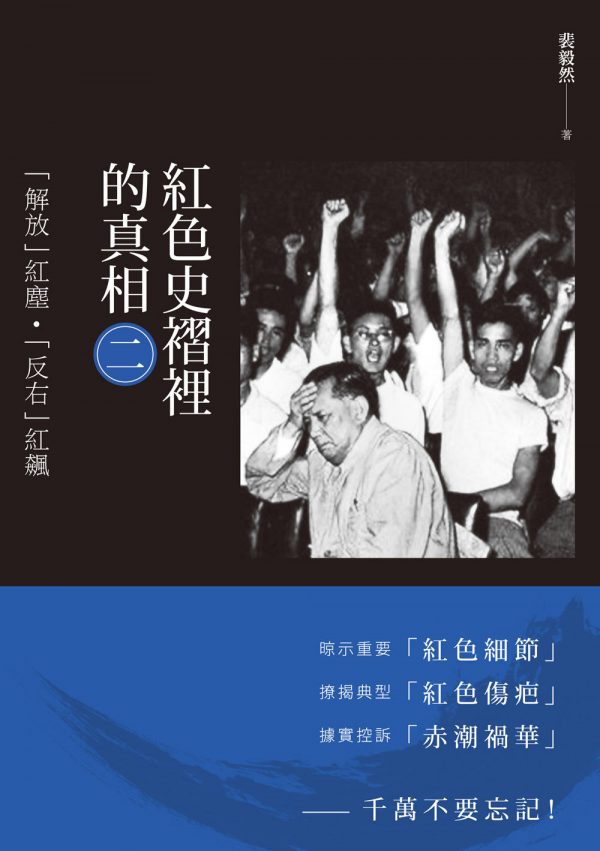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1、一位地下党员的悲剧人生
赵宏才(1923~2003),河南洛阳人,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该校中共秘密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骨干。1947年6月(南京学运高潮)入党,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1949年南京易手前,两次被捕,险些丢命,越狱逃脱。
1948年底,赵宏才受命赴江北赤区,专跑交通,负责将南京地下党员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区”。多次遇险,受刑,吊打、压杠、上拶、“灌洋酒”(鼻孔灌水)、假枪毙,手下两名交通员被处决。赵宏才一夜吊打,悬绳三断,冬泅冰河,冒死逃脱,回到“党的怀抱”。不过,他的忠诚不但没增加“革命资本”,反遭审查,长达一年(搁置党籍),结论“没有问题”,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后任上海市长)批准恢复党籍。这段被捕经历,成为他一生苦难的开始。
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难始于出生入死迎来的“解放后”。1957年划“右”,文革再陷囹圄,两次越狱,二十一年非人生活,八年乞讨打工,挣扎于死亡线,直至老毛伸腿才得回家。此时,鬓毛摧枯,浑身是病。。
五七“划右”
1957年,赵宏才供职北京中苏友协,“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机关二把手林朗命他写板报文章,将毛泽东鼓动“鸣放”的话用他自己的话再说一遍,动员全机关“鸣放”——助党整风。于是,赵宏才写了三篇〈闲话〉——
提倡说心里话
党群之间有墙有沟,要拆墙填沟
过去励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为了改革连杀头都不怕,我们为帮助党整风,提点意见还怕报复吗?
6月8日风向一逆,他顿时成为单位“右派”头目——鼓动“右派”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尽管三篇〈闲话〉全来自毛泽东三次讲话,没一句是他自己的,且为奉命作文。此时,二把手林朗如此转弯子——
毛主席是站在左派立场上讲的,而右派分子对毛的讲话是站在右派立场“各取所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里的“各取所需”,亦非来自林朗,原始出处也是毛泽东。
既已划“右”,出路只有一条——真诚认罪,否则“觉悟太低”,怎么能与党不保持一致呢?党都划你“右派”了,还不认帐么?难道党会错么?赵宏才自居“真正党员”,自况为党背负十字架,为维护“党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像上刑场一样承担反党罪责。他的划“右”结论,层层拔高后才获上峰批准,若按初始结论,本不“达标”。
中苏友协一把手乃1926年入党的印尼归侨廖经天(1913~1998),北伐后流亡海外,坚持“闹红”,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林朗多年老战友。“反右”开始后,上峰指示林朗揪出廖经天,林朗下不了手,“弃车保帅”推出办公室主任赵宏才。廖经天不明就里,党组会上为赵宏才辩护,说赵是十分忠诚的党员。最后,不仅赵、廖划“右”,林朗也被划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林朗那套批判“右派”的分析哲学,对他自己也适用了。
反右运动正酣,林朗被查出癌症(晚期),忍着肉体精神双重痛苦,接受批判、检举他人,以示对党忠诚。不久,林朗去世。
一、二把手先后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赵宏才的思想工作——
比你问题严重的人多的是,可是你已经划作右派了,就不好再改。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
赵宏才晚年说,这位三把手诱导“心服”的话,他记了一辈子,每个字都像火红冒烟的烙铁哧啦啦烫着他的心尖。为了“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认也得服。廖经天不服,1962年后多次从流放地贵州铜梁返京闹翻案,一再碰钉子。
漫漫炼狱
赵妻年纪比丈夫小,党龄却比他长。为免株连,赵宏才提出离婚,赵妻不耐烦了:
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
性格倔强的赵妻,此前三天两头与丈夫吵架,这会儿特温柔,不再吵了。因不肯揭发丈夫反动言行,她被单位斥为与“老虎”(坏分子贬称)睡觉。他们被赶出机关宿舍,塞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阴冷潮湿的地上。严冬季节,赵宏才发配渤海滩唐山柏各庄劳改农场。下放该场的中宣部系统“右派”:廖经天、萧乾、陈企霞、锺惦棐、蓝翎,以及曾在白洋淀战斗过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新四军记者季音,还有一位部长(抗战前泰共华侨)。这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心甘情愿被骂“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
他们有一共同疑惑——
同样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同样用胁迫劝诱的手段,同样要你低头认罪,为什么国民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败了,共产党却办到了?
南京某大学一位郭“右派”,批斗大会上低头认罪,私下与组织谈话则坚不认罪。许多“右派”陆续摘帽分配工作,他仍戴着“右”帽拉板车。一位党员同情他,要他低个头认罪算了,少吃苦头。郭“右派”凛然回答:“气节”!而之所以曾当众认罪,那是“维护党的影响”!
一位农村工匠与赵宏才告别时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实在太尕古。”(方言:古怪)赵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之所以说违心话,乃是不希望工匠对党有看法。直到晚年,这位出身中央大学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当年的愚昧。
柏各庄劳改农场,赵宏才与锺惦棐邻床,关系极熟,两人躺着聊起锺那篇贾祸名文——〈电影的锣鼓〉(台湾全文转载)[1],锺惦棐嘿嘿一笑:“那是周扬和我交换意见以后,他叫我执笔写成文章发表的。”啊,原来如此!次日,农场领导问赵:“锺惦棐跟你讲了周扬部长什么了?”赵宏才极其惊讶小报告打得如此灵快,只好如实相告。领导听后说:
这就对了。昨天锺惦棐急着找我,赶在你前面说了此事,怕你歪曲他的话,添油加醋,咬他一口。
那么亲密的老锺,如此设防,人际之间呵!也是这位赵宏才,看到别人揭批萧乾“挣了表现”,为摘“右”帽得分,——
我也蠢蠢欲动,只是因为找不出老萧的错误作为攻击他的材料,只好听别人揭发。
1959年河北省委下文,赵宏才摘帽,回原单位听候分配,他的反应——
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
他被分配淮南徽州农校副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俞时模,“右派”摘帽,发配歙县安徽师校副校长,这位大革命時期的党员,文革时被活活整死于黑牢。
文革乞讨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斗争激烈,赵宏才四处逃躲,有家归不得。徽州农校成立革委会,他以为局面安定下来,回到学校。不料,两派头头因“大联合”分享权位,合力搞阶级斗争,专斗“黑五类”。他被关入楼梯下小黑房,一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审讯,踢打逼供。俞时模就是此时关在农场黑牢,惨遭刑讯批斗。俞曾越狱,失败后死于非命,死前,俞耳朵已被耗子咬烂。赵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次越狱,逃出囚禁,不敢回家,流浪皖北巢湖一带乞讨,夜宿废弃瓦窑,偶而扛活自养。
一位地主成分的农村小学教师,受不了批斗自杀。造反派念着毛语录将尸体抬上台,两个戴口罩的“革命群众”将死尸竖立台前,一批人挥着小红书“尸斗”,台下一片寂声,赵宏才连忙转身离去。
八年乞讨、扛活,他得了伤寒,差点死在“旅途”。后见报纸上说“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他回到徽州农校。这次不再打骂关押,但经地委批准,大会宣布他是叛徒,监督劳改。他每月向地区革委会递交申诉,要求平反。不久,来了两位项目人员,宣布定他叛徒没错,但可不以叛徒处理,解除劳改。赵宏才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于是继续当叛徒、继续劳改。
劫后余声
多年劳改、流浪、乞讨,这位革命者头发花白,百病缠身,正不知所以,“忽传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新任地委书记正是1949年审查赵宏才越狱的那位老兄。递上一纸申诉,冤案迎刃而解,解除劳改,恢复自由。中宣部也来函,要他申请“右派”复审,“右派”问题也改正了——“俱往矣”。
复得自由,赴宁见妻,相拥涕泣,回忆录戛然而止。2003年12月7日,这位红色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最后六年拼力完成的回忆录《劫后余声》(20万字)。临终前,说心里长出一块“癌肿”,非要说出来——
马恩一些哲学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毛遵循马恩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也摧残了无数无辜。
密友穆广仁(1925~ ,新华社副总编)评价:
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2]
赵宏才的回忆录超越了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找赤灾成因,追溯赤祸源头至马恩理论,相当不易。
重大局限
红色信徒的个人命运,当然只能与国际共运“同呼吸共命运”,谁陷入赤色漩涡谁倒霉,既受骗帮着数钱,还得“心甘情愿”为党吃冤枉。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最后还在坚持赤说,仍以“马列信徒”自荣,为回不到“党的怀抱”伤心痛苦,还认为马列“经是好经,只是和尚(斯大林、毛泽东)念歪了”。他们意识不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这一似乎绝对神圣的红色目标,才将俄中东欧等赤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一步步走入相反的独裁专权。很简单,若无这面指向天堂的赤旗,国际共运如何发动?赤潮如何涌起?中共又怎会集体认同老毛公然违反一系列人文原则?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怎么一步步“符合逻辑”地走来?
止步控诉、无力追源,只批手段,不触目标,乃是绝大多数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两头真”的宿命,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他们一方面担心被指“马列叛徒”,一方面也确实无力辨析赤说之谬。究其根本,价值体系单一、思想偏窄狭隘,延安一代、解放一代拿什么去质疑“光芒万丈”的马列主义?不握持真正的现代人文理念,又如何对抗“最先进”的共产赤说?
思想必须以思想去对抗,逻辑亦须逻辑去驳斥。这批“两头真”最终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列的这一部分驳诘马列的那一部分。他们一生的悲剧凸显一条粗长的赤潮根须——文化的贫困。
初稿:2010-12-23~25;补充:2013-7-17;
[1]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121。
[2] 燕凌、穆廣仁等编著:《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中国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上册,页128~138。
原载:《开放》(香港)2013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