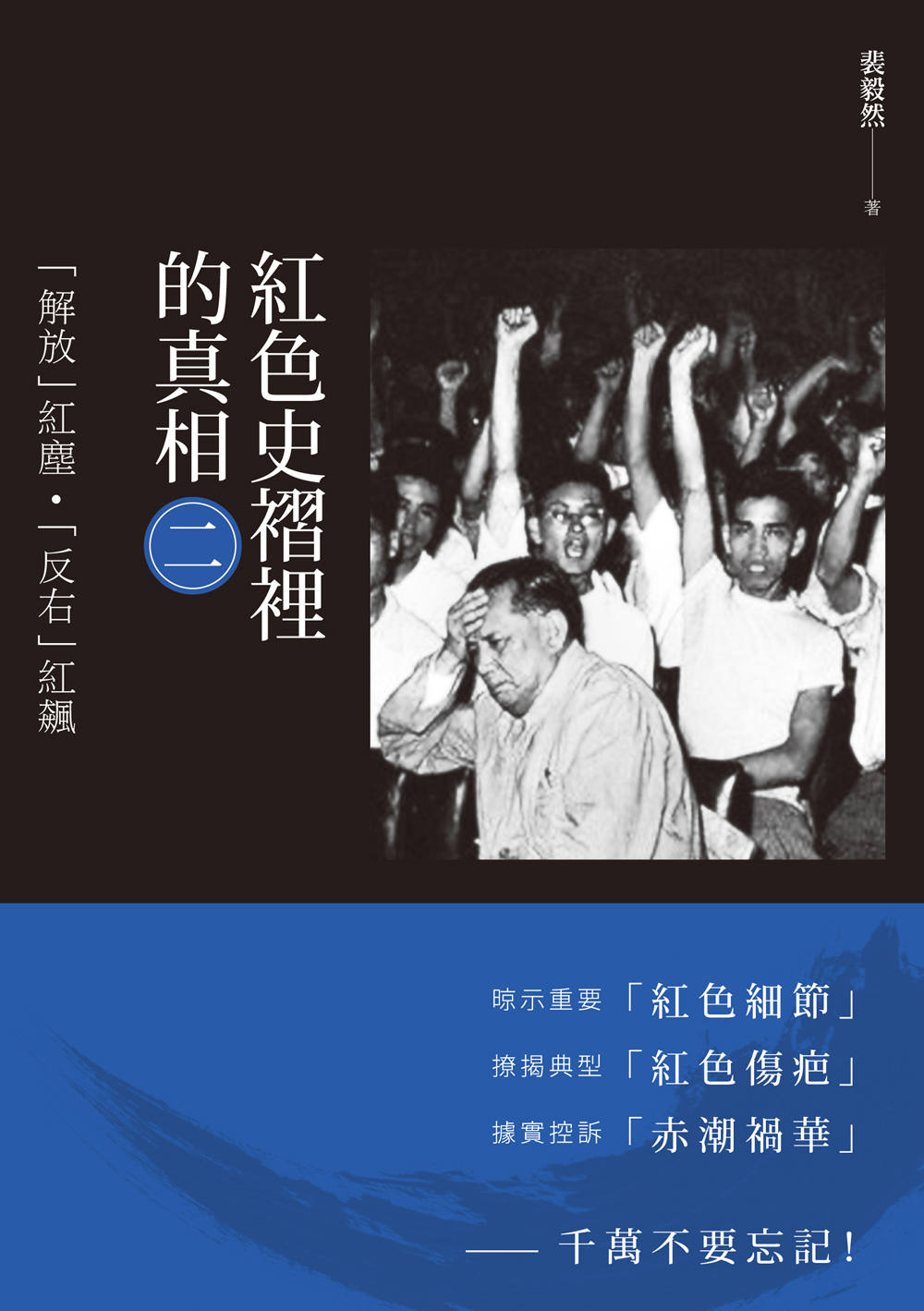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2)
“刘少奇的苦”
1959~61年大饥荒,笔者5~7岁,虽在江南杭州,吃苦不大,仍有一些烙印很深的记忆。长大后,听到不少有关这场大饥荒的忆述,惊心不已。
童年饥荒记忆中,最清晰最典型的是“一斤鸡蛋”与“一箱土豆”。1960年“六一”儿童节,我尚在杭州邮电幼儿园,每童发一斤鸡蛋,母亲小心翼翼提回家。正值上海外婆来杭,直说这斤鸡蛋极珍贵,至今还记得外婆盯看鸡蛋的惊喜眼神。其时年幼,不知外婆“珍贵”之意,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她饿,“市面上啥格都呒没卖”。
“一箱土豆”则是1961年东北小舅舅托运来的,约25公斤。小舅舅19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因出身不佳(外公1949年前曾任扬州教育局长),从财政部下放至安达(现大庆)。得知鱼米之乡的江南居然也挨饿,他那边正好土豆敞开供应,便铁路托运来一箱土豆。母亲得讯便记挂起来,火车托运很慢,将近一个月才盼来这箱土豆。第一次煮吃,全家激动不已,个个脸上放光。东北土豆很粉很香,实在好吃!很长一段时间,这箱土豆成为全家记挂之物。母亲每次取食,数着点着,尽量延长“服务期”。不过,一箱土豆还是很快吃完,盛装的木箱成为垫撑碗橱的“家具”。母亲一直说:“那段日子,全靠这箱土豆!全靠这箱土豆!”
由于营养不良,全家四口三人患肝病,父亲、姐姐肝炎,笔者“肝肿大三指半”,注射整整一学期“葡萄糖”,每天下课带针剂去省中医院推注半小时。那段灾难岁月,作为“祖国花朵”,我十分幸运了,仅仅“肝肿大三指半”,还有葡萄糖可注射。较之中西部重灾区,杭州毕竟地处杭嘉湖平原产粮区,中共又力保城市,尤其省会大城市(关乎政治形象),杭州市民终于在半饥饿中维持下来。
1960年冬,西安食品普遍短缺,人们见面礼改为“习惯动作”——用手指去摁对方前额或小腿内侧,相互鉴定浮肿程度。[1] 由于饥饿,上海拖鼻涕小孩发现: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上海中学)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2]
1980年代初,笔者供职浙江省政协,一位川籍同事乃副主席何克希女婿,一说起“三年自然灾害”,三十六、七岁的他十分动容:
我们村里很多人饿死,不少人家甚至都绝户了。隔壁家一位老婆婆向我家求食,真可怜,我是真想帮她,给她一点吃的,但实在是无力呵!自己也饿得不行啊!有什么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位婆婆饿死!唉!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社会主义怎么还会饿死人?!
1970年底,笔者上山下乡东北大兴安岭,多次听到同一版本的“忆苦思甜”——
村里举行当时全国流行的“忆苦思甜”,指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诉苦。临上台前,村干部怕他搞混年代,一再叮嘱:“千万记住了,今天是诉蒋介石的苦,旧社会的苦,不是1960年刘少奇的苦,勿要搞错了!”不料老贫农上了台,还是实话实说:
我这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最苦的还是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那是叫真苦!真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以前替地主扛活打工,至少还能吃饱饭嘛。不吃饱肚子,怎么给他家干活?……
村干部急忙上台,将越说越离谱的老贫农哄着拉着弄下台,连连埋怨:“怎么搞的?跟你说不要诉刘少奇的苦,怎么还要诉呢!”纯朴真诚的老贫农一脸不解:“不是让诉苦么?刘少奇的苦就是最苦的苦嘛!不诉他的苦,诉谁的苦?”刘少奇是那时的国家主席,老百姓眼里最高的Number One。
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1936~ )回忆录——
“四清”工作组在乡下搞忆苦思甜活动,老农们却大忆其三年困难时期之苦,令人有些尴尬。[3]
学者周国平(1945~ )也有一段类似记载——
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4]
那几年,富庶的江苏常州地面也挨饿。乡亲们为找活路,来杭州投奔当小官的笔者岳父。其时,岳父三十出头,浙东“三五支队”出身,接收《东南日报》(即后来《浙江日报》)军代表,18级副处,月薪八十余元(已属高薪),但他能做的,只有“大出血”让乡亲们下一顿馆子(七十余元只能吃全素席),再给乡亲们一点盘缠,让他们回乡。拙妻回忆,那时每人一月一斤糕饼票,珍贵极了,大人都舍不得吃,全省给子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丈母娘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念叨的便是“糕饼票”。
拙妻1957年出生,父母《浙江日报》党员,一水儿红色教育,也是从现实“受教育”,慢慢“睁开眼”。1966年5月文革爆发,父母投身运动,无暇照顾孩子,送她们姐弟回江苏武进农村。过年时,一碗莳茹炖鸡,端进端去半个月(不时加热防腐),只能看不能吃,元宵节后才准下筷。祖父乃上中农,领着姐弟俩到几块上好稻田:“土改前,这块地是我们家的,那块也是。你奶奶上海当奶妈挣回钱买下的。”奶奶也对不到十岁的孙辈说:“解放前乡下哪像现在啥啥都没得吃,蚕豆一缸缸,哪里吃得完?鸡鸭满林跑,来客人随便抓一只杀来吃,哪像现在过年只能看半个月!”1980年代,她虽听了我的反共言论有点吓丝丝,却认同我的关键论据——今不如昔。
拙妻一位亲戚,大饥荒时在沈阳读大学,二十刚出头的女生,胃口按说不会怎么大,但她有关大饥荒的记忆:就想吃馒头!每次上食堂,眼睛直直盯住小窗里那一只只白面馒头,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没限制地吃那一蒸屉馒头,她觉得能吃下整屉馒头!
还有一则经典情节:一位饥饿青年一口气狂吃满满一罐猪油(约一公斤)。当晚,这位老兄狂泄不止,肠子都快拉下来了,第二天仍希望再吃一罐猪油!陕西“反动分子”康正果回忆:一位饿极了的劳教犯贪吃一年一度敞开供应的土豆,肠胃堵塞,活活撑死。[5] 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班竟一半学生同时戴黑纱。
最悲惨的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政治劳改犯。“胡风分子”何满子在宁夏劳改,每顿只有一二两粮食,却得干背土砖这样的重活。[6]上海外语学院右派学生王升陞回忆安徽劳改农场:“我们劳改队400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二十多人。”[7]
安徽亳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晚年撰文——
由于粮食高估产,引发了连年粮食高征购,致使购粮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加之1959年夏秋旱灾,致使粮食征购连年完不成征购任务,采取了年年季季户户搜粮,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普遍发生,从而出现了全县性的荒、逃、饿、病、死,更严重的出现了人吃人。……因饿而引发的多种疾病达50万人次以上。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耕畜减少50%以上,鸡鸭大减,许多村庄猫狗绝迹。农民房屋扒拆倒塌近10万余间。80%以上的林木被砍伐,全县农村面貌全非,一片凄凉。……全县28000多户农民家庭毁灭,30%左右农民死亡。[8]
陕西通渭县,“1959年和1960年,饿死了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9] 罗瑞卿岳父母不得不从河南临漳老家赶至北京女儿家投食。[10]
白桦:
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我: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里的砻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是谣言。1958年全国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的报导历历在目,亩产万斤、数万斤、十余万斤……那些粮食都到了哪了呢?后来,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是我的老乡,党员。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来以后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的铺位在我的铺位的上面,平时从来不敢和我说话(按:白是“右派”)。有一天晚上,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着他返乡的故事——
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
我没有搭话,我装聋作哑。他当然也希望我是聋子。在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我心里明白,他实在是痛苦之极,又无人诉说。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反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11]
1959年末,贾植芳之妻任敏关在青海化隆县监狱,一女犯带着孩子蹲监。问起案由,女犯不说话,孩子回答:妈妈将一岁多的弟弟杀死煮熟,同他一起吃了,被邻居看见,押送入监。孩子对妈妈说:“这里有馍馍吃,我们不要回去了,就住在这儿吧?”[12]上海百货商店因货架久空,竟用《毛泽东选集》填充,火柴煤球、针头线脑都要配给供应。[13]
其时,出国访问普遍在国外购买食物,包括级别很高的大干部。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内,以致黄油融化脏了衣服。1961~62年,外交部不得不规定:出访人员不得在外购买食物,以免“不良国际影响”。[14]
事情当然很清楚:强制推行公社化,刚刚得到土地没几年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一大二公”的政策使所有劳动成果均须通过集体分配,硬性抹平强弱勤懒之别,劳动绩效无法体现于收成,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磨洋工”,消极对抗公社化。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公有制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现实生产力,社会意识悖离社会存在。同时,“集体食堂”打乱了农民对粮食的自主安排,秋后短期的放开肚皮撑吃,造成后面无粮可吃的“春荒”。所谓“天灾”,中共推责词耳,当然是“人祸”。
此外,中共为制造原子弹,在国力极其有限的基础上,耗资411亿美元购买苏联核技术,原定16年归还的“抗美援朝”债务硬逞强五年还掉,“苏联老大哥”给的粮食援助也不要。大饥荒初期,周恩来居然还向专家请教如何储存粮食,因为各省虚报产量,中央在为粮食太多发愁呢![15]
大饥荒发生时,由于报喜不报忧的“体制病”,大陆媒体还是形势一片大好,还在“赶英超美”。本该实话实说的《内部参考》,仍没一篇真实报导,只有一二篇闪烁其词的相关简讯,饥荒的专用代称“浮肿病”。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源于中共为证“伟光正”的瞎折腾,出于对“主义”负责而非对人民负责的国际共运。中共至今仍未承认这场罪恶“人祸”,还在托词“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所谓缴纳“社会主义学费”,那可是4000余万条生命呵!河南信阳、安徽凤阳、甘肃夹边沟…… 那些可怜的饿毙者,愿意成为“学费”么?
历史不会仅仅只是随风飘去的日子,一切必将得到“最后审判”。最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同意失去这一段记忆么?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偌大吾华会缺一二“直笔”史家么?
初稿:2005-8-14~15;增补:2006-5-23;
原载:《开放》(香港)2005年9月号(初稿)
[1]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二版,页33。
[2]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三联书店(香港)2004年,页10、60。
[3] 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5年,页159。
[4]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三联书店(香港)2004年,页60。
[5]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二版,页214。
[6]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页161。
[7] 丁抒:《阳谋》,九十年代出版社(香港)1991年,页362。转引自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页177。
[8] 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3期,页18。
[9] 杨继绳:〈通渭——曾是“苦甲天下”的地方〉,《炎黄春秋》(北京)2005年第12期,页67。
[10]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页91。
[11] 白桦:〈暴风中的芦苇〉,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年,上册,页176~177。
[12] 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00年,页443。
[13] 白桦:〈暴风中的芦苇〉,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版,上册,页179。
[14] 资中筠:〈在胡志明家做客〉,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4年,页199。
[15] 杜维明:〈反思文革先要超脱集体健忘〉,《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6月号,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