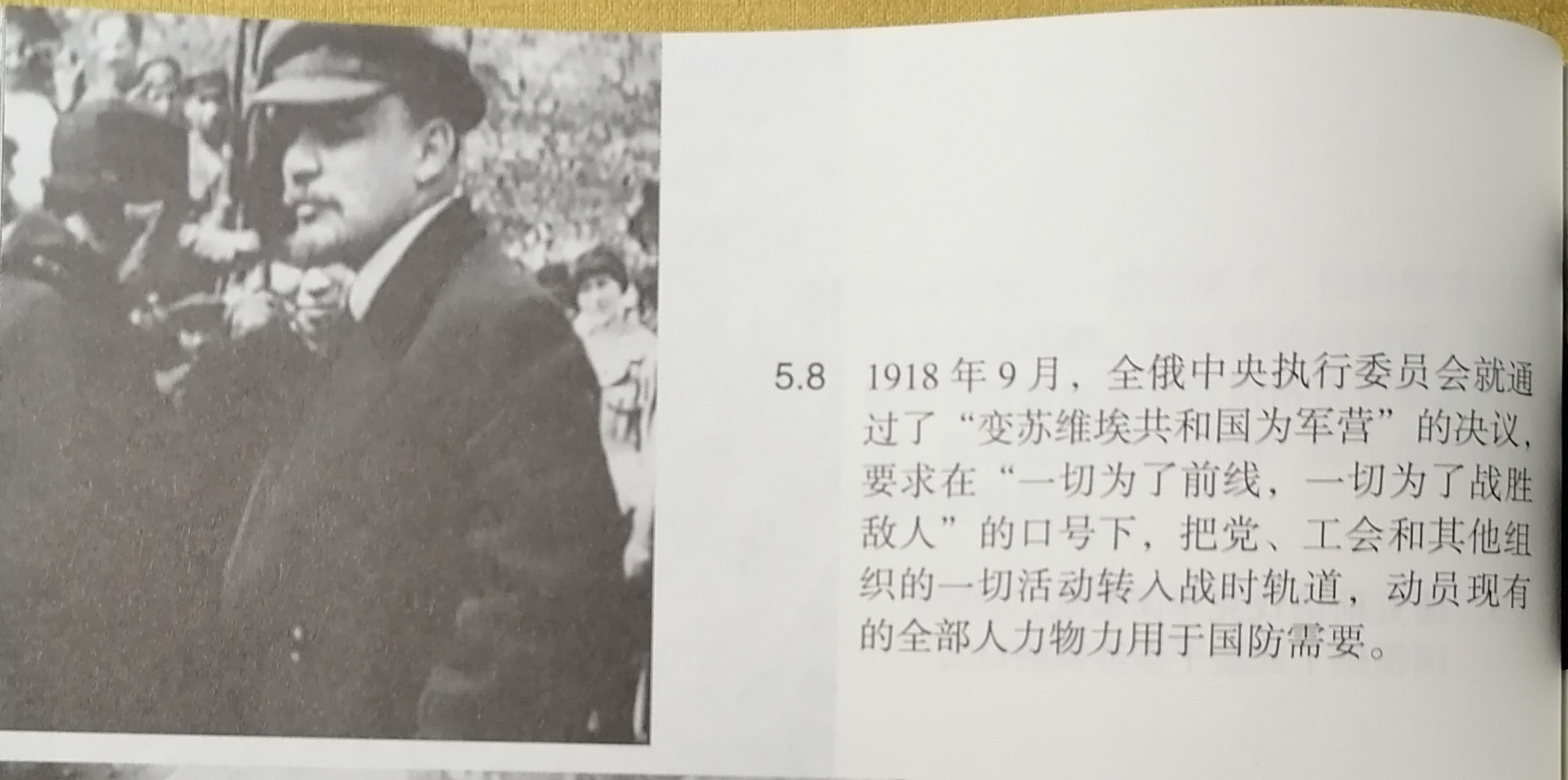列宁: 一个胸膛,两个心灵(1)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列宁的一生》被誉为“是世界上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部列宁传记。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评价此书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在这部著作中,有一章题目为《一个胸膛,两个心灵》,作者用不长的篇幅叙述了列宁理论与实践的一些矛盾之处。他说:
在列宁的胸膛里有两个心灵: 一个是理论家兼宣传家的心灵,另一个是国务活动家的心灵。这两个心灵从来都没有互相接触过,因为如果它们相遇的话,那它们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列宁的许多抽象概念存在于非现实的世界里,同他的实际活动是完全分离的。
列宁经常不断地预言世界革命很快就将到来,这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抽象概念,就像他在1917年时一再坚持认为国家很快就将自行消亡那样一种抽象概念呢?他在1919年7月20日回答(美国)合众(国际)社提出的问题时,又重复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叠句。他断言: “资本主义达到成熟,而且成熟过度了。资本主义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代替资本主义的是苏维埃共和国。……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路易斯·费希尔在书中指出,虽然列宁反对空想和幻想,主张尊重客观情况,但是“列宁在1911年时所作的预言(他当时曾预言,“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以及他在1912年时所表示的信念(他当时曾深信,美国处在社会革命的前夜),难道是客观的吗?费希尔在书中还阐述了列宁对西欧一些革命事件作了过高的估计。
费希尔认为列宁提出的“欧洲联邦”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列宁自自己后来也承认的。他指出: “列宁在1914年发表文章,主张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欧洲联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 “列宁在1915年8月23日取消了关于欧洲联邦的口号,宣布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 列宁自己说: “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费希尔对列宁理论与实际脱节浓墨重彩之处是列宁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他不同意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后国家将立即开始消亡的提法。他指出:“没有什么比距离国家消亡更加遥遥无期的了”,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居然把国家的消亡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即就提上了日程”。
费希尔在这里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他写道:
根据列宁时常为自己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作辩护这一点来判断,和根据列宁曾经多少次企图对自己的《国家与革命》一书重新“进行解释”这一点来判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定使列宁感到十分难堪。1919年7月11日,当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一次“论国家”的演讲。在演讲一开始的两分钟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说,国家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楚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一分钟后,他又回到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来。他说: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
国家问题已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列宁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体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在汉语辞典里有两种简要的解释::一种是政治定义,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自行消亡。另一种是自然定义,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阐述显然是围绕着政治定义进行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偏见而且往往罔顾事实甚至前后矛盾。例如,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不屑一顾,而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让人怎么看都是独裁者的自白。
首先看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列宁先后给无产阶级专政下过多次定义,而且越来越极端。在1917年8月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这里他还没有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巴黎公社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虽然在做进一步解释时,他强调了“实行镇压”和“使用武力”,但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实行专政的亲身体验,也没有遇到政敌的直接对抗。但到了1918年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他的口气就强硬起来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这样说: “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者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 这里他强调的是“无情镇压”,他实际上也是这么干的。不久,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他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更进一步的定义,他说: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这里,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凭借暴力手段”,二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些列宁主义的卫道士曾企图对后一点加以掩饰,说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是指“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约束”。这些人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列宁明明说的是“任何法律”,而“任何”是指“一切”而不是“一部分”。因此,“任何法律”不仅包括资产阶级法律,也包括无产阶级或布尔什维克自己制定的法律。其实,列宁1920年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重复这个定义时曾更明确地说: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约束、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凭借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特别是也不受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限制,是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所下定义的真谛所在,这是布尔什维克执政的金科玉律,列宁本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后来斯大林、毛、邓、波尔布特、金家三代对这一点也都是心领神会的。
列宁在以独裁者的口吻大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后,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攻击西方民主制度。费希尔接着写道:
这里列宁提到了恩格斯,用他的话来说,恩格斯这样来教导人们: “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列宁接下去说道: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会有不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另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许诺说,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国家将立即开始消亡。现在他把这个最终的结局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推迟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的那个时候。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自有他的理论认知。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论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由时说: “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 不久他又论述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具体理由: 第一,“不无情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第二,为了对付“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他们数量“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必须有铁的手腕”。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小资产阶级。当然,列宁特别强调的是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理由。例如他说: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愈厉害,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愈疯狂。” “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 看到这些宣扬暴力、宣扬镇压、宣扬仇恨的言论,人们可以想像到当时的苏俄社会现实该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1917年12月,列宁起草的《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规定: “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官吏以及投倒把分子都应给予上述同样处分(即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 “把违反或迴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这里的“怠工”、“投机倒把”、“迴避” 含义模糊,完全由当政者说了算,成为大规模迫害的口实。
列宁曾在1918年写过一篇题为《怎样组织竞赛》的短文,文中强调了运用恐怖手段对付敌人的绝对必要性,提出总目标是“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列宁在文中宣布“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流氓、懒汉决战”。具体办法是: “在一个地方捉十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去坐牢。在另一个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把他们当作危害社会分子加以监视。在第四个地方,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在第五个地方,……对于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可以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简直是无法无天,对“害虫”的惩罚随心所欲: 同一种“罪行”既可以被罚扫厕所,又可以被就地枪决。而这种既残暴又荒唐的政策一直被其追随者和信徒视之为革命斗争原则的典范。
路易斯·费希尔对列宁思想的矛盾双重性继续进行揭示:
列宁不相信在现实世界中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他提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关于“谁战胜谁?”这个斗争问题,并作出了回答: 共产主义必将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列宁没有指定日期。
当时,在列宁对问题的答复时,他向合众社表现出一副幽默的样子: 苏维埃俄国愿意同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展开竞赛。列宁就资本主义社会中压制自由这一点写道: “再举一个小例子。美国的资产阶级吹嘘他们国内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以此欺骗人民。但是,不论是这个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或政府,都不能也不敢根据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同我们的政府进行竞赛,比如说,订立一种条约,保证我国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自由交换……以政府名义用任何一种文字出版的刊有本国法律条文和宪法条文并说明该宪法比起其他宪法有哪些优点的小册子。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不敢同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和平、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条约。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一切政府都是靠压迫和欺骗群众来维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铁幕时期、柏林墙时期之前讲的,而在这样的时期,苏维埃使用了干扰台来干扰外国的无线电广播;在这样的时期,苏维埃还使用了共产党人用以妨碍自由交换意见的其他一切手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宣布,自由和国家是不能并存的。他在放弃了国家自行消亡这一思想之后,又埋葬了国家和自由不能并存这一思想。因为他声明,苏维埃国家是民主的。1919年10月5日,列宁在对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艾萨克.唐·莱文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走得还要更远,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亲笔用英文写下了这样的回答: “是的,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我们准备来证明这一点。”
他会怎样来证明这一点呢?
还是用列宁自己作出的决定证明“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吧:
1918年2月21日,列宁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中规定: “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劳动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决。” “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这里人们又看到布尔什维克任意编织罪名,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枪杀犯罪嫌疑人的不讲法治的残暴行为。这种“法令”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所的政治报告中,针对孟什维克的批评意见,宣布: “凡是公开宣扬孟什维克主义的人,我们的革命法庭一律要处以死刑”。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而且是死罪,仅凭这一点,列宁还好意思和西方民主国家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上“进行竞赛”,真是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1922年,列宁在审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法典法律条文草案》时,批示要“扩大使用枪决的范围”,把“凡是进行宣传或鼓励,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 “一律处以死刑……” 改为“凡是进行宣传或鼓励,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或可能为其效力者” “一律处以死刑”。 这种以莫须有的“可能”的罪名处人以死刑的法律真是“世界上所有政府中最民主的政府”才能制订出来。
1919年12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我们直接了当地说: 专政这个词是残酷的、厉害的,甚至是带有血腥气的,但是,我们也说,工人专政将保证农民推翻剥削者的压迫。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第二天他补充说: “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都是绝对必要的。”
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第一天,根据加米涅夫的倡仪通过了废除对士兵实行死刑的法令。托洛茨基虽然对此有所犹豫,但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隐藏着。当他来到斯莫尔尼宫(起义总指挥部),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愤怒地高声说: “荒唐!取消枪毙怎么能够进行革命呢?”因此苏维埃政府决定不把这项法令声张出去。
有西方学者对列宁执政六年多苏俄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考证后得出一千四百万的数字。看来,列宁同志最大的“功绩”不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是执政年均二百多万人死于非命的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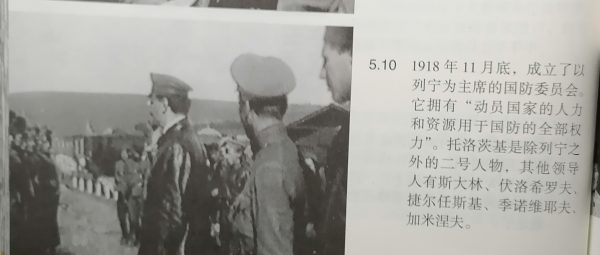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29)
在1960年代诺沃提尼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时起,布拉格就流传这样一句俗话: “国家假装要付工资给我们,我们也假装工作。” 捷克人这样解释那些对这种现象感到不解的外国人: “在我国,劳动的人和不劳动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差别。”
荀路 2021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