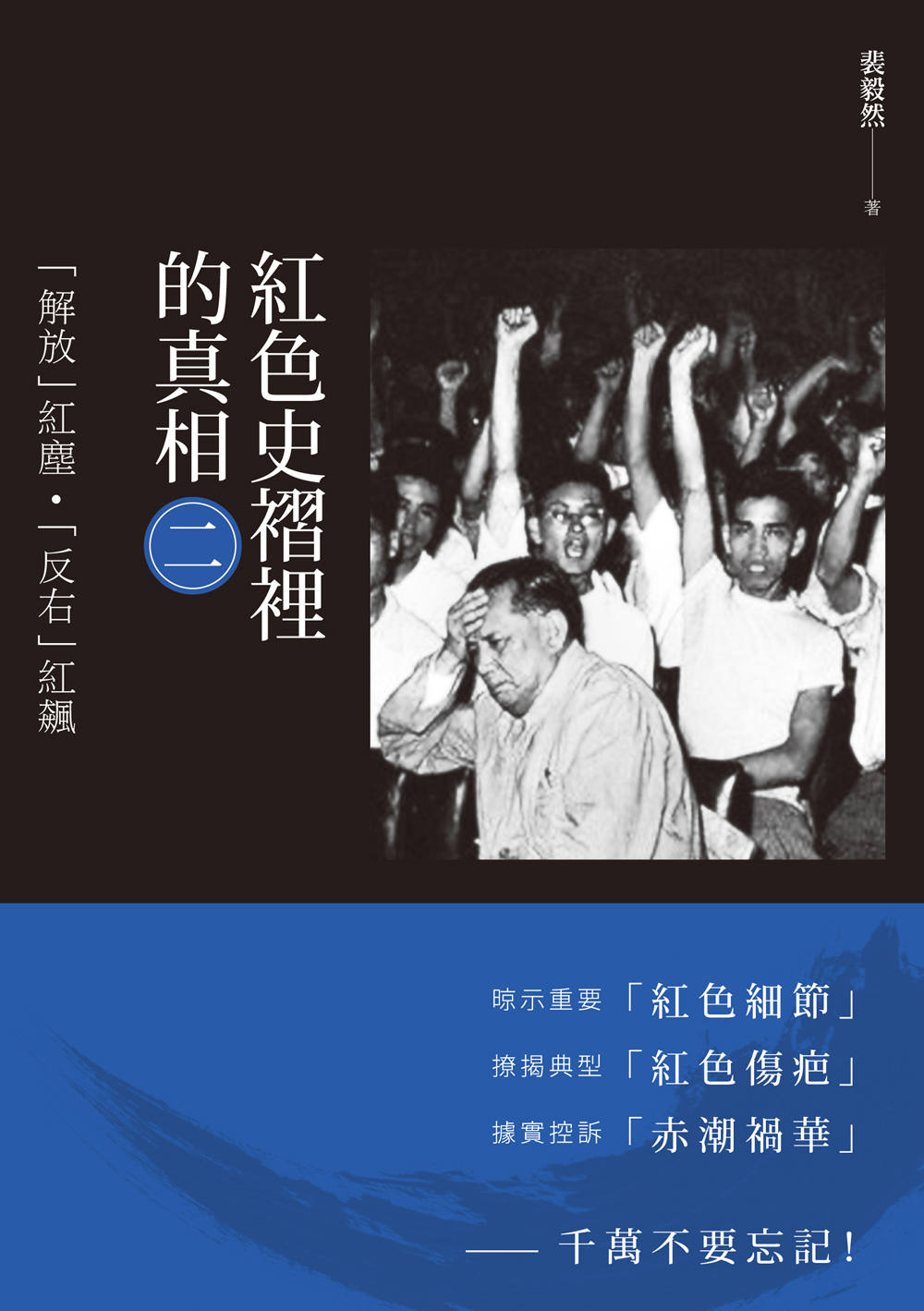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1)
又一份民间〈秘密报告〉
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余年间至少读了四五十本“右派”自传。底层“右派”的惨烈度远甚中上层,苦难更深,“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真正落到实处。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据说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前索阅)、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最感人也最有细节。2011年9月,得阅四川“右派”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美国溪流出版社2007年初版、台湾秀威公司2013年再版),深深撼我,很有必要撮精转述。笔者读后感浓缩为两句话:一、不能让这一滴“右”泪湮没史尘;二、又一本“反右”决算时的民间《秘密报告》。
赤色少共
这么一位墨墨黑的“反动阶级黑崽子”,偏偏一心想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能改造好子女”,心心念念“把一切献给党”。半年后,张先知入团,担任好几年团副支书,参加土改。1951年“镇反”,其父被毙重庆菜园坝,刑前游街卡车从他身边开过,车上五花大绑的父亲看到车下的儿子。街边贴着枪毙大布告,第一名即张父,但张先知此时为西南军区土改工作队员——
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通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按:其父)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1]
这边“我本将心托明月”,那边却是“哪知明月照沟渠”。不久,凡是血亲被镇压的“反属”均遭清洗。1953年,张先痴立三等功,1954年仍得转业,入南充县民政科。女友胡光君不到15岁参加共军,分配西南军区保育院,其父1951年亦被镇压。两位虔诚的共青团员“反属”找“反属”,成分一般“黑”,恋爱也不“红”,小伙子居然对姑娘憨憨地说:“你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你爱我。”
一天,张先痴发现胡光君箱里有一条半透明纱裙与一件红艳上衣——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胡君怎么会有这类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才拥有的东西?
此前,他在一位战友背包里发现一床红色花被面,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铁证”。可女友这两件资产阶级服装竟是组织上发的礼服,“第二职业”需要。每周六晚,她都得上李家花园陪首长跳舞。青年张先痴更惊了,红色将军也会喜欢“蓬嚓嚓”——资产阶级靡靡之舞!他们不知道:各地红色首长不少亦好这一口,“解放初期天津市的有些领导经常在解放路交际处举办舞会,用小汽车到圣功女中接一些有姿色的女学生去伴舞,很晚才送回学校。”[2]
胡光君虽然只是幼儿园保育员,可是为高级首长培育“革命接班人”,也是重要岗位,万一“阶级报复”…… 1954年一起“被复员”,入南充专区医院。
最初阴影
1955年,胡光君18岁,张先痴21岁,法定婚龄,各打结婚报告。南充县府人事科派员去胡光君单位通报:张父被镇压,张本人也有历史问题,要胡慎重考虑。一心向共的张小伙没想到组织上会这样。当胡光君向他转述组织“忠告”,他大哭一场,写了诀别信。幸好“被镇压的”没嫌弃“被镇压的”,总算结成婚,婚礼十分简陋,“规格”很低——无一位副科级以上干部莅临祝贺。
1956年,张先痴将凉山当兵经历写成散文〈金沙江边送别〉,发表川省刊物《草地》创刊号,稿费40元,加入南充巿文联,兼任市文联杂志《百花》诗歌编辑。不久,省刊《草地》又发表他五百多行长诗,稿费每行近一元,成为县级机关首富,买了一辆自行车(比现在宝马车还稀罕),一时得意。
1957年,“反右”狂飙天降,鹏程万里的文学青年一下子沦为“极右”。他请20岁的妻子重新考虑未来。胡光君连夜写报告,向组织申诉,说与丈夫朝夕相处,保证他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报告一递,当天就被揪出——“自己跳出来右派”!夫妇“同归于『右』”。艰难时刻,胡君派六岁小姑送条给丈夫:“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3]
“反右”运动中,南充市文联全军覆没。当年挤都挤不进去的高雅殿堂,成了躲都躲不开的阴森地狱。
艰难赴疆
张先痴划“右”后送劳教,胡光君开除公职,遣返原籍,带着两岁孩子回到渝郊长寿县华中公社。娘家父母双亡,茅屋将塌,丈夫几件毛料衣服与羊毛背心被村吏搜走,扔下话:“身边没有男人,为什么有男人衣服?”她背着孩子上成都找到婆婆,饥饿的张家又增加两副需要填充的肠胃,婆婆毫无怨言接纳了儿媳、孙子。
1958年,张先痴二妹考取大学。报到第二天,学校发现她有一个劳教的“右派”哥哥,勒令退学。二妹大哭,前景辉煌的大学生瞬间沦为最没出息的待业青年。此时,新疆建设兵团技校在成都招生,二妹不愿去那遥远的地方,胡光君便借小姑的高中毕业证应考,旋被录取。新疆地广人稀,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农垦部长王震想成为“当代左宗棠”,希望移入大量汉人,毋须户口迁移证。胡光君没有城镇户口,“天赐良机”。于是,她冒名小姑张先云去了新疆兵团技校,儿子只能放在奶奶身边,否则高中生怎么已生孩子?
张先痴大妹在西宁,要母亲过去带她的孩子。大妹嫁给劳改队首长,她的孩子可是“革命接班人”,怎么能让母亲在成都带“右派的儿子”,而不带自己的“革命接班人”?无奈,胡光君只能将孩子托付给弟弟——兰州铁路局“右派”,开除公职后回乡。“右派”舅舅带了“右派”姐姐的外甥。这一托付,这位“右派”之子终身文盲。
大饥荒时期,胡光君从新疆不断以二妹名义给“吃官司”的丈夫邮寄日用品,包括十分稀缺的维生素。张先痴不服管教,越狱脱逃两月余,在天津抓回,送原劳教队,加刑至18年。他不断回信暗示——
我欠你二嫂的已太多,她随便怎样安排今后的生活,我不会有丝毫异议。
胡君二嫁
胡光君从新疆兵团技校毕业后,分配当地拖拉机修配厂,一晃已二十六七岁。不少男人追上来,热心介绍者也接二连三,工会、妇联都很关心她的“个人问题”。援疆青年毕竟男多女少,肉少狼多,资源紧缺。胡光君拒绝交友,已传“生理问题”、“心理有病”。她既不能向人吐露罗敷有夫且有一子,更不能说冒名顶替,还是“右派”。
1964年,张先痴因“叛国罪”加刑至18年,胡光君绝望了。1965年,已28周岁的她,只得嫁给一位中专技术员,不久生下一儿一女。双职工带孩子是个大问题,胡君向前婆婆求援。前婆婆放下直系孙子,赶到新疆为前媳妇带她“与其他男人生的孩子”。
文革爆发,张先痴在西宁的一位弟弟,忌恨母亲去新疆为“前二嫂”带他人孩子,向胡光君单位写信揭发:冒名顶替报考、隐姓埋名的“右派”、且早与“右派”二哥结婚并有一子。检举信一到新疆,很快挖出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我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成果”!
中专技术员原本就性情暴躁、嗜酒如命,得知老婆的“真相”,委屈大去了——“双重受害者”,政治上婚姻上都中了“右派”圈套。从此,酒后就打胡光君,骂她“一条毒蛇”,不到头破血流不停手,还罚她通宵站在床头反省。“前婆婆”受株连,撵入废窑洞,只得辗转返回西宁。
最后绝唱
1979年,狱中“右派”大多平反出监,张先痴知道难期将尽。此时,他在监狱医院教外语,一位19岁女护士看上他,闹了一场师生恋。张先痴最终止步,因为心里还装着胡君,很想破镜重圆,无法与19岁小护士“肝胆相照”。1980年,小护士嫁给一位出狱医生。那年月,政治犯“质量高”,常闹出监狱看守爱上犯人的花边新闻。
1980年8月23日,张先痴终于收到平反裁定书,对他22年7个月13天的苦难,所有的国家赔偿只有三个字——“向前看”。
二妹夫妇从成都赶到凉山来接兄长。回成都途中,二妹向张先痴介绍了胡君近况,劝他不要直接写信,以免影响她的家庭关系。张先痴直到此时仍对组织抱有幻想。中央政策规定:凡因“右派”离异的夫妻,原单位应尽力协助恢复关系。回南充后,张先痴不愿再回原单位民政科,三个月后入某厂技校执教。他一直忍住未去找胡君。
1981年春节,张先痴上西宁与母亲团聚。回成都后,二妹告知:“胡君来过了!”原来,胡光君回成都探亲,新疆技术员丈夫担心她与前夫联系,派两孩子随行。胡君未上二妹家中,怕遇到张先痴会抱头痛哭,伤害两个孩子心灵。她上二妹的工厂,背着孩子递给二妹一封信——
亲爱的先痴:
我们还能同时活在这世上,便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南充的朋友来信告诉我,你渴望与我团聚,为此我也感到欣慰。坦率地说,我身边这位丈夫给我的伤害比给我的爱多得多,只是我实在舍不得我这一对儿女,他们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也不忍心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去经受失去母爱的痛苦。思之再三,我决心继续把自己钉在受难的十字架上,原谅我吧,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心灰意冷,要重新站起来,自强不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私人生活上。你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就足以陪伴我心力交瘁、病弱衰老的风烛残年……
永远爱你的 君[4]
一封笔者读到的最感人情书,比茶花女写给阿尔芒的还要感动。张先痴无奈,只得另组家庭。2011年9月30日,笔者向沙叶新先生感叹:“这则题材如写成剧本,都有点玷污其神圣,只能拍纪录片!”
三幕殉情
一、胡光君在成都保育院时,有一位最要好的闺蜜,十分漂亮的川妹子黄代玉。一次周末伴舞,遇到战斗英雄刘子林(显赫度不亚于当今影星),英雄向美女求爱,美女含羞接受。但黄父也是被镇压的“反革命”。明确关系后,组织上向刘子林“交底”,战斗英雄只能撤退。1955年,黄代玉又谈了一位保卫干事。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成分太差,不适合成为党员干部之妻。黄痛不欲生,与保卫干事在成都东门大桥相拥投河。1957年春“鸣放”,《人民日报》驻川记者李策发表了〈他们为什么自杀〉。
二、1950年6月下旬,“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驻扎渝北合川县。一声巨爆,血丝肉渣顺流漂下。原来,文工队区队长(南京大学生)与漂亮女生相携参军,一起进军大西南,向往革命烈火中锤炼青春与爱情。漂亮女生能歌善舞,四个月前被上级文工团调去,前些天获悉女生经组织介绍要嫁首长。介绍过程:基层领导先出面,女生以目前不考虑个人问题搪塞;二号首长出马,女孩只好说已有意中人,恋爱两年多了。首长的回答令她再度吃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做工作。”首长最后说:“我们有些青年同志口口声声说为革命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一遇到具体考验,问题出来了……”女生只得含泪答应。结婚之日,区队长拉爆手榴弹自杀。
三、国民党“起义”电讯干部谢邦琼(24岁),爱上一女孩,但女孩被组织安排给首长。尽管谢邦琼从小在长沙孤儿院长大,仍因“前国民党人员”遭清洗,两名保卫干部押离凉山剿匪前线。途中宿旅,谢邦琼趁保卫干部不备,偷过手枪自杀。[5]
饥饿与性
1961年,张先痴服刑于四川公安厅劳教筑路二支队108中队,进驻川东北旺苍县快活场。此时,每月口粮从48斤降至35斤,干着重活的“右派”只能用衣物找老乡换食。张先痴用一件毛衣换了一只鸡,请那位乡妇煮好,晚上去吃。是晚,下了学习,张先痴不敢擅离宿舍,因为违纪,会被怀疑逃跑。只得邀请班长一起享用,万一有麻烦,可分担风险。乡妇不到三十岁,红光满面,身体很好,丈夫在外打工。她如约将鸡炖好,放在后房卧室以避耳目。两个男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乡妇守在旁边问好不好吃?孩子睡着在床。
吃到只剩下鸡汤,班长虑及毕竟人家用毛衣所换,提前离去,以便让张独自喝尽最后一粒油珠珠。张先痴刚吃完,乡妇突然挨过来,紧紧抱住张先痴,滚烫的脸庞贴着他的脸,随后脱裤子到床头马桶撒尿,尿完后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去拉呆立一旁的男人,然后裸着下身横躺床上,示意张上来。
我却感到极度紧张,劳教分子干这类事是非常危险的,又加上我对这种粗糙的作爱方式似乎还有些为难。但我毕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便也脱下裤子准备如此这般地来个婚外性行为。没想到当了父亲的我,竟然象一个阳萎患者那样无能为力。她在下面不停地悄声喊着:“展劲!展劲!”我却展不起劲。后来我知道,这也是“自然灾害”留下的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看到这位女老乡过去那嫣然的笑容,哀怨的目光对我说的是:“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这块心病久怀难释,每当劳教队再来家属探视,张先痴都在心里默祷:
上帝保佑他们不要和我一样“不中用”![6]
“精彩”轶事
《格拉古轶事》的真实度还可通过作者的自我检举得到印证。1957年6月8日,张先痴一位同事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愤曰:“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只有两人在场。当时还想当“左派”的张先痴卖友求荣,向组织揭发这位同事的言论,“当时我简单地想法只认为对党应该老老实实”。
张先痴还自揭一起偷窃。1961年9月,他逃亡途中在新潼关百货公司与扒手联合行动,将四双偷来的袜子贱卖农民,换了两大碗盖浇饭。
文革时期,四川公安厅劳改局第108筑路中队彝族分队长,奴隶娃出身,向犯人训话:
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7]
人民写史
中共老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个个被平反的“反革命”、“右派”算不算“人民”?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一幕幕一天天是不是历史?
毛时代遵循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一再制造敌人,日益扩大“对立面”——土改斗死地富及其家属至少百万,镇反又是百万(中共炫耀的数据),思想改造运动至少整了二三百万知识分子,“三反”、“五反”、“肃反”又整了至少500万,“反右”55万余“右派”、“中右”150万,“反右倾”200万,大饥荒至少饿死4000万,文革再整了一亿人、整死二千万。如以一位冤屈者或挨整者至少连着五六位直系亲属,毛时代几乎将国人得罪遍了(其时全国人口七、八亿),人人自危,人人担心“专政铁拳”哪天砸到自己身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只剩下几十万处级以上官员,真正获益者只有二三万厅级以上高干。“人民政府”,人民安在?这些是不是历史?
毛泽东晚年最怕身后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九·一三”后,以他的精明,应该知道“完了”,但以他的狂妄,绝不会想到完得那么快。无论如何,估计老毛决不会想到自己比斯大林还惨——他的党还没出赫鲁晓夫,民间就已一页页一册册在做他的〈秘密报告〉,而且是不可能翻案的“最后审判”,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
2011-10-1~3上海
[1]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19。
[2]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34。
[3]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87、297、120。
[4]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01、120、34~41。
[5]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58~166。
[6]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42~44。
[7]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87、248、43~44、21、76~77、261。
原载:《开放》(香港)2012年3月号
博评精选:
“展劲展劲”印象深,毛衣换鸡饿与性;墙壁虽白人说黑,训话队长奴出身。
可悲的时代,可怜的人们,可恶的暴政。
平铺直叙,却看得惊心动魄。五千年文明,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欠的这些账,怎么才能清算呢?“反右”早就知道,但具体事件所知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