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6)

俄国各界的反思(36)
俄罗斯右翼对苏联解体的反思还有下列原因:
5.俄共破坏了苏共和苏联的统一
原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认为,俄共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在2000年10月4日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说: “现在人们忘记了正是俄共对苏联解体起到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成立了一个‘俄罗斯CP人’团体,它作为一个由216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党团被登记在册。6月19日随即召开俄共成立大会。实际上是苏共发生了分裂导致国家本身的分解过程加剧。正是这个俄共中央加入到了同中央政权的斗争当中。因此,当现在许多CP活动家指责他人使苏联解体了,我想提醒他们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左派和右派全都对苏联解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人民而外。”
哈斯布拉托夫2001年接受《论坛报》采访时说: CP人“破坏了统一,从苏共中分出了分支,在建立俄共后开始折磨戈尔巴乔夫。出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位CP员作家第一次公开说出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的想法。CP人实际上一致同意退出苏联,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反对俄罗斯主权的人只有五六个”。
曾两度出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的沙赫赖2001年12月14日在《论据与事实》上发表的题为《苏联为什么死了》的文章也认为俄共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说: “很少有人记得,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俄罗斯没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在俄共于党的关键时刻建立,在俄共与联盟的领导形成对峙后,波洛兹科夫(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久加诺夫(俄共中央主席)对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停步。1991年9月筹备召开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目的是把戈尔巴乔夫从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位上撤下来。戈尔巴乔夫不无担心地同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们谈判,答应极大地扩大他们的权力。但这些谈判根据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被记录了下来’,传达给了‘党内的同志’。结果发生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叛乱,这是最后的一滴水,从而使天平向苏联的解体一方倾斜。”
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CP代表大会召开。从俄罗斯联邦选出来参加苏共二十八大的27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是否成立俄罗斯CP的问题。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俄罗斯联邦局主席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并作了题为《为俄罗斯和全国的命运负起责任》的主旨报告。他说: “成立俄罗斯联邦CP是合适的和必要的”,但要“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俄罗斯联邦与苏联的对立,俄共与苏共的对立”。戈氏在报告中提出,苏联“必须转入市场经济,不能回到行政命令体制。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并不对立。”他承认: “党犯有错误,对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估计不足。党内斗争也很尖锐,有一些人怀疑党的方针是否正确。”他呼吁党振作起来,“在自由竞争中保持苏共的政治领导地位”。他批评了成立俄共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建立议会式的俄共,使俄共成为俱乐部式的组织,从党内来破坏CP;另一种是企图使俄共反对改革,把改革看成是修正主义的。戈氏强调,生活发生了变化,党也要发生变化,否则会被大水冲走。
大会围绕怎样克服苏联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和俄共建党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塔斯社报道说,“尖锐的批评性质是这次辩论的特点”,“苏共领袖过去从未在党代会上受到如此严厉的评价”。克麦罗沃州委第一书记在发言中说: “一小批人垄断了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中央委员会和党本身却被排除在外”。他还批评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苏共民主纲领派代表李森科则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目标”,他主张放弃这一目标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并改变CP的名称。经过辩论,大会于6月20日宣告俄罗斯联邦CP正式成立。会议通过的宣言表示,俄共是苏共的组成部分。大会于22日选举55岁的苏共克拉斯诺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
俄共的成立对戈尔巴乔夫是有利的。戈氏是按照这样一个政治脚本来设计俄共的,即使其成为叶利钦政权的对立面和牵制因素。但也像法新社评论的那样,俄共成立大会“显示了保守派的强大力量和戈尔巴乔夫的虚弱境地”。
俄罗斯右翼提出苏联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是:
6. 政治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导致联盟的瓦解
前文提到的《大革命》一书的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演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过程,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该书作者把1987年初以前时期定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他们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任何重大的行动可以称之为深刻改革现存制度的尝试,但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新因素,标志着革命的前提已经成熟。第一,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导致经济形势恶化不可避免。第二,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急剧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方向,奉行停止冷战和军备竞赛、减少军费开支的方针。同西方关系的总的调子发生了变化。第三,意识形态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强调人道主义原则和人的因素,同动员型机制发生了不妥协的矛盾。第四,新领导的地位表现出矛盾。一方面他们进行谨慎改革,同过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新领导人的上台引起社会的期望,这种期望远远超过了所进行的改革的实际潜能。
《大革命》一书的作者认为,1987一1988年期间,“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逐渐演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 时期。这一时期的外部表现特征是: 首先,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被吸引到政治中来。国家当时并不反对建立非正式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有发展成政党的趋势。其次,各个精英阶层之间冲突尖锐化。如企业工人积极参加经济方略的决定,如由劳动集体来选举厂长等;从1987年试图在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中实行差额选举,在挑选和任命干部问题上的原则改变带有激进性质。由此也引起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传统的最高苏维埃改造成两院制的议会。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以此替代政治局和苏共中央。取消宪法第六条,苏共作用因此降低。国内各个官僚集团的矛盾尖锐化。第三,旧的意识形态的方针被根本取代。虽然还保留“社会主义选择”不可动摇,但却强调现存的社会制度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为此需要改革。开始传播捍卫现存制度并不等于捍卫社会主义的思想。公开性的界限扩大了,意见越来越多样,对“社会主义成就”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正是从1987年开始当人们越来越习惯“公开性”这个词的时候,官方正式推出“社会主义多元化”(实为言论自由的委婉说法)这一术语。其结果导致社会严重分化: 在上层表现为出现左的和右的反对派;在下层表现为各种群众运动,如从1989年起遍及全国各个地区的罢工、集会、示威不断。各加盟共和国建立人民阵线组织,民族冲突,与苏联的离心趋势加剧。
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先是党内的保守派对他的压力。保守派几次胁迫戈尔巴乔夫下台。“八一九”事件只是保守派的最后挣扎。一开始戈尔巴乔夫想同保守派合作,因此牺性了不少改革的成就。这引起强烈反应。1991年3月莫斯科的民主力量组织大规模的支持叶利钦的行动;5月的示威喊出了明确的反戈尔巴乔夫的口号。戈尔巴乔夫又急忙改变方针,开始积极讨论新联盟条约问题。新联盟条约实际上使权力从中央完全转向各共和国。这时,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就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了。形势因此不可逆转,最终苏联以基本上和平的方式瓦解了。
从“自上而下的改革”演变成“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论断让我想到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一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的论断: 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的结果。它对此的解释有令人信服之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领导人的政治家,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一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些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的最高层领导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8月政变的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倡导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惟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莫斯科CP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了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演变的最终解释是: 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提出这一论断后,该书列举了许多论据去证明,后面再继续引用。现在再回到俄罗斯右翼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上,从这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苏联解体的党国精英作用。
亚夫林斯基认为,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讲台。在1990年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持激进态度的反对派和一些共和国的分立主义力量以微弱优势取胜。政治斗争开始转变为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1990一1991年形成了中央政权机关同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关的对峙局面。苏联宪法中关于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变成了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的口号: 一些共和国宣布不加入苏联,另一些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本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处于最高地位,开始“法律大战”。企业对各级国家管理机关的从属关系问题变成了分配联盟和共和国财产的问题。地方苏维埃通过把地方所有财产从国家所有制中分离出去的法律,各个自治构成体宣布自己拥有主权。1990年下半年国家进入政治和经济无政府状态加剧的时期,在还未用市民社会的横向联系取代之前,极权主义国家现存的自上而下的联系开始迅速崩溃。
在这些条件下提出了“五百天计划”,试图在实行硬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连续不断地放开商品价格和逐步使卢布可以自由兑换,加快发展市场结构和企业的横向相互联系,以便稳定经济和实行改革,把中央经济机关改革成跨共和国的管理机构。但是“五百天计划”在1990年10月被苏联最高苏维埃驳回。戈尔巴乔夫也不再支持该方案,他立场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亚夫林斯基认为,对“五百天计划”的攻击与其说是私有化引起的,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签署经济条约就会排除签署政治条约的可能性,各共和国将不再需要中央,自然也就不会再需要苏联总统。
在放弃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之后,苏联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实现政治一体化和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但是这一进程处于各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领导人的强大压力之下。签订联盟条约势必导致整个联盟政权的全面改组,包括撤换领导人。这就是1991年八月叛乱的实际原因,政变分子没有得到人民、军队和大众传媒的支持,以全面流产告终。从1991年8月底开始,政治局势急剧改变,整个的联盟政权结构实际开始重新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在俄罗斯的压力下放弃了对签订联盟条约的研究和准备。苏联立法机构的工作被暂停,苏联政府被消灭,建立有效能的经济联盟的一切努力又一次被破坏。这一政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消灭苏联和建立象征性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亚夫林斯基说: “20世纪的历史表明,革命往往发生在俄罗斯社会在道德与精神上同政权相隔绝的时候。1917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俄国君主政体不再存在;1991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失去了人们信任的、名声彻底败坏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自己的谎言和无所作为的重压下崩溃了。”
很赞同上文的最后一个观点: 1991年,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了”。苏联解体的实质是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格.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英文版名为《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1993年出版时,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伯特写了一篇前言,对书名提出了他的解释。他说: “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仍然使人感到伤脑筋: 这个跨越了11个时区、占有1/6地球土地面积、毁灭或饿死了成千万公民的,却又是把第一个人送上太空、赢得了一个超级大国称号、在40多年时间中使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的不寻常的政治大杂烩,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回过头去看,苏联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有生存力的国家。它的2.8亿人口讲着太多的语言,彼此有着太多的怨恨,都不喜欢把它们紧紧地束缚于全联盟首都莫斯科的联系。苏联实际上也不具有帝国的特征,尽管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帝国。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这个帝国的宗主国,可是到头来俄罗斯也只是这个各族人民监狱中又一个不满的囚徒而已,而当监狱大门被打开时它也要求出狱,成为又一个要独立的国家。如果苏联既不是一个国家,又不是一个帝国,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名称就是阿尔巴托夫用作他的书名的那个词,即苏联是一种制度,而根据我的辞典,制度的意义就是‘由许多从属于一个共同计划或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
这里对“制度”的定义比较抽象,但说白了,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些人结合成团伙“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当他们发现这个理想根本无法实现时,他们决定散伙。结果是制度崩溃,国家瓦解。
问题在于西方的制度为什么能延续几百年,而苏联的制度不到一百年就崩溃了呢?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研究。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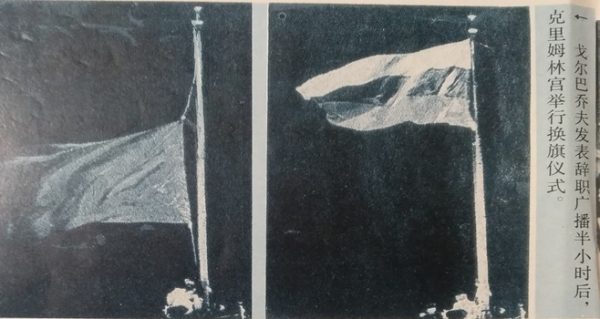
荀路 2022年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