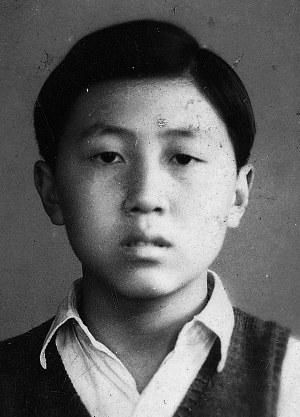11.毛主席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解放第一年是在困难中度过的,毛主席说了:“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九个字。1950年“红五月”纪念宣传活动很多,也是环绕着这个。大概就是在“五四”那天晚上,上海市在跑马厅搭起台子来召开了全市青年团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本致开幕词,我早在普陀区某个礼堂开的一次团干部会上听过张本的报告,她是一个文弱女知识分子,个子不高。陈毅市长也在会上作了报告,由于我在四川生活过,他那一口的四川话我听着特别亲切。特别记得他说到刚解放的时候群众欢欣鼓舞:“年轻娃儿敲起了棒棒打腰鼓,那个劲头大噢!”接着说到许多人在“二六轰炸”遇到困难后有些泄气了。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会说话,这个指挥打了二十几年大仗的人,说起话来幽默、机智、豪爽。他从天刚刚擦黑一直讲到深更半夜,足足有四五个钟头。他自己一点也不累,我们听着一点也不感到困,他讲的正是大家关切、困惑、忧虑的,他的话既能解惑,又很鼓气。
为了应付当时的困难,人民政府在全国发行了一种“胜利折实公债”,顾名思义,是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发行的。“折实”的意思是,这种公债的面额不是人民币多少圆,而是折实单位若干,说明那时候物价还没有稳住,涨得厉害。全市大张旗鼓宣传动员,掀起认购折实公债的热潮。清心中学也在礼堂里举行了认购大会,宣传动员之后进行当场认购。可以个人认购,也可以由班级集体认购,造成一种声势和竞争气氛。那时我们这个初三班和王笃信(他解放前教过我这个班的地理课)先生带的那个初三班都集合坐在礼堂楼上,级任先生当然也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这两个年轻老师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开”,班级认购实际上是以他们为后台,基本上由他们出钱。学生坐在前面,先生坐在后面。报了认购数以后,听了别人报的还可以再加码,就像大拍卖一样。沈锦辉和我们在前面朝着台上大声报数,听到哪个班超过我们时,我們就赶快回头去看陈拱龢。于是他就给我们甩过来一个新数目,或者只做一个手势。我们就大声叫出去。结果认购大会成了这两位争强斗胜的“小开”大“别苗头”的擂台。搞得大家很开心,都朝着这两个年轻气盛的先生做拉拉队鼓劲。作为团总支委员我自己也带了头,除了手上的钱悉数拿出之外,还向家里要了些钱。
这时我开始懂得了“站稳阶级立场”。
妈妈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叫吕亦陶,我大约一岁的时候妈妈独自回昆明探亲,曾经把我寄养在吕亦陶家里,于是她成了我的“干妈”。她丈夫冯友真抗战时在屯溪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在我刚进清心中学时吕亦陶曾和一个美国神父说好,等我初中毕业后把我送到美国加州去上学。她的两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女儿早已在那里。1948年冯友真飞往台湾办理中央社迁移的事,所乘“空中堡垒”(由军用飞机B-29改装的)飞机失事遇难了。“干妈”则在解放前不久去了香港,在皇后大道开起一家服装公司。那时和妈妈常有书信来往,解放前夕还寄过两件羊毛衫和一支“原子笔”(即后来的圆珠笔,那时我在上海还没有开过眼界,质地精致,价钱很贵)给我。
我成了青年团干部以后,则满怀革命激情以诚挚的态度给干妈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宣传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分析批判”了冯友真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劝导她和冯友真彻底划清界限,回到上海来为人民服务,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妈妈在“肃反运动”中的交待说,解放后吕亦陶还曾在来信中提到她女儿已在美国结婚,她也想移居美国等等,想来就是接到我的信之后,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不敢来信了,从此后和我家消息完全断绝。
虽然我那么幼稚,我那时心里也没有认为这是因为她“太反动”,我想她只是被我吓着了,因为她去了香港没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完全不懂得“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等革命道理。
清心中学收费是比较贵的,后来家中生活困难了,改为走读,爸爸还和我一同去找教务主任徐中一(绰号“老黄牛”)申请过助学金。为此,爸爸不敢穿以前出门穿的深蓝色毛料长袍,特地穿了件家常的灰布罩袍去。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我在自己日记上向家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斗争”,就说这件事情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父亲”弄虚作假唯利是图思想的典型表现。责备自己当时觉悟不高,立场没有站稳。
后来进了上海中学以后究竟收不收学费,我现在已想不起来。我就是这样在家里“从来不问柴米油盐”,但我并非“纨绔子弟”,我想我当时进步快的诸原因之中也许包括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性比较容易接受那时“革命队伍”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比起小时和我同样家境的人来,我一直很节俭,爱惜东西,讨厌奢侈浪费。除了必须用的钱,我极少向父母伸手。住读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补袜子,一双袜子往往补了又补。那时候的袜子都是棉织的,也容易破。久之我就想,科学发达了总有一天会发明出一种像橡皮一样结实的东西来做袜子,总穿不破,那才好。还不到二十年以后果真出现了各种尼龙袜子,和我幻想过的“橡皮袜子”差不多。走读的时候,要坐电车去上学,英商电车公司的车,前面一节是头等车厢,长一些,里面座位多而且有靠背;后面一节是三等车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二等车厢),短一些,只是沿着车窗的地方有长凳,大多数人都只好站着。当然票价是不同的,我几乎从来都是坐的三等车厢。
我这种看来很矛盾的习性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方面在经济上从来是个丢三落四的“马大哈”,买了东西刚回到家,别人要问我价钱我就答不上来了。要问我现在有多少钱,什么时候我都得问了太太才报得出。在单位里评上哪一类“先进”才和长工资有关系我长时期都不知道,后来是太太知道了对此非常恼火,才叫我开始明白了的。1970年底我下放到湖北南漳县山区去劳动了三年,回武汉以后单位里的人才告诉我附近银行储蓄所有我一笔为数不算小的存款,他们到单位来查找存款人胡某到哪里去了?我那时简直对此毫无印象,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我买菜不好意思还价,所以常常吃亏,只有买便宜的青菜时太太才放心让我一个人去买。可是另外一方面,平时人家总是觉得我这个人节约得太“抠门儿”,买东西都舍不得买贵一些的;一口剩饭一点菜叶子都舍不得丢;冲了好几次的陈茶叶舍不得倒;一张写过字的纸只要还没有写满就要留着打草稿用;如果在家里不出门,我就会把十几年的破旧衣服拿来穿,必要“物尽其用”,除非是捐了出去有别人接着穿,心才得安。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习性就是习性,我很清楚这和利害算计毫无关系,我对用公家的东西也是这么“抠门儿”的。大概只是天生的不忍暴殄天物,这种性格眼下很不合时宜,不仅时尚的年轻人嫌我完全没有现代消费观念,“老派”的同代人也经常说风凉话:“怎么这样想不开?”。但我在大得大失上却表现得比别人更“想得开”,事例很多毋庸赘述了。这也许与我经历过不少大起大落有关。
这些年观周围事例我还有那么点实际体会:解放前舒服过,见过点“世面”的人,到困难日子来的时候(例如三年“大跃进”)照样也心安理得挺得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过好日子的时候,这些人大概是“历经沧海难为水”,反倒并不屑于讲奢侈、摆排场,过得实惠就行了。
12.转学
但是我那时还不够进步,“立场不够稳”。那就是当我个人的志趣和团组织对我的要求起冲突时我那次选择了个人志趣,初中毕业时去投考了上海中学。
初中三年级有物理课了,物理先生郁青田在清心很有点名气,课讲得很精彩。你如果对周围看到的现象喜欢追根究底,你如果对和你一起存在的这个世界喜欢一个劲的往深处想,那么你一旦接触到这门叫做物理学的课,就会感到兴奋不已,显然我就是这样的人。初中三年级是我开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也是我理性思维开始萌动的时候。
恰好这时,我遇上了新社会和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同时又遇上了物理学。就好像同时遇到了两个都那么叫你动心的姑娘。不同的是,不应该说在革命事业和物理学之间你只能选一个,好在那个时候热情和精力是用不完的。我发现物理学能满足我从小追求解释清楚一切的癖好。在那个年代,初中物理课内容主要是讲些初步的而且是经典的知识,像牛顿力学、经典热学、几何光学、电学的初步、经典的原子概念等。当然郁先生讲课时也对现代物理学新进展方面略有提及,但不可能展开讲。所以我们学的大致上是18世纪到19世纪前、中期的东西。这些经典的物理学成果虽然是在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用了专门的实验方法得出的,但是它还是比较接近普通生活的直观经验。由于我从小喜欢冥思苦想,有些猜想在我脑子里或多或少已经朦胧地存在着了,有的想法已经接近了希腊人的水平(他们还不知道做实验)。所以我听课的时候,常常“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也正因为这样,我很容易把这些东西看成了先验的终极真理,就像那时我已学过的欧氏几何学中说的“公理”一样。于是我一度很快地在哲学上自发地陷入了机械论,以为原子概念加上牛顿力学定理就可解释或推论出世间万象。
到底是谁对我首先提出初中毕业以后去考上海中学的建议,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接受了这个想法。原因就是那时我对学科学的热情正在萌发,而到上海中学去,无疑最能满足我的这种向往。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沈锦辉,虽然那时在团内我是他的“领导”了,但在我心目中还是把他当作兄长和引路人。不料他不赞同我转学,说这里团的工作需要我,还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替代。我大概是从他的劝告中第一次听到,关于个人志向和革命需要有抵触时必须服从后者这个道理。但是我太向往上海中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在组织能力等方面还很“嫩”,章北威、顾伯衡特别是沈锦辉自己都比我老练,为什么他们不能来担任团总支委员呢?虽然我还是很认真地考虑了沈锦辉的意见,但最后终于拗不过自己的愿望,还是决定投考上中。见我决心已定,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接着,我又一次在一件小事情上和沈锦辉的意见相左。初中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打算各走各的路,这意味着老师同学们要分别了。不知道究竟是陈拱龢先生还是哪位同学的动议,要去制作一枚毕业班的纪念戒指。班会上决定,有兴趣的人都来参加设计,提出方案,然后让大家来评判选择。我当然也有这个兴趣,虽然我在美术上一直没有注入过多少精力,但自觉身上还有点“艺术细胞”。我突然想到,清心中学历来用的练习簿封面上都印着花体字的英文校名“Laurel Institute”,花体字本身就是很好的美术图案,我就选用了它的缩写“L I”。因为练习簿封面上整个词排成一条圆弧,所以每一个字母的上下边缘都略带弧形地向上拱起。我设计的戒指面板像一个纵切啤酒桶的截面,大体接近长方形,但上下两个长边都是略向外凸的弧形。于是把上述“L I”两个花体字放进去以后,字的上边和戒指面板上边框弧线平行对齐,而在两个字母和下边框之间留下一个梭状空白,正好可以填入我们的级号“1950”(即1950年初中毕业班)。戒指是银质的,字和边框都采用凸雕,余下的凹处,填以漆黑的釉。黑底银字,应是简练、素雅而悦目。
参加设计的同学的作品都出来了,那次由陈先生主持班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设计画在黑板上,大家来评选。画出来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的含义不清,有的太花哨,有的突出了政治意义,画面搞得很繁复,差不多像国徽了。等到都画出来后,陈先生一眼就看中了我那一幅。他还是过去那个脾气,断然下结论,不容分说。认为显然只有胡某人设计的这个好,很雅致很大方,其它的做出来都不像样,于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
可是这时候,沈锦辉却提出了抗议,他认为我那个方案太“洋化”,和新时代、新中国有些格格不入。解放后有一个短时间,不仅在学校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认为“解放”和“民主”是天然连在一起的。那时进步同学很喜欢唱的一首歌,不是叫《民主进行曲》就是叫《民主青年进行曲》,唱道;“嘿!我们,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看灿烂的太阳升在东方,……在广阔的大地上,封建和独裁就要灭亡。”有要紧事情,都通过开会来讨论决定。先生和学生都是平等的,并且遵守一定的议事规程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过,那次绝大多数同学都附议陈先生的意见,我的方案就被选定,而且很快便制作成了戒指,戴在了大家手上。
从我与沈锦辉一年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当时提出这些指责完全不像后来政治生活中那种扣帽子、打棍子。那时他和我一样真诚地在领会和接受共产党的主义,所以我们都有着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我们也许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大一样:我那时已经表现出不乐意把审美完全政治化,以政治淹没了自然的审美。不料这一点苗头,后来滋长发展成了我的“右派思想”和“右派言论”的一个方面。
但是后来到上海中学以后,从清心中学初三另一个班考去的邱善昌(后来和我是团支部委员会的老搭档),看了我戴的戒指,却也很不以为然。他倒没有评论我设计的图案,而是鄙夷我竟戴银质戒指。他说:“这像是江北人戴的!”上海人对“江北(苏北)人”的轻蔑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什么东西一说:“像江北人的”,那档次就掉了一截。邱善昌以此来评论这枚戒指,意思是说它土气、俗气。好在他只是嫌戒指是用银子打制的,与设计无关。不过经他这一说,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戴它。
离开清心前夕,我和许多人一样,拿了一个本子遍请老师和同学们题写纪念词。那是从爸爸那里“揩油”来的一个精装簿面的左右长、上下短的本子,里面的纸张红、黄、蓝白好几种颜色,大概就是专门为题词用的。爸爸的公司散摊子的时候,分了些办公用品带回家来,有砚台、笔筒、订书机,甚至空白账簿,还有一个很大的红木做的吸墨水器和这个小本子。国文老师李彬之先生用毛笔为我写了一页漂亮的隶书,但是内容我忘了;美术老师华并英先生画了题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八个字的“钢笔国画”;陈拱龢先生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两页纸,表现出他对我这个学生的格外器重,而且用的是对挚友的口气。他的钢笔行书真的“字如其人”,在潇洒中带着刚劲。总之,我说过,做了我两年多级任老师的陈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外貌、穿着似有点“花花公子”,但内心深沉,学养不薄,多少有点心高气傲,不轻易苟同时流。后来听说他和我一样成了“右派”,看来好像有此必然性。
婶婶有一个沈家的哥哥(也许是堂兄)是乡下的地主,记得好像他们说是在松江那边的,但是现在想想挺奇怪,因为据我知道沈家是苏州人。那时可能已经风闻要土改了,他们一家人躲到上海他弟弟(即我们这里79号住的沈钟毅)家里来。他的一个儿子也来了,大概读书读得不错,来到这里也想考上中。他的名字好像叫沈鸿基,镶着一颗金牙齿,这大概是乡下地主少爷的一种标志。考上中有如登龙门(实际上上中的主楼就叫“龙门楼”),茅盾曾经专门以投考上中的情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但我们那个时候上中的入学考试已经不像茅盾的小说里写的那样要到郊区老远的本校去考,这个过程我几乎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笔试和口试都没有到上中本校去,是借用了市区哪个学校(我有一次去过震旦大学的印象,似乎就是那一次)的教室考的。我只对口试的情形还有一点印象,地点是上海西南区的一个学校楼上教室里,光线明亮,应考学生(都是经过笔试已录取了的)济济一堂坐在教室里。主考先生坐在讲台上,按次序一个个叫上去站在讲台下回答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我三年的同窗。
沈鸿基大概是没有考取,而且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人了。我一直没有去想过他们一家人的去向,早就忘在脑后了。
我离开清心去上中的那个学期,堂弟仲威就考进了清心中学。他也是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然后转学进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2000年清心中学建校1400周年华诞,编了一本书《人才从市南走出》(清心中学解放后改名“市南中学”)其中绝大部分是从耄耋之年到世纪末的后生老校友成才的自述,末尾有十多篇是由旁人执笔,讲述的都是清心中学几代成就最为显赫的校友。其中一篇就是学生对杰出教育家胡仲威的访谈录。
仲威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执教于本已有名的松江二中,他任教关键的数学课,使得凡他教过的班级在历年高考中都取得优异成绩,松江二中也因此年年稳居上海市名牌中学之列,后来他担任松江二师的校长。他和我一样没有入党,但也和我一样在五十三岁那年获得相当于大学正教授的特级教师称号(在当年这都属于特别冒尖的)。在获得的许多荣誉中,当了两届市人大代表,1994年被评选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东长治路690弄85号“资产阶级”胡家子弟中除了区区我在政治上闹了个不争气以外,年龄能赶上受到完整教育的胡田田、胡苹苹、胡仲威三人先后都成了大上海的市级劳动模范,胡苹苹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他们都心甘情愿一生投入在长年来被人认为没有奔头的中小学教育岗位,而就在这里他们成了凤毛麟角的顶级尖子,量极不亚于大学教授中的博士生导师。
13.德清新市“寻根”游
等待开学的时候,我和仲威到祖先的家乡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去玩了唯一的一次。
祖母姓陈,从来没有人提过她的名字,恐怕我们这一辈人都不知道,只见过户口簿上写着“胡陈氏”。
老家新市还住着她的一个嫂嫂,抗战胜利我们由重庆回上海以后她就来上海玩,在我们家住过不止一回。爸爸这一辈都叫她“舅母”。有一次她带来了她的儿子叫陈允生,看样子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好像比较瘦弱。长发,穿着灰色棉袍,我常见她在祖母房里双手笼在棉袍袖子里,不声不响蔫蔫然地坐着。后来才知道,那一次他们是来托大叔叔替他在上海找个差事的。
大叔叔把他介绍在中兴公司的一艘海洋轮船上当海员,经常出海。过了一年半载他又来我家的时候,样子完全变了,再不是一个乡下人的模样了,身体也变得壮实了。性格也“活络”起来了,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外面的见闻。我记得他说起船到日本,船员下船碰到东洋乌龟(日本人),就举起拳头吓唬他们,那些东洋男女都低头弓背而过,不敢犟。他们这帮人算是心理上得到些满足,他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在日本式的恭顺背后,人家内心隐藏着些什么。
说到我们去新市的事,因为解放前夕中兴公司的船都出逃了,跟不出去的人只好遣散。于是允生叔叔失了业,和两三个船员(大概是同乡)凑了些钱,打伙买了一条机帆船,跑黄浦江搞“城乡交流”(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时新名词)。黄浦江从上海一直往上游走,进入浙江的太湖流域,包括德清县新市镇。至少带我们去的那一次目的地就是新市。
我们是吃过晚饭上船的,那船停在苏州河口,外白渡桥和二白渡桥之间。那一带塞满了不少船,大的是小火轮,小的是舢板,机帆船是中等的。我们从来没有晚上来这个地方,而且是下河,一切都感到新鲜而兴奋。沿河点点灯火,半明半暗,我们是过了外白渡桥到右岸去上船的。允生叔叔小心翼翼地招呼着我们走跳板越过别人的船登上他们的船。船一时还不能走,我记不清他们说的是等涨潮还是等退潮。起先我们兴致勃勃地站在船上看周围的船和灯火,但是不久就打起呵欠来了。于是就睡觉,这才知道船上的“客舱”(实际上没有客舱,只不过是船员睡觉的地方)像个扁的大木盒子。从一个小窗口一样的“舱门”爬进去,大概只有两尺高,所以进去后只能匍匐前进不能坐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从重庆坐船回来时人家说的“黄鱼”(那些不买票白坐船的)。塞在这样的舱里,不仅是黄鱼,简直就是沙丁鱼。后来船终于起锚,“突突突突……”地开了。驶入黄浦江,经过外滩,经过十六铺,两岸灯光愈来愈稀少,我们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船正好到嘉兴,我知道已经在浙江地界了。好像记得在那里停了一下,嘉兴船码头那里我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它处在一个河流的三岔口。到一个地方你如果只看见车站或码头,总会误以为这个地方很小,那次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后来我有了经验,知道这个印象一定要修正,可惜直到现在我除了火车经过嘉兴看到有好粽子卖以外,从来没有见到过嘉兴城里是什么样子。那天还因为我是早晨起来第一眼又看到黄浦江,最让我惊奇的 是黄浦江变成一条“小河浜”了,但是水变得比较清了。
我们爬出来,翻到舱顶上面去吃早饭。白天也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坐坐,那上面好像还搭了一个布篷,因为正是夏天。饭菜是他们在船尾做的,很简单,舀给我们的是在上海平时很少吃到的糙米饭。但那天我觉得胃口特别好,而且他们做的菜里面居然有辣椒。天气很好,一路上饱览江南水乡青翠柔媚的景致。那时已在上海住了四年半了,这还是第一次见识了锦绣江南。
第二天清早醒来,没有再听到柴油机的突突声,也没有颤动的感觉,船已是停下了。倒是听到船外有人捣漱口缸漱口的声音。从“黄鱼舱”的窗口看出去,发现我们的船已经停在石头砌的岸边,有几级石阶上去是一条沿河的青石板路。路的另一边是鳞次栉比的青瓦屋顶二层楼房,漱口的声音就是从一家楼上的窗口传出来的。这时路上还没有什么人,许多人家的门板还关着。我们跟着允生叔叔上了岸。
沿着河边石板路走去,才注意到路旁许多房子的楼上都是突出来的,下面有柱子支着,就形成了一条遮雨的走廊。这一点和上海原法租界的一些马路(例如过去叫“法大马路”的金陵东路)很相似。允生叔叔领着我们转弯抹角走过一条条横的竖的街,竟有不少都是这样在河边的。河也是横的竖的,都不宽,河的这一边和那一边都有这种石板路的街,每走不多远就有一座连通两边的石拱桥。当然也有一些街巷是不傍河的,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一条不傍河的巷子。
据我的记忆,允生叔叔首先引我们去的地方不是他的家,而是“阿呜大伯”(炽麟叔叔)的家。那是一所不算小的旧宅院,有天井,楼下有比较大的堂屋,但是光线不怎么好,没有什么像样的布置,显得有些零乱。家主是“啊呜大伯”的母亲,是爸爸他们的婶母,所以我们也应该像叫祖母一样叫他“嗯奶”。我只记得她长得有点富态,老式女人的穿着。对我们上海来的亲戚很是热情,问长问短。“啊呜大伯”的妻子也在,我应该叫他婶婶;仲威应该叫他“大伯母”,或者为了和我妈妈区别开,也叫他“啊呜大姆”。当然这会把她搞糊涂的,不知“阿呜”二字从何而来。原来是仲威一家孩子们叫他“乡下大伯”,季威弟当时刚开始学说话,把上海口音的“乡下”说成“啊呜”,而“啊呜”则是上海人吓小孩时对老虎的叫法。季威这个无意中撞上诙谐的创意得到推广,除了我(因为他比我爸爸小,我应该叫他叔叔),大家都叫起“啊呜大伯”来了。听说这位婶婶解放以后表现非常“前进”,而且很精明能干,积极参加街道上的社会工作,还负了个什么责,忙得不亦乐乎。在我家就听到“啊呜大伯”拖着他那结结巴巴的声调,讲他老婆“前进”的情形,又像有点自豪,但更多的是揶揄挖苦(也许因为他自己是个“落后分子”),说得叫人捧腹。他们款待了我们一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她们把南瓜叫做“fan瓜”,却给我留下了印象。那时我以为是叫“蕃瓜”,后来到了三年“大跃进”饿肚子的时候,有时把南瓜当饭吃,我回过头来猜想她们说的其实可能是“饭瓜”。江浙虽然富庶,偶尔遇上饥荒,也要拿南瓜来当饭吃的。
晚上,允生叔叔把我们带到他自己家里去睡觉。也是两层楼房,但是比较窄,我们睡在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不知道为什么,他家里没有别的人,允生叔叔的母亲(就是多次来过我家的,爸爸他们叫“舅母”的那个瘦小老太太)也不在。第二天大清早 ,来了一个老头子,是我们祖父辈的亲戚,具体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弄明白(小时候对这些我是一概不问的),他把我们带到街上去吃早饭。那时候街上已经熙熙攘攘很热闹了,我们又穿过一些傍河的街和不傍河的街,过了一两座桥。我想我很可能见到了电影《林家铺子》里那条街和那爿铺子;也可能见到了电影《蚕花姑娘》里满载白花花蚕茧的小船走的那条河和摇过的那个桥洞。
60年代时,我从报纸和电影杂志上得知,这两部影片里的江南水镇风光镜头都是在新市拍的,可见新市也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威尼斯”式的市镇。九十年代以来,乌镇和周庄被营造成赫赫有名、人气旺盛的国际旅游胜地,而老早在电影里露过脸的新市却被冷落了。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